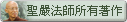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人生421期:懂孤獨,不寂寞
作者:人生雜誌編輯部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09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人生單行本
規格:平裝 / 21x28 cm / 彩色
商品編號:1215000421
定價:NT$180
會員價:NT$30 (17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孤獨是「哪個」?
↑TOP
前言:
在別人眼中,張釗維擁有令人欽羨的家庭、頭銜、成就,
但他的內心卻有一股躁動與悶。
關於紀錄片的普遍性與獨特性、創作者與記錄者之間的拉鋸,
糾結著「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的孤獨……
■ 張釗維(CNEX共同創辦人暨製作總監)
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
既不在這裡,也不在那裡;
那到底是什麼?
這是我內心一直以來的疑情。
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年齡最相近的姊姊長我九歲,父親因工作關係常不在家,成長過程中,除了母親為伴,我幾乎是一個人,陪我長大的是兄姊留下來的書、卡帶,還有模型。但真正感到孤獨,是離家北上念大學,必須獨自面對陌生的環境,一個人生活。
躁動,探向深層的孤獨
讀大學的1980年代,正是解嚴前後,臺灣政治最動盪的時候,我積極加入社團,參與野百合學運、創辦青年獨立文化刊物《破週報》,也像其他人一樣交女朋友,看似很活躍,但內心總有一股躁動,彷彿找不到生命的著力點。曾在晚上一個人數度從新竹騎摩托車到臺北,再騎回新竹,只為替內心那份躁動找出口,那或許是孤獨的表徵,不過那也是到很後來才明白。
大學畢業後,從理工科轉考歷史研究所,雖然父母擔心我未來的出路,但身為家裡最小的孩子,上面的兄姊又都是成功人士,因此家裡給予我很大的自由。儘管自己也不知道要什麼,但自覺比較隨興也很幸運,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從大學、研究所到進報社工作,一直以文字工作為主,尤其寫論文動輒數萬字,其實有點疲乏,退伍後,姊姊送我一部V8,一接觸影像後,發現影像比文字更觸動人心,對人的影響更直接。因此在報社工作半年後,決定到英國攻讀紀錄片製作。1990年代,念影像方面的人不多,又因為學歷史的緣故,我選擇了主修紀錄片而不是電影,歷史是紀實的文字,跟整個社會脈動、文化發展都有關係,不同的是,紀錄片是用影像呈現。
開始拍紀錄片後,我經常到世界各地出差,一到陌生的地方,那種孤獨的感覺就會浮上心頭。從入住旅館到工作開始的這段時間,常要想法子打發,看書、聽音樂、看影片,直到累了就睡覺;有時會到當地夜店、茶館混時間,但因為個性內向,縱使很期待與人互動,由於自己不善搭訕,往往像一個旁觀者,那種時候又隱約感到內心那股由孤獨引發的躁動。
張力拉扯,記錄者的孤獨
一直到四十歲,那份躁動才逐漸平息,意識到那可能是獨處所產生的寂寞,不是真正的孤獨,也慢慢能面對與接受這樣的自己。拍紀錄片讓我安心於事,但籌拍過程中,發現自己看歷史的角度往往屬於非主流,自覺很重要的觀點,可是卻不受大家重視,也找不到可以分享的人;就算有人願意聽,也不見得懂,這種不被了解的感覺,讓我覺得悶。對我來說,拍一部紀錄片,它的普遍性與獨特性是並重的,甚至前者更重於後者,因為紀錄片是為了讓更多人看見,而不只是去追求一個特殊的議題或個人角度,這樣的看法可能也與許多導演不同。
偏偏我又不是藝術家,藝術家可以把不被了解的孤獨視為理所當然,化作創作動力,但紀錄片對我而言不是創作,是一群人在展演他們的生命故事,自己只是一個記錄者,唯有他們被看見,才能讓公眾產生改變的力量,記錄者才有存在的意義。記錄者與創作者的角色,以及紀錄片的普遍性與獨特性之間的張力,不斷將我拉扯著。
紀錄片不同於電影創作,紀錄片是曾發生過的生命軌跡、歷史片段。用什麼角度解讀?如何呈現?是否會被接受?一切都要等到片子完成被看見了,才能得知自己努力的結果,所以拍攝過程中,難免受到委託者、出資方的質疑。例如,之前籌拍《?天》,講述1937至1945年空軍抗戰的故事,找資料時發現很多線索藏在民間的角落,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比如飛行員劉粹剛與許希麟的情書、陳懷民妹妹陳難寫給日軍飛官妻子的信,提醒我,身為空軍太太的她們是很特殊的一群,最後決定以地上的女性角度,來看天上這一群年輕有抱負的空軍。這個角度不是我第一個看到,但卻是第一個重視並且將它呈現出來,這個角度當時也曾受到質疑,但最後我還是說服了大家,放映後獲得不錯的回響,證明這樣的角度是被接受了。
撥開迷霧,見到無我的孤獨
一路走來,如今兩岸三地每年紀錄片的產能已提昇至三、四十部,比起二十年前每年頂多五部的景況,呈現了很大的成長,但相較於一年上百部的電影、電視劇,更不用提破萬部的網路影片,紀錄片仍是弱勢小眾;加上品質良莠不齊,許多人往往一心追求獎項,卻忽略了紀錄片的本質,是為了讓更多人看見,進而正視我們周遭人事物的變化。
面對這種情況,我會有種「夏蟲語冰」的感觸,那無關對錯;就好比修行人,由於修行時間、追求境界不同,某甲可能無法領略某乙的禪悅法喜。有時候我甚至會覺得,紀錄片的發展已偏離本身的宗旨,與自己當初拍紀錄片的初心,似乎愈離愈遠,內心的悶,擴成一片迷團,甚至自問還要繼續拍下去嗎?
所幸,那樣的孤獨感,在拍片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慢慢轉化了,我試著從資料中將自己對歷史的看法寫下來,想寫一部關於中國大陸東南沿岸的歷史,也是一部要給兒子看的歷史書,這是作為父親的我,能夠給兒子最好的禮物。這時候,孤獨感反而變成是創作的原動力。
這二、三年來,聖嚴法師紀錄片是我的拍攝重心,翻閱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法師一直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雖然他也有「佛法那麼好,知道的人那麼少,誤解的人那麼多」的感慨,一路上遇到很多逆增上緣,但他的內心始終充滿能量,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
如果那也是一種孤獨,它不同於追尋自我、凸顯個人主義、我思故我在或存在主義的西方哲學式孤獨,而是一種「無我」的孤獨,一種充滿同理心的慈悲,不會陷在時不我與、自艾自憐的寂寞中無法自拔。期許自己向法師看齊,不管是紀錄片或人生,可以參透「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那到底是什麼」的孤獨公案。(邱惠敏採訪整理)
在別人眼中,張釗維擁有令人欽羨的家庭、頭銜、成就,
但他的內心卻有一股躁動與悶。
關於紀錄片的普遍性與獨特性、創作者與記錄者之間的拉鋸,
糾結著「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的孤獨……
■ 張釗維(CNEX共同創辦人暨製作總監)
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
既不在這裡,也不在那裡;
那到底是什麼?
這是我內心一直以來的疑情。
我是家裡最小的孩子,年齡最相近的姊姊長我九歲,父親因工作關係常不在家,成長過程中,除了母親為伴,我幾乎是一個人,陪我長大的是兄姊留下來的書、卡帶,還有模型。但真正感到孤獨,是離家北上念大學,必須獨自面對陌生的環境,一個人生活。
躁動,探向深層的孤獨
讀大學的1980年代,正是解嚴前後,臺灣政治最動盪的時候,我積極加入社團,參與野百合學運、創辦青年獨立文化刊物《破週報》,也像其他人一樣交女朋友,看似很活躍,但內心總有一股躁動,彷彿找不到生命的著力點。曾在晚上一個人數度從新竹騎摩托車到臺北,再騎回新竹,只為替內心那份躁動找出口,那或許是孤獨的表徵,不過那也是到很後來才明白。
大學畢業後,從理工科轉考歷史研究所,雖然父母擔心我未來的出路,但身為家裡最小的孩子,上面的兄姊又都是成功人士,因此家裡給予我很大的自由。儘管自己也不知道要什麼,但自覺比較隨興也很幸運,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從大學、研究所到進報社工作,一直以文字工作為主,尤其寫論文動輒數萬字,其實有點疲乏,退伍後,姊姊送我一部V8,一接觸影像後,發現影像比文字更觸動人心,對人的影響更直接。因此在報社工作半年後,決定到英國攻讀紀錄片製作。1990年代,念影像方面的人不多,又因為學歷史的緣故,我選擇了主修紀錄片而不是電影,歷史是紀實的文字,跟整個社會脈動、文化發展都有關係,不同的是,紀錄片是用影像呈現。
開始拍紀錄片後,我經常到世界各地出差,一到陌生的地方,那種孤獨的感覺就會浮上心頭。從入住旅館到工作開始的這段時間,常要想法子打發,看書、聽音樂、看影片,直到累了就睡覺;有時會到當地夜店、茶館混時間,但因為個性內向,縱使很期待與人互動,由於自己不善搭訕,往往像一個旁觀者,那種時候又隱約感到內心那股由孤獨引發的躁動。
張力拉扯,記錄者的孤獨
一直到四十歲,那份躁動才逐漸平息,意識到那可能是獨處所產生的寂寞,不是真正的孤獨,也慢慢能面對與接受這樣的自己。拍紀錄片讓我安心於事,但籌拍過程中,發現自己看歷史的角度往往屬於非主流,自覺很重要的觀點,可是卻不受大家重視,也找不到可以分享的人;就算有人願意聽,也不見得懂,這種不被了解的感覺,讓我覺得悶。對我來說,拍一部紀錄片,它的普遍性與獨特性是並重的,甚至前者更重於後者,因為紀錄片是為了讓更多人看見,而不只是去追求一個特殊的議題或個人角度,這樣的看法可能也與許多導演不同。
偏偏我又不是藝術家,藝術家可以把不被了解的孤獨視為理所當然,化作創作動力,但紀錄片對我而言不是創作,是一群人在展演他們的生命故事,自己只是一個記錄者,唯有他們被看見,才能讓公眾產生改變的力量,記錄者才有存在的意義。記錄者與創作者的角色,以及紀錄片的普遍性與獨特性之間的張力,不斷將我拉扯著。
紀錄片不同於電影創作,紀錄片是曾發生過的生命軌跡、歷史片段。用什麼角度解讀?如何呈現?是否會被接受?一切都要等到片子完成被看見了,才能得知自己努力的結果,所以拍攝過程中,難免受到委託者、出資方的質疑。例如,之前籌拍《?天》,講述1937至1945年空軍抗戰的故事,找資料時發現很多線索藏在民間的角落,一般人是看不到的,比如飛行員劉粹剛與許希麟的情書、陳懷民妹妹陳難寫給日軍飛官妻子的信,提醒我,身為空軍太太的她們是很特殊的一群,最後決定以地上的女性角度,來看天上這一群年輕有抱負的空軍。這個角度不是我第一個看到,但卻是第一個重視並且將它呈現出來,這個角度當時也曾受到質疑,但最後我還是說服了大家,放映後獲得不錯的回響,證明這樣的角度是被接受了。
撥開迷霧,見到無我的孤獨
一路走來,如今兩岸三地每年紀錄片的產能已提昇至三、四十部,比起二十年前每年頂多五部的景況,呈現了很大的成長,但相較於一年上百部的電影、電視劇,更不用提破萬部的網路影片,紀錄片仍是弱勢小眾;加上品質良莠不齊,許多人往往一心追求獎項,卻忽略了紀錄片的本質,是為了讓更多人看見,進而正視我們周遭人事物的變化。
面對這種情況,我會有種「夏蟲語冰」的感觸,那無關對錯;就好比修行人,由於修行時間、追求境界不同,某甲可能無法領略某乙的禪悅法喜。有時候我甚至會覺得,紀錄片的發展已偏離本身的宗旨,與自己當初拍紀錄片的初心,似乎愈離愈遠,內心的悶,擴成一片迷團,甚至自問還要繼續拍下去嗎?
所幸,那樣的孤獨感,在拍片蒐集資料的過程中慢慢轉化了,我試著從資料中將自己對歷史的看法寫下來,想寫一部關於中國大陸東南沿岸的歷史,也是一部要給兒子看的歷史書,這是作為父親的我,能夠給兒子最好的禮物。這時候,孤獨感反而變成是創作的原動力。
這二、三年來,聖嚴法師紀錄片是我的拍攝重心,翻閱資料的過程中,發現法師一直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雖然他也有「佛法那麼好,知道的人那麼少,誤解的人那麼多」的感慨,一路上遇到很多逆增上緣,但他的內心始終充滿能量,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
如果那也是一種孤獨,它不同於追尋自我、凸顯個人主義、我思故我在或存在主義的西方哲學式孤獨,而是一種「無我」的孤獨,一種充滿同理心的慈悲,不會陷在時不我與、自艾自憐的寂寞中無法自拔。期許自己向法師看齊,不管是紀錄片或人生,可以參透「既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那到底是什麼」的孤獨公案。(邱惠敏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