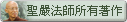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牛的印跡:禪修與開悟見性的道路
Hoofprint of the Ox: Principles of the Chan Buddhist Path as Taught by a Modern Chinese Master
作者:聖嚴法師、丹.史蒂文生
譯者:梁永安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23年01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大智慧
規格:平裝 / 15x21 cm / 448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0750181
ISBN:9789575989705
定價:NT$480
會員價:NT$408 (85折)
序/後記
< 回商品頁序
↑TOP
聖嚴法師是禪門曹洞宗與臨濟宗的法師,二十年來在臺灣、美國和歐洲接引信徒不遺餘力。《牛的印跡》這本書,是要用聖嚴法師自己的語言,為他獨具特色的禪法所依據的原則,提供一個系統性的導論。
多年前初識法師時,我聽他說了一則故事。有一個人手持寶劍乘船渡江,中途不小心把劍掉到水裡。他在劍落水處的船舷做了一個記號,等船靠岸,再在記號下方的水裡到處尋覓,結果找了一整天都毫無所獲。這個寓言,許多方面符合了聖嚴法師對禪修的觀點。
法師生於清帝國覆滅後的時期,親歷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戰、共產革命和中國人為建造一個強大新中國持續至今的努力。所有這些經驗,都在法師其人及其學說裡留下無可磨滅的印記。雖然深受中國傳統僧院文化的影響,但聖嚴法師憑著禪修與多年來教導中國和西方學生的經驗,也對這種文化的局限性產生敏銳的體認。因此,他的教誨是前瞻性的,並且他毫不諱言對過去的吸納有所選擇。法師不願意當個刻舟求劍的人。
當然,對很多西方讀者來說,聽到我說在今天的中國還有禪師,也許會感到驚訝,甚至不敢置信。按照流行的觀點(一種除中國人以外幾乎任何人都相信的觀點),真正的禪學早在十多世紀以前就已從中國消失,而這一點,是因為佛教自唐代衰亡(九○六)後出現「庸俗化」所造成的。對持這種看法的人來說,聖嚴法師的禪學之所以和想像中一千年前的禪學有所出入,正好是禪學在中國已經式微的佐證。然而,聖嚴法師卻是當今中國僧人裡最受仰慕的其中一位,他的禪修課程動輒吸引數以百計的報名者,而他的公開佛法講座吸引到坐滿一整個音樂廳的聽眾,也是常有的事。
聖嚴法師並不是一個特例。在比他早一輩的僧人中,虛雲老和尚(一八四○~一九五九)和來果禪師(卒於一九五三)以及天寧寺、南華寺和高旻寺這些禪學重鎮,都被視為是禪傳統的楷模,足以與禪宗的遙遠過去並駕齊驅。不管我們拿從前哪一個時代來跟近代中國禪學比較,我們就是無法得出禪學在現今中國是死氣沉沉的結論。
就像日本、韓國與越南的佛教徒那樣,中國的禪師與禪修團體都自視為佛教「黃金時代」(唐代)遺產的繼承者。而且也像日本、韓國與越南的佛教徒那樣,中國的禪師彼此間也會爭論傳統與變遷、忠實與偽誤的問題;事實上,這些也是歷代不同的禪宗派別常常爭論的問題。雖然有些人主張,禪宗想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須抗拒變遷,並保存傳統的禪與修行方法,但聖嚴法師和一些僧人卻不如是觀,反而認為轉變才是生命力之所繫。正如聖嚴法師所說的︰「如果想要找出中國禪宗一個明確的特徵,那大概就是:禪在中國一直是處於變化之中的。」
如果我們能夠一改多年來的偏見,重新評價近代中國的佛教文化,就會發現這是值得的。尉遲酣(Holmes Welch)在其研究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佛教復興運動的經典著作中,就已經對此做過嘗試。過去二十年來,佛教以前所未有的蓬勃,在工業化的臺灣繁榮滋長。①當我一九八一年在臺灣參加佛經的大眾講座時,一個晚上的聽眾是兩百到三百人,而現在,聽眾的數目即使未達數萬人,至少也是數以千計。佛教組織的規模也相當驚人。像是由花蓮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功德會,轄下就有醫院、基金會和大批隨時為應付各種社會災難而待命的志工。
還有許許多多的組織(包括聖嚴法師的「法鼓山」在內),資助從佛學課程到環保計畫等範圍廣泛的活動,舉辦為俗家人而設的禪七和念佛會,又把很多過去只有在佛寺裡才接觸得到的佛教教義,介紹給大眾。很多這一類的活動,追本溯源,就是由民國初年致力於復興佛教的僧俗人士發起的。聖嚴法師身為這個傳統的繼承者,又是今日中國佛教界的領導人物之一,他的這本《牛的印跡》,可說是一個適時的窗口,讓我們一窺中國佛教史上一個深具潛力的階段。
不過,如果說《牛的印跡》有紀實價值的話,那並不代表它的意義僅止於一件文化展示品。歸根究柢,《牛的印跡》乃是一部規範性的作品:一本向全世界對佛教感興趣的大眾介紹禪修方法的作品。此書絕不只是聖嚴法師個人信仰的一個記錄,相反的,這些信仰能回應學禪者對禪修的某些誤解,這本書是有特別的話要說的。
聖嚴法師在講課時忍不住要反覆批判的有兩個誤解:一是認為禪是一種純粹直觀的修行,與文字和概念架構完全無涉;另一個則是認為禪是獨立自成的,與傳統的佛教教義迥不相干。聖嚴法師在中國大陸當小沙彌的歲月中,曾對這兩個誤解的遺害有過深切感受。不過對禪宗的新鮮人來說,這兩個誤解又尤其危險,值得我們在這裡略談一談。
很多讀者都知道,禪是一種泛見於整個東亞的佛教傳統(中國的Chan、日本的Zen、越南的Thién、韓國的Sôn),而它首度形成自己鮮明的輪廓,是在一千五百年前的中國。就像大多數東亞大乘佛教的宗派一樣,禪宗相信,釋迦牟尼在成佛時所體現的覺性,是眾生本具的。這種覺性又稱為「佛性」,它並不是後天學習得來,被賦予、或重新啟動的,而是如如自然,而且一直就是自然而然的。
禪宗也像大多數其他佛教宗派一樣,聲稱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艘可以把人渡到「彼岸」的「擺渡」、是一根指示月亮方向的「手指」。不過,禪宗和別的宗派不一樣之處,在於它認為人應該直接面向月亮和彼岸,而不要一味把注意力放在「手指」和「擺渡」上。它主張一種「無法之法」,不依賴思惟,不拘於言說文字,以「直指本心」為旨歸。馬祖道一禪師(七○九~七八八)一再強調「平常心是道」②,臨濟義玄(卒於八六七年)則敦促弟子「只當個無事人就好」③。
這些主張,因為對人的內在價值予以無條件的肯定,所以聽起來非常合乎自然,非常有吸引力。在那些對既有宗教建制已經不抱幻想的人看來,這些主張甚至像一種失落的智慧,既充滿應許,又沒有把「組織性宗教」的枷鎖強加於人。然而,只要對禪宗稍加接觸,就會知道它教導的第一課,就是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什麼是自然而然的。不管本具的佛性可以把我們帶到何種明覺的境界,但從無始時來,這種佛性就受到了貪、瞋、癡三種煩惱(佛教稱之為三毒)的扭曲,變得面目全非。哪裡有光,哪裡就會有陰影;哪裡有和平喜樂,哪裡就會有衝突痛苦。這全都是累世的惡業和惡念所造成的障礙引起的。
不管佛性的概念乍看之下是多麼地自我肯定,但糾纏我們的各種煩惱就是不會自己消失。想要讓佛性展現,需要進行一場徹徹底底的心靈革命。而想要達到這樣的轉化,又必須先要有方向感、決心、貫徹一生的毅力和鍛鍊,以及——這是常常被忽略的一點——規制。
事實上,當馬祖道一說出「平常心是道」一語時,他的話是針對那些已經過著最有紀律生活的僧團而發的。不管是在中國、越南、日本還是韓國的禪學派別,這種組織是無所不在的︰它們表現在每日的禪修作息規律,表現在禪堂的格局和運作,表現在師父與弟子間的應對進退,表現在佛壇前的早晚課,表現在行者的受持戒律,甚至表現在禪宗高度風格化的語言、意象、文字,以及頗為古怪的禪公案裡。這就是歷史上禪宗的實質(至少聖嚴法師是這樣認為的),也是《牛的印跡》一書教誨的立足點。
禪對西方來說幾乎是全新的東西,西方不但不熟悉它的術語,而且因為西方認定它是透明和率真的(這也是它吸引人的原因),遂對它產生很多不符事實的期望。這使得美國的學禪者和禪的論述與中國、越南、韓國與日本的情況大異其趣。特別是因為禪宗強調「不立文字」的直觀主義和「以心傳心」的方法,讓美國的禪修者夾帶了很多奇怪的、未明說的假設。正如很多美國禪修團體在一九八○年代初期(一個禪師人數在美國銳減的時代)所證明的,任由這些假設默默存在而不加以討論的話,它們會產生很大的殺傷力。
聖嚴法師的憂慮是,人們誤解禪只是一種「離言說文字」的修行或直接體悟。多年前,我曾在聖嚴法師紐約的一場演講中擔任翻譯,題目是禪修與「般若」以及「空」的關係(這在當時是一個常常談論到的題目)。到了發問時間,一個長相銳利的聽眾站了起來,直直看著法師的眼睛,問道︰「你是開了一張精彩的菜單,但菜在哪裡呢?」講堂裡頓時鴉雀無聲,全部眼睛盯在法師臉上。不過,法師從容平靜地回答說︰「有空來打打禪七吧。」(摘錄)
多年前初識法師時,我聽他說了一則故事。有一個人手持寶劍乘船渡江,中途不小心把劍掉到水裡。他在劍落水處的船舷做了一個記號,等船靠岸,再在記號下方的水裡到處尋覓,結果找了一整天都毫無所獲。這個寓言,許多方面符合了聖嚴法師對禪修的觀點。
法師生於清帝國覆滅後的時期,親歷了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第二次世界大戰、共產革命和中國人為建造一個強大新中國持續至今的努力。所有這些經驗,都在法師其人及其學說裡留下無可磨滅的印記。雖然深受中國傳統僧院文化的影響,但聖嚴法師憑著禪修與多年來教導中國和西方學生的經驗,也對這種文化的局限性產生敏銳的體認。因此,他的教誨是前瞻性的,並且他毫不諱言對過去的吸納有所選擇。法師不願意當個刻舟求劍的人。
當然,對很多西方讀者來說,聽到我說在今天的中國還有禪師,也許會感到驚訝,甚至不敢置信。按照流行的觀點(一種除中國人以外幾乎任何人都相信的觀點),真正的禪學早在十多世紀以前就已從中國消失,而這一點,是因為佛教自唐代衰亡(九○六)後出現「庸俗化」所造成的。對持這種看法的人來說,聖嚴法師的禪學之所以和想像中一千年前的禪學有所出入,正好是禪學在中國已經式微的佐證。然而,聖嚴法師卻是當今中國僧人裡最受仰慕的其中一位,他的禪修課程動輒吸引數以百計的報名者,而他的公開佛法講座吸引到坐滿一整個音樂廳的聽眾,也是常有的事。
聖嚴法師並不是一個特例。在比他早一輩的僧人中,虛雲老和尚(一八四○~一九五九)和來果禪師(卒於一九五三)以及天寧寺、南華寺和高旻寺這些禪學重鎮,都被視為是禪傳統的楷模,足以與禪宗的遙遠過去並駕齊驅。不管我們拿從前哪一個時代來跟近代中國禪學比較,我們就是無法得出禪學在現今中國是死氣沉沉的結論。
就像日本、韓國與越南的佛教徒那樣,中國的禪師與禪修團體都自視為佛教「黃金時代」(唐代)遺產的繼承者。而且也像日本、韓國與越南的佛教徒那樣,中國的禪師彼此間也會爭論傳統與變遷、忠實與偽誤的問題;事實上,這些也是歷代不同的禪宗派別常常爭論的問題。雖然有些人主張,禪宗想要保持生命力,就必須抗拒變遷,並保存傳統的禪與修行方法,但聖嚴法師和一些僧人卻不如是觀,反而認為轉變才是生命力之所繫。正如聖嚴法師所說的︰「如果想要找出中國禪宗一個明確的特徵,那大概就是:禪在中國一直是處於變化之中的。」
如果我們能夠一改多年來的偏見,重新評價近代中國的佛教文化,就會發現這是值得的。尉遲酣(Holmes Welch)在其研究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佛教復興運動的經典著作中,就已經對此做過嘗試。過去二十年來,佛教以前所未有的蓬勃,在工業化的臺灣繁榮滋長。①當我一九八一年在臺灣參加佛經的大眾講座時,一個晚上的聽眾是兩百到三百人,而現在,聽眾的數目即使未達數萬人,至少也是數以千計。佛教組織的規模也相當驚人。像是由花蓮證嚴法師創辦的慈濟功德會,轄下就有醫院、基金會和大批隨時為應付各種社會災難而待命的志工。
還有許許多多的組織(包括聖嚴法師的「法鼓山」在內),資助從佛學課程到環保計畫等範圍廣泛的活動,舉辦為俗家人而設的禪七和念佛會,又把很多過去只有在佛寺裡才接觸得到的佛教教義,介紹給大眾。很多這一類的活動,追本溯源,就是由民國初年致力於復興佛教的僧俗人士發起的。聖嚴法師身為這個傳統的繼承者,又是今日中國佛教界的領導人物之一,他的這本《牛的印跡》,可說是一個適時的窗口,讓我們一窺中國佛教史上一個深具潛力的階段。
不過,如果說《牛的印跡》有紀實價值的話,那並不代表它的意義僅止於一件文化展示品。歸根究柢,《牛的印跡》乃是一部規範性的作品:一本向全世界對佛教感興趣的大眾介紹禪修方法的作品。此書絕不只是聖嚴法師個人信仰的一個記錄,相反的,這些信仰能回應學禪者對禪修的某些誤解,這本書是有特別的話要說的。
聖嚴法師在講課時忍不住要反覆批判的有兩個誤解:一是認為禪是一種純粹直觀的修行,與文字和概念架構完全無涉;另一個則是認為禪是獨立自成的,與傳統的佛教教義迥不相干。聖嚴法師在中國大陸當小沙彌的歲月中,曾對這兩個誤解的遺害有過深切感受。不過對禪宗的新鮮人來說,這兩個誤解又尤其危險,值得我們在這裡略談一談。
很多讀者都知道,禪是一種泛見於整個東亞的佛教傳統(中國的Chan、日本的Zen、越南的Thién、韓國的Sôn),而它首度形成自己鮮明的輪廓,是在一千五百年前的中國。就像大多數東亞大乘佛教的宗派一樣,禪宗相信,釋迦牟尼在成佛時所體現的覺性,是眾生本具的。這種覺性又稱為「佛性」,它並不是後天學習得來,被賦予、或重新啟動的,而是如如自然,而且一直就是自然而然的。
禪宗也像大多數其他佛教宗派一樣,聲稱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艘可以把人渡到「彼岸」的「擺渡」、是一根指示月亮方向的「手指」。不過,禪宗和別的宗派不一樣之處,在於它認為人應該直接面向月亮和彼岸,而不要一味把注意力放在「手指」和「擺渡」上。它主張一種「無法之法」,不依賴思惟,不拘於言說文字,以「直指本心」為旨歸。馬祖道一禪師(七○九~七八八)一再強調「平常心是道」②,臨濟義玄(卒於八六七年)則敦促弟子「只當個無事人就好」③。
這些主張,因為對人的內在價值予以無條件的肯定,所以聽起來非常合乎自然,非常有吸引力。在那些對既有宗教建制已經不抱幻想的人看來,這些主張甚至像一種失落的智慧,既充滿應許,又沒有把「組織性宗教」的枷鎖強加於人。然而,只要對禪宗稍加接觸,就會知道它教導的第一課,就是這個世界根本沒有什麼是自然而然的。不管本具的佛性可以把我們帶到何種明覺的境界,但從無始時來,這種佛性就受到了貪、瞋、癡三種煩惱(佛教稱之為三毒)的扭曲,變得面目全非。哪裡有光,哪裡就會有陰影;哪裡有和平喜樂,哪裡就會有衝突痛苦。這全都是累世的惡業和惡念所造成的障礙引起的。
不管佛性的概念乍看之下是多麼地自我肯定,但糾纏我們的各種煩惱就是不會自己消失。想要讓佛性展現,需要進行一場徹徹底底的心靈革命。而想要達到這樣的轉化,又必須先要有方向感、決心、貫徹一生的毅力和鍛鍊,以及——這是常常被忽略的一點——規制。
事實上,當馬祖道一說出「平常心是道」一語時,他的話是針對那些已經過著最有紀律生活的僧團而發的。不管是在中國、越南、日本還是韓國的禪學派別,這種組織是無所不在的︰它們表現在每日的禪修作息規律,表現在禪堂的格局和運作,表現在師父與弟子間的應對進退,表現在佛壇前的早晚課,表現在行者的受持戒律,甚至表現在禪宗高度風格化的語言、意象、文字,以及頗為古怪的禪公案裡。這就是歷史上禪宗的實質(至少聖嚴法師是這樣認為的),也是《牛的印跡》一書教誨的立足點。
禪對西方來說幾乎是全新的東西,西方不但不熟悉它的術語,而且因為西方認定它是透明和率真的(這也是它吸引人的原因),遂對它產生很多不符事實的期望。這使得美國的學禪者和禪的論述與中國、越南、韓國與日本的情況大異其趣。特別是因為禪宗強調「不立文字」的直觀主義和「以心傳心」的方法,讓美國的禪修者夾帶了很多奇怪的、未明說的假設。正如很多美國禪修團體在一九八○年代初期(一個禪師人數在美國銳減的時代)所證明的,任由這些假設默默存在而不加以討論的話,它們會產生很大的殺傷力。
聖嚴法師的憂慮是,人們誤解禪只是一種「離言說文字」的修行或直接體悟。多年前,我曾在聖嚴法師紐約的一場演講中擔任翻譯,題目是禪修與「般若」以及「空」的關係(這在當時是一個常常談論到的題目)。到了發問時間,一個長相銳利的聽眾站了起來,直直看著法師的眼睛,問道︰「你是開了一張精彩的菜單,但菜在哪裡呢?」講堂裡頓時鴉雀無聲,全部眼睛盯在法師臉上。不過,法師從容平靜地回答說︰「有空來打打禪七吧。」(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