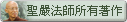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傳入西藏的中國禪法
Tibetan Zen: Discovering a Lost Tradition
譯者:黃書蓉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22年12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法鼓文理學院譯叢
規格:平裝 / 21x15 cm / 272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190051
ISBN:9789575989750
定價:NT$350
會員價:NT$298 (85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導論 一個消失的傳統?
↑TOP
在西藏被否定,在中國被遺忘,傳入西藏的中國禪法幾乎已完全消失。八世紀時,鼎盛時期的吐蕃帝國邀請漢地禪師到訪,禪法便於此時首次傳入。根據傳統歷史,在西藏王室中,印度和中國的佛教徒於教義上的分歧持續擴大,西藏贊普便要求以一場正式的辯論來解決這種情況。當法諍導致印度方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時,禪師便被遣送回中國了。雖然這個故事曾受到質疑,但很明顯的,禪法在西藏的影響力日益衰退,其原始文本也被完全遺忘。
這種情況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在中國中亞地區的敦煌所發現的一個滿是古老寫本的密封洞窟才有所改觀。洞窟中的藏文寫本可以追溯至九、十世紀,使它們成為已知最早的西藏佛教資料。其中大約有五十多個寫本是僅存的原始藏文禪法文本,也是了解傳入西藏的禪法主要的資料來源。這些寫本提供了八至十世紀早期禪法傳統的樣貌,所以也可以做為研究中國、日本,及韓國禪宗的重要資料來源。再者,西藏禪法顯然曾經融入密法的元素,而發展成一個獨特的傳統,然而這個神奇的融合卻仍鮮為人知。
在中亞沙漠的邊緣,從一片峭壁中開鑿出許多洞窟,這個密封洞窟便是敦煌佛教洞窟群的一部分。我們對於這個洞窟知之甚少,既不了解它為何裝滿了寫本,也不清楚它為何被封。但我們卻擁有這個歷史偶發事件的結果,那就是數以千計中文、藏文、突厥文、梵文及其他語種的書籍,以及佛教繪畫和寺院牌匾。事實上,「圖書館洞」一詞是種誤導,因為據我們所知,這些埋藏起來的寫本,並非條理分明的圖書館藏品。除了佛教經典、註釋本和論書外,還有筆記本、採買清單、練字本、信件、合約、簡圖以及隨筆塗鴉。
因此,放入洞窟中的,並非井然有序、精挑細選過的圖書館館藏,而是這個城鎮及寺院日常生活的雜亂物品。對於過去百年來研究此洞窟文本的許多學者來說,這似乎是種困擾。但對於我們這個想要了解一個曾經存在,但卻消失無蹤之傳統的研究來說,卻是種優勢。在西藏傳統中,我們已經擁有一整套佛教大藏經,其中包括百卷以上的經典、注疏以及論文。然而藏經並無法完整表達出宗教傳統的真實日常。經典入藏的標準取決於藏經編輯與贊助者,而非日常的宗教生活。而一個宗教傳統也藉由這些「決定」來界定自身。在大藏經中,類似的文本被整合入同一個部類。這些依部類而分置的文本,在入藏經前,其實是更複雜且各具特色的。
這就是藏於敦煌洞窟之寫本的優勢所在。它們有可能如第一位拜訪石窟的歐洲人奧萊爾‧斯坦因(Aurel Stein)所說的,是「神聖的垃圾」,而不是如同藏經藏書一般精挑細選井井有條,並展現出完美傳統形象的東西。在這堆混雜的舊物中,文本彼此堆疊磨擦,這是莊嚴肅穆的藏經所無法容忍的情況。也許我們可以自問自答的是:人們用這些文本來做什麼;它們的功能究竟為何?
讓我們以最早流傳下來的藏文禪法寫本為例。那是個卷軸殘片,不在敦煌,而在遙遠西方一處西藏碉堡的廢墟中。此碉堡現在以米蘭(Miran)這個突厥語名稱而為人所熟知,在九世紀中到十世紀中時由藏人建造,用於守衛其帝國邊境。傳統上對於這個特殊物件的文本研究法,是謄錄這件禪本,在文本最後附上發現它的地點,以及它可能被撰寫的時間範圍,然後在純文本的領域中與其他類似的單篇文本進行比對。
拿到文本後,與其匆忙地離開碉堡,我們不如多待一些時間,看看由考古學家奧萊爾‧斯坦因所發現的這件卷軸旁的一些其他物件。有軍人的物品:盔甲上的皮革鱗片、一個箭鏃,及一隻羽毛箭杆。還有一些任何人都可能使用過的東西:一些皮囊、一隻梳子、一把鑰匙、一把木柄刀、一粒六邊形的骰子。然後有些用來製作寫本的物品:一隻筆尖分岔的鵝管筆和三個獸角握柄印章,用來在官方書信及契約上蓋章。這些都是陪伴最早的藏文禪本千年以上的物品,我們不應太快拆散它們。
至於碉堡內的其他寫本,大部分是吐蕃帝國不同前哨站之間的官方公報。較短的每日訊息是以細長的木片傳送,有時會用兩片,使其能以細繩綑綁再用黏土封印。當有補給品的請求時,木片會被削掉右下角做為記號,等補給品到達,便可當作收條與原本的訂單進行比對。是什麼原因使得碉堡中的物件與這些官方文書放在一起,這個問題,我們傾向透過釐清這些物件的用途來解答。這些物件背後的行為模式是什麼?骰子是用來占卜、賭博,亦或兩者皆是?這個軍人會多常需要使用到這些箭?他也用筆來速記訊息,還是碉堡中備有專門的書記官?當訊息寫好,誰把它們帶到最近的軍隊指揮部?誰又把食物及其他補給品帶回來?也許這些問題不總是能有答案,但提出這些問題,卻似乎理所當然,切合實際。
因此,如同我們想對骰子、箭和皮囊所問的問題一樣,如果我們要對米蘭出土的禪法文本(又或是文本中摘錄出來的部分)提出問題,那會是什麼?我們會問:它是如何製作的?誰把它帶來這裡?誰使用它,目的為何?這些問題對考古學家來說,會變成更為廣泛的行為模式的問題。藉由從大型考古遺址取出的一整批物件,將它們依照彼此的關係來排放,我們就有可能釐清這些模式。這種作法讓我們不僅思考文本的意義,更加上了它的功能,也就是它原本被設定的實際用途。
因為米蘭沒有造紙設備,藏文禪卷是因為某些原因而被帶到了那裡。當然,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明白其目的,但藉由仔細觀察寫本,我們也許能找到一些線索。例如,翻過面來,我們發現背頁寫著另一篇文章,字跡較禪本凌亂些。這是個密法修持法本,說明對佛教本尊獻供以完成息、增、懷、誅四業的修持法。這些修持法對於遙遠碉堡的軍士大有助益。所以這個藏文禪本有可能只是順道攜來,而不是被帶去實際使用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位在家或出家佛教徒帶去的某個修行法門的一部分。然而我們真的能從這樣的物件中,得知它們所關聯的日常修行嗎?
這種情況一直到二十世紀初,在中國中亞地區的敦煌所發現的一個滿是古老寫本的密封洞窟才有所改觀。洞窟中的藏文寫本可以追溯至九、十世紀,使它們成為已知最早的西藏佛教資料。其中大約有五十多個寫本是僅存的原始藏文禪法文本,也是了解傳入西藏的禪法主要的資料來源。這些寫本提供了八至十世紀早期禪法傳統的樣貌,所以也可以做為研究中國、日本,及韓國禪宗的重要資料來源。再者,西藏禪法顯然曾經融入密法的元素,而發展成一個獨特的傳統,然而這個神奇的融合卻仍鮮為人知。
在中亞沙漠的邊緣,從一片峭壁中開鑿出許多洞窟,這個密封洞窟便是敦煌佛教洞窟群的一部分。我們對於這個洞窟知之甚少,既不了解它為何裝滿了寫本,也不清楚它為何被封。但我們卻擁有這個歷史偶發事件的結果,那就是數以千計中文、藏文、突厥文、梵文及其他語種的書籍,以及佛教繪畫和寺院牌匾。事實上,「圖書館洞」一詞是種誤導,因為據我們所知,這些埋藏起來的寫本,並非條理分明的圖書館藏品。除了佛教經典、註釋本和論書外,還有筆記本、採買清單、練字本、信件、合約、簡圖以及隨筆塗鴉。
因此,放入洞窟中的,並非井然有序、精挑細選過的圖書館館藏,而是這個城鎮及寺院日常生活的雜亂物品。對於過去百年來研究此洞窟文本的許多學者來說,這似乎是種困擾。但對於我們這個想要了解一個曾經存在,但卻消失無蹤之傳統的研究來說,卻是種優勢。在西藏傳統中,我們已經擁有一整套佛教大藏經,其中包括百卷以上的經典、注疏以及論文。然而藏經並無法完整表達出宗教傳統的真實日常。經典入藏的標準取決於藏經編輯與贊助者,而非日常的宗教生活。而一個宗教傳統也藉由這些「決定」來界定自身。在大藏經中,類似的文本被整合入同一個部類。這些依部類而分置的文本,在入藏經前,其實是更複雜且各具特色的。
這就是藏於敦煌洞窟之寫本的優勢所在。它們有可能如第一位拜訪石窟的歐洲人奧萊爾‧斯坦因(Aurel Stein)所說的,是「神聖的垃圾」,而不是如同藏經藏書一般精挑細選井井有條,並展現出完美傳統形象的東西。在這堆混雜的舊物中,文本彼此堆疊磨擦,這是莊嚴肅穆的藏經所無法容忍的情況。也許我們可以自問自答的是:人們用這些文本來做什麼;它們的功能究竟為何?
讓我們以最早流傳下來的藏文禪法寫本為例。那是個卷軸殘片,不在敦煌,而在遙遠西方一處西藏碉堡的廢墟中。此碉堡現在以米蘭(Miran)這個突厥語名稱而為人所熟知,在九世紀中到十世紀中時由藏人建造,用於守衛其帝國邊境。傳統上對於這個特殊物件的文本研究法,是謄錄這件禪本,在文本最後附上發現它的地點,以及它可能被撰寫的時間範圍,然後在純文本的領域中與其他類似的單篇文本進行比對。
拿到文本後,與其匆忙地離開碉堡,我們不如多待一些時間,看看由考古學家奧萊爾‧斯坦因所發現的這件卷軸旁的一些其他物件。有軍人的物品:盔甲上的皮革鱗片、一個箭鏃,及一隻羽毛箭杆。還有一些任何人都可能使用過的東西:一些皮囊、一隻梳子、一把鑰匙、一把木柄刀、一粒六邊形的骰子。然後有些用來製作寫本的物品:一隻筆尖分岔的鵝管筆和三個獸角握柄印章,用來在官方書信及契約上蓋章。這些都是陪伴最早的藏文禪本千年以上的物品,我們不應太快拆散它們。
至於碉堡內的其他寫本,大部分是吐蕃帝國不同前哨站之間的官方公報。較短的每日訊息是以細長的木片傳送,有時會用兩片,使其能以細繩綑綁再用黏土封印。當有補給品的請求時,木片會被削掉右下角做為記號,等補給品到達,便可當作收條與原本的訂單進行比對。是什麼原因使得碉堡中的物件與這些官方文書放在一起,這個問題,我們傾向透過釐清這些物件的用途來解答。這些物件背後的行為模式是什麼?骰子是用來占卜、賭博,亦或兩者皆是?這個軍人會多常需要使用到這些箭?他也用筆來速記訊息,還是碉堡中備有專門的書記官?當訊息寫好,誰把它們帶到最近的軍隊指揮部?誰又把食物及其他補給品帶回來?也許這些問題不總是能有答案,但提出這些問題,卻似乎理所當然,切合實際。
因此,如同我們想對骰子、箭和皮囊所問的問題一樣,如果我們要對米蘭出土的禪法文本(又或是文本中摘錄出來的部分)提出問題,那會是什麼?我們會問:它是如何製作的?誰把它帶來這裡?誰使用它,目的為何?這些問題對考古學家來說,會變成更為廣泛的行為模式的問題。藉由從大型考古遺址取出的一整批物件,將它們依照彼此的關係來排放,我們就有可能釐清這些模式。這種作法讓我們不僅思考文本的意義,更加上了它的功能,也就是它原本被設定的實際用途。
因為米蘭沒有造紙設備,藏文禪卷是因為某些原因而被帶到了那裡。當然,我們可能永遠無法明白其目的,但藉由仔細觀察寫本,我們也許能找到一些線索。例如,翻過面來,我們發現背頁寫著另一篇文章,字跡較禪本凌亂些。這是個密法修持法本,說明對佛教本尊獻供以完成息、增、懷、誅四業的修持法。這些修持法對於遙遠碉堡的軍士大有助益。所以這個藏文禪本有可能只是順道攜來,而不是被帶去實際使用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位在家或出家佛教徒帶去的某個修行法門的一部分。然而我們真的能從這樣的物件中,得知它們所關聯的日常修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