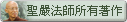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中國佛教文化研究論集【內頁泛黃】
作者:冉雲華
出版社:法鼓文化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智慧海
規格:15x21 cm / 平裝 / 344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000181
ISBN:2001010100184
定價:NT$250
會員價:NT$125 (50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一○、元代禪僧與西藏喇嘛辨論考
↑TOP
一○、元代禪僧與西藏喇嘛辨論考
現代的學者都曉得,西元第八世紀中國和印度的佛教哲學家曾在拉薩辯論過。歷史和語言學家也都知道八思巴在元朝有崇高地位。但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間禪僧和八思巴在大都(北平)辯論一事,幾乎不為研究者所注意,實在是相當不平常。這件事或許是因發生在拉薩辯論之後,中國和西藏的佛教徒之間唯一有意義的辯論,因此它的重要性,在佛教史或佛教的比較研究史上,是不需要誇張的。由於學者還只留意前次的辯論,所以研究元代禪僧和西藏喇嘛的辯論也可能有助於瞭解上一次的辯論。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論述下列諸問題:第一,本論文將嘗試揭露元朝禪僧和西藏喇嘛辯論的事實和主題;第二,依照辯論來衡量禪和西藏佛教的發展。為了重視推究,本論文接著要把元朝那次辯論和第八世紀舉行的辯論併在一起討論。
最早提到元朝那次辯論的書是鄧文原的著作。鄧氏為元朝的中國學者。在西元一三○三年出的《禪源諸詮集都序》的前言中,鄧氏說至元十二年即西元一二七五年,元世祖忽必烈召集眾僧,向他們問禪宗的教理,帝師(即八思巴)和其他高僧根據《禪源諸詮集》(禪宗本源的解釋)這本書來回答元帝的問題。鄧氏更進一步說,「上意悅,命板行於世。」,這個早期的資料有些史學家很注意,但在日期和事件內容兩方面,該書的敘述含有一些錯誤,尤其當它宣稱八思巴和其他高僧依據《禪源諸詮集》這本書回答元帝的問題時。這點使人產生一個印象,即那些僧侶彼此之間沒有什麼異議或問題。
同書的另一篇序文,是賈汝舟所寫的。賈氏和鄧文原是同時代的人。賈氏稍為詳盡的重述相同的事實。他說先是至元十二年春正月,元世祖有一個清閒的時間,沒有繁重的任務在身,他在瓊華島,邀請帝師為伴。劉公(諡曰文貞)那時候也在場。因之元世祖召集學識淵博的老和尚,同他們問禪宗與佛教教理之間的衝突。已亡故的西菴法師,名贇,與其他諸人,總共八位,根據圭峰大師所著的《禪源詮》的原文回答元帝的問題,這使帝心大悅。後法師吩咐他的屬下印那本書、以便流通。
雖然賈汝舟重述日期和事件內容,但和鄧文原所寫的字比較一下,則他的敘述有若干確定的差異:以帝師為元帝之伴,因此不是被召集的眾僧中的一員。多了一個參加那次集會的人,即劉秉忠(一二一六~一二七四)命令印行《禪源詮》的不是元帝而是西菴法師。對該事件的日期,賈氏所敘述的也帶來問題。從藏文的資料得知帝師八思巴「西元一二七四年準備回西藏,元世祖決定送他一程。他陪他好幾個月,直到他們到達Amdo地帶Machu(黃河)的上流彎曲處。」中國官方資料元史證實了日期,它記載那年三月「帝師八思巴還西藏,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同樣地,劉秉忠於西元一二七四年九月二十日去世。所以不可能這兩位重要的傑出人物會出現於西元一二七五年的那次集會,如《禪源諸詮集》的兩篇序文所說的那樣。二篇序文互相矛盾的敘述,那件事發生日期的可疑問,對那件事的內容缺乏詳細的描寫,都使學者們不敢追問那件事。
有關元代禪僧與西藏喇嘛的辯論,在從倫傳中留了一個比較詳盡而且正確的記載。該傳中記至元九年即西元一二七二年,西菴法師被元帝召到皇宮,討論禪宗的教理。他根據圭峰大師(即宗密,七八○~八四一)所著《禪源詮》來講述這個題目。接著,他回答有關這個題目的問題。最後論到禪宗的公案。從倫傳以「拆辯抵暮」結束它對那件事的描述。這點證實了那次辯論的性質和重大。
因為從倫傳是那件事唯一的長篇記錄,所以值得討論出現於那次有辯論的問題。「什麼是禪?」是忽必烈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回答,引用了上面已說過的宗密所著的書禪源詮,原文如下:
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中華翻為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
對禪這個術語,這段文章提供了一個根本的定義,即它的梵文和中文翻譯。就這個術語的原文和中文翻譯而言,沒有什麼可爭論。
在印度佛教中,禪那的地位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進化。八正道中,第一個是「正見」,最後一個是「正定」。這或許表示禪那(Jhana)是精神生活的高峰。然而在教義演進的過程中,更多的變化發生。在巴利文經典的教義中,禪那的地位為智慧(Panna)所取代;又變成大乘六波羅蜜中的第五項。六祖惠能(六三八~七一三)首先辯說「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禪定與智慧不異的說法,或許對多數學者是一個文字的問題,但這種說法卻真的使禪宗更接近早期的佛教教義。換言之,禪宗對宗教的經驗比對這宗教文字或純理論的描述更感興趣。
一旦禪宗把禪那當做是禪定與智慧合一的一般術語,勢必更進一層斷言禪為絕對。從倫引用一些經文以證明這個斷言不誤。他敘述如下:
禪為萬德之源,故名法性,華嚴經說。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楞伽經說。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經說。
這段引文的第一句和禪源詮的原文不同。後者說「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華嚴經》稱「禪為萬德之源」,且為法性的同義字。
在那段敘述後,從倫對宗密所解釋的禪那的分類更加注意。他向蒙古統治者忽必烈說禪那有不同的層次。由淺而深,其層次如下:第一,外道的禪那,目的在於往生為更高級的種姓。第二,凡夫的禪那,為了生生世世獲得幸福愉快。第三,小乘的修行,以無我觀為目標。第四,大乘的禪那,為得二空即我空法空的智慧。第五,禪宗修行的禪那。
禪那的第五層次是禪宗,在此層次:
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是如來清淨禪,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
禪僧從倫在忽必烈和八思巴面前所提出來的關於禪那的定義、證得、分類,在他的聽眾中並沒有激起任何問題出來。元世祖把上面的敘述略過去,而問了禪宗其他方面的問題。忽必烈的第一個問題是有關禪宗內諦理與言詮之間的關係。他問「在先有問,皆言無說,汝今云何卻有說耶?」從倫法師回答,「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元世祖問,「何故理無言說?」這問題的答案包含兩部分。第一,從倫法師說,「理與神會」。神是不可測知的,而語言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工具。因此後者不能完全或充分地把前者表示出來。這個答案的第二部分是一個比論:
如人食蜜,若問蜜之色相,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
這個答案促成了從倫法師第一次和忽必烈的西藏帝師八思巴的間接辯論。元世祖轉向帝師,要他做一個批判。八思巴說:「此與教中甚深般若了無異也。」
八思巴沒有非議禪宗,反而恭維禪宗為甚深般若。這是很有意義的事。甚深般若是梵文gambhira-prajna Paramita的中文翻譯,這個詞常出現於般若部的經籍中。甚深般若被稱為「諸佛母」,為「諸菩薩摩訶薩母」,因它「能生諸佛」。甚深般若也被形容為「難思議」,「不可思議」。它是「非一非二,非三非四,亦非多。」它是「無價珍寶」,「無思慮」。它「無生無滅,無分別相」。換言之,它是佛教的絕對。因此它「無相無說」,「離名言」。八思巴好像用這些描述甚深般若的語辭,特別是它的不可說性,來稱讚禪宗。
帝師八思巴接著問禪宗祖師的公案。從倫法師選六祖的「心幡」公案做為答案。那個故事是
「時有風吹幡動。一僧曰動,一僧曰幡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帝師曰:「實風幡動,何名心動?」師曰:「一切唯心,萬法唯識,豈非心動耶?」
從倫傳於此結束辯論的故事。
我們不知道在辯論時所有被提出來討論的問題,但記錄雖然短,卻也還提到若干值得注意的問題。
首先西藏帝師賞識禪宗,反映了雙方的新發展。就中國的發展而論,頓漸悟理論之間的衝突,在宗密的著作中已被解決。雖然他的頓悟漸修的主張並未直接痛快地被禪僧所接受,但也沒有人反對它。而且他這個主張給予頓悟說以本體論的承認,即是一切眾生生來即秉賦有圓滿的佛性,這點滿足了禪宗自以為優於其他宗派的要求。藉漸修印證開悟的經驗和獲得,在阻止其他宗派非議禪宗這點上,也是有幫助的。換句話說,禪宗在第十三世紀時,是比前期更成熟豐富。同樣地,西藏的密宗也發展成熟。它不再只知附合印度佛教,卻以西藏人的創造力吸收消化它。這個新發展或許促使西藏人更能賞識禪宗,這種可能性由下面這個事實更可看出來,即禪宗與西藏密教兩者都是大乘的「激進」派。它們自然變成更容易了解和欣賞。
我們知道八思巴是屬於薩迦派(Sa—Skya—Pa)的。這派的主要教義,「顯然是源自瑜伽的唯識教」。這派認為「識是不二,無始、無常、無終、無妄想。」這種領悟當然是很接近禪宗的體證。
這派的教理強調「因」和「果」:
就「因」而論,它是自然之明;就「道」而論,賢哲藉著「開」「合」之法,應用無上瑜伽,先證明,後證空。以禪定得「果」後,此法在化身與明,空與法身合而為一時,達到極致。
當一個人達到這種境界時,「諸法僅顯現於心中,因心中不可能有二,一切相皆虛妄。」腦子裡記住這點,而回來重新審查禪僧從倫所做的解釋,「一切唯心、萬法唯識。」在這些方面,禪宗與密教的理論基礎與言詮是相當接近的。難怪八思巴對從倫這個解釋頗為賞識。
印度和中國的佛教僧侶八世紀在拉薩的辯論,在西藏佛教之歷史、哲學、和政治的研究上,很引人注意。雖然無疑的,印度和中國的佛教徒在拉薩是有過辯論,但對這次辯論的態度與重要性,學者之間頗有爭論。根據一派的學者,所謂中國與西藏僧侶之間的論戰,「是在西藏國王的面前舉行一次非常長的公開辯論(七九二~九四)而做決定。」蓮華戒(Kamalashila)「被西藏政府從印度請來」,做他們的代表,「在辯論結束時,蓮華戒被判贏得勝利。西藏人對這件事傳統的簡單敘述,其他學者有不同的意見。Yoshiro Imaeda是這些學者中最好的代表。小心研究不同的經文後,他說:「依據敦煌的中文和藏文資料,不得不這樣下結論:兩位大法師的會面非是史實,而是後代西藏史家所25553;造的稗史。」Imaeda所提出的證據如此令人信服,以致根特(Herbert Guenther)提議,「第八世紀那次辯論的故事必須完全重寫。」
有關前次禪宗與印度——西藏佛教的辯論的爭論,使我們引發另一個問題,即十三世紀的辯論,對上一次的辯論有什麼意義?八思巴對禪宗不懷敵意反而大加賞識的反應,好像更加強了Imaeda的結論。這個印象是依據下面這個事實而來的,即八思巴很了解中國與西藏之間的歷史關係。當他隨著他的伯父薩迦班24312;大(the Sakya Pandita)到蒙古朝廷時,他們「這一群人經過拉薩,在那裡年輕的八思巴出家,當了和尚,……在佛像前,第一次受戒,……被一位中國王子帶到西藏。」我們知道八思巴是西藏古代史的專家。有一本歷史書叫做西藏歷代國王系譜,傳說是他為的,這本書現在還存留於世。他對西藏古代史的確具有廣博的知識,從他和忽必烈的會話,他告訴這位蒙古皇帝有關西藏過去和中國的關係這件事,可進一步地加以證實。八思巴所說的那些都經過朝廷史官的核對與證實。
腦子裡記得這些背景,自然就會懷疑為什麼八思巴沒有說第八世紀那次辯論中,中國佛教被宣佈失敗。他若這樣說,將可能加強他的威勢,以及西藏佛教的優於中國佛教。八思巴不提第八世紀西藏密宗宣稱在辯論中獲得勝利,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在八思巴的時候,這段稗史尚未為人所知。若真是如此,則可推想這段稗史是在八思巴到元朝後才被杜撰出來的,並且由於他到元朝的成就而激起人造出這段稗史。
要言之,在第十三世紀中的七十五年代,中國禪僧與西藏喇嘛有過一次辯論。有關禪宗的歷史,性質,和範圍的問題都被問到。真理與其言詮的問題,以及公案的法則,也被提出來討論。西藏喇嘛八思巴就此題目,問了一些問題,並對答案表示賞識與恭維。一點反對也沒有。就歷史來說,這次中國禪僧與西藏喇嘛的辯論已是第二次。八思巴並未道及前一次的辯論,更加強了某些學者的看法,即西藏對上一次辯論的描述,為後代西藏史家編造出來的一段稗史。
編按:本文為作者之英文著作"The Encounter Between Ch、an and Tibetan Lamas at
Yuan Court" 許洋主譯
現代的學者都曉得,西元第八世紀中國和印度的佛教哲學家曾在拉薩辯論過。歷史和語言學家也都知道八思巴在元朝有崇高地位。但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間禪僧和八思巴在大都(北平)辯論一事,幾乎不為研究者所注意,實在是相當不平常。這件事或許是因發生在拉薩辯論之後,中國和西藏的佛教徒之間唯一有意義的辯論,因此它的重要性,在佛教史或佛教的比較研究史上,是不需要誇張的。由於學者還只留意前次的辯論,所以研究元代禪僧和西藏喇嘛的辯論也可能有助於瞭解上一次的辯論。
本論文的目的在於論述下列諸問題:第一,本論文將嘗試揭露元朝禪僧和西藏喇嘛辯論的事實和主題;第二,依照辯論來衡量禪和西藏佛教的發展。為了重視推究,本論文接著要把元朝那次辯論和第八世紀舉行的辯論併在一起討論。
最早提到元朝那次辯論的書是鄧文原的著作。鄧氏為元朝的中國學者。在西元一三○三年出的《禪源諸詮集都序》的前言中,鄧氏說至元十二年即西元一二七五年,元世祖忽必烈召集眾僧,向他們問禪宗的教理,帝師(即八思巴)和其他高僧根據《禪源諸詮集》(禪宗本源的解釋)這本書來回答元帝的問題。鄧氏更進一步說,「上意悅,命板行於世。」,這個早期的資料有些史學家很注意,但在日期和事件內容兩方面,該書的敘述含有一些錯誤,尤其當它宣稱八思巴和其他高僧依據《禪源諸詮集》這本書回答元帝的問題時。這點使人產生一個印象,即那些僧侶彼此之間沒有什麼異議或問題。
同書的另一篇序文,是賈汝舟所寫的。賈氏和鄧文原是同時代的人。賈氏稍為詳盡的重述相同的事實。他說先是至元十二年春正月,元世祖有一個清閒的時間,沒有繁重的任務在身,他在瓊華島,邀請帝師為伴。劉公(諡曰文貞)那時候也在場。因之元世祖召集學識淵博的老和尚,同他們問禪宗與佛教教理之間的衝突。已亡故的西菴法師,名贇,與其他諸人,總共八位,根據圭峰大師所著的《禪源詮》的原文回答元帝的問題,這使帝心大悅。後法師吩咐他的屬下印那本書、以便流通。
雖然賈汝舟重述日期和事件內容,但和鄧文原所寫的字比較一下,則他的敘述有若干確定的差異:以帝師為元帝之伴,因此不是被召集的眾僧中的一員。多了一個參加那次集會的人,即劉秉忠(一二一六~一二七四)命令印行《禪源詮》的不是元帝而是西菴法師。對該事件的日期,賈氏所敘述的也帶來問題。從藏文的資料得知帝師八思巴「西元一二七四年準備回西藏,元世祖決定送他一程。他陪他好幾個月,直到他們到達Amdo地帶Machu(黃河)的上流彎曲處。」中國官方資料元史證實了日期,它記載那年三月「帝師八思巴還西藏,乃以其弟亦憐真嗣焉。」,同樣地,劉秉忠於西元一二七四年九月二十日去世。所以不可能這兩位重要的傑出人物會出現於西元一二七五年的那次集會,如《禪源諸詮集》的兩篇序文所說的那樣。二篇序文互相矛盾的敘述,那件事發生日期的可疑問,對那件事的內容缺乏詳細的描寫,都使學者們不敢追問那件事。
有關元代禪僧與西藏喇嘛的辯論,在從倫傳中留了一個比較詳盡而且正確的記載。該傳中記至元九年即西元一二七二年,西菴法師被元帝召到皇宮,討論禪宗的教理。他根據圭峰大師(即宗密,七八○~八四一)所著《禪源詮》來講述這個題目。接著,他回答有關這個題目的問題。最後論到禪宗的公案。從倫傳以「拆辯抵暮」結束它對那件事的描述。這點證實了那次辯論的性質和重大。
因為從倫傳是那件事唯一的長篇記錄,所以值得討論出現於那次有辯論的問題。「什麼是禪?」是忽必烈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回答,引用了上面已說過的宗密所著的書禪源詮,原文如下:
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中華翻為思惟修。亦名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
對禪這個術語,這段文章提供了一個根本的定義,即它的梵文和中文翻譯。就這個術語的原文和中文翻譯而言,沒有什麼可爭論。
在印度佛教中,禪那的地位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進化。八正道中,第一個是「正見」,最後一個是「正定」。這或許表示禪那(Jhana)是精神生活的高峰。然而在教義演進的過程中,更多的變化發生。在巴利文經典的教義中,禪那的地位為智慧(Panna)所取代;又變成大乘六波羅蜜中的第五項。六祖惠能(六三八~七一三)首先辯說「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禪定與智慧不異的說法,或許對多數學者是一個文字的問題,但這種說法卻真的使禪宗更接近早期的佛教教義。換言之,禪宗對宗教的經驗比對這宗教文字或純理論的描述更感興趣。
一旦禪宗把禪那當做是禪定與智慧合一的一般術語,勢必更進一層斷言禪為絕對。從倫引用一些經文以證明這個斷言不誤。他敘述如下:
禪為萬德之源,故名法性,華嚴經說。亦是眾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楞伽經說。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經說。
這段引文的第一句和禪源詮的原文不同。後者說「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華嚴經》稱「禪為萬德之源」,且為法性的同義字。
在那段敘述後,從倫對宗密所解釋的禪那的分類更加注意。他向蒙古統治者忽必烈說禪那有不同的層次。由淺而深,其層次如下:第一,外道的禪那,目的在於往生為更高級的種姓。第二,凡夫的禪那,為了生生世世獲得幸福愉快。第三,小乘的修行,以無我觀為目標。第四,大乘的禪那,為得二空即我空法空的智慧。第五,禪宗修行的禪那。
禪那的第五層次是禪宗,在此層次:
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是如來清淨禪,達摩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
禪僧從倫在忽必烈和八思巴面前所提出來的關於禪那的定義、證得、分類,在他的聽眾中並沒有激起任何問題出來。元世祖把上面的敘述略過去,而問了禪宗其他方面的問題。忽必烈的第一個問題是有關禪宗內諦理與言詮之間的關係。他問「在先有問,皆言無說,汝今云何卻有說耶?」從倫法師回答,「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元世祖問,「何故理無言說?」這問題的答案包含兩部分。第一,從倫法師說,「理與神會」。神是不可測知的,而語言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工具。因此後者不能完全或充分地把前者表示出來。這個答案的第二部分是一個比論:
如人食蜜,若問蜜之色相,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
這個答案促成了從倫法師第一次和忽必烈的西藏帝師八思巴的間接辯論。元世祖轉向帝師,要他做一個批判。八思巴說:「此與教中甚深般若了無異也。」
八思巴沒有非議禪宗,反而恭維禪宗為甚深般若。這是很有意義的事。甚深般若是梵文gambhira-prajna Paramita的中文翻譯,這個詞常出現於般若部的經籍中。甚深般若被稱為「諸佛母」,為「諸菩薩摩訶薩母」,因它「能生諸佛」。甚深般若也被形容為「難思議」,「不可思議」。它是「非一非二,非三非四,亦非多。」它是「無價珍寶」,「無思慮」。它「無生無滅,無分別相」。換言之,它是佛教的絕對。因此它「無相無說」,「離名言」。八思巴好像用這些描述甚深般若的語辭,特別是它的不可說性,來稱讚禪宗。
帝師八思巴接著問禪宗祖師的公案。從倫法師選六祖的「心幡」公案做為答案。那個故事是
「時有風吹幡動。一僧曰動,一僧曰幡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帝師曰:「實風幡動,何名心動?」師曰:「一切唯心,萬法唯識,豈非心動耶?」
從倫傳於此結束辯論的故事。
我們不知道在辯論時所有被提出來討論的問題,但記錄雖然短,卻也還提到若干值得注意的問題。
首先西藏帝師賞識禪宗,反映了雙方的新發展。就中國的發展而論,頓漸悟理論之間的衝突,在宗密的著作中已被解決。雖然他的頓悟漸修的主張並未直接痛快地被禪僧所接受,但也沒有人反對它。而且他這個主張給予頓悟說以本體論的承認,即是一切眾生生來即秉賦有圓滿的佛性,這點滿足了禪宗自以為優於其他宗派的要求。藉漸修印證開悟的經驗和獲得,在阻止其他宗派非議禪宗這點上,也是有幫助的。換句話說,禪宗在第十三世紀時,是比前期更成熟豐富。同樣地,西藏的密宗也發展成熟。它不再只知附合印度佛教,卻以西藏人的創造力吸收消化它。這個新發展或許促使西藏人更能賞識禪宗,這種可能性由下面這個事實更可看出來,即禪宗與西藏密教兩者都是大乘的「激進」派。它們自然變成更容易了解和欣賞。
我們知道八思巴是屬於薩迦派(Sa—Skya—Pa)的。這派的主要教義,「顯然是源自瑜伽的唯識教」。這派認為「識是不二,無始、無常、無終、無妄想。」這種領悟當然是很接近禪宗的體證。
這派的教理強調「因」和「果」:
就「因」而論,它是自然之明;就「道」而論,賢哲藉著「開」「合」之法,應用無上瑜伽,先證明,後證空。以禪定得「果」後,此法在化身與明,空與法身合而為一時,達到極致。
當一個人達到這種境界時,「諸法僅顯現於心中,因心中不可能有二,一切相皆虛妄。」腦子裡記住這點,而回來重新審查禪僧從倫所做的解釋,「一切唯心、萬法唯識。」在這些方面,禪宗與密教的理論基礎與言詮是相當接近的。難怪八思巴對從倫這個解釋頗為賞識。
印度和中國的佛教僧侶八世紀在拉薩的辯論,在西藏佛教之歷史、哲學、和政治的研究上,很引人注意。雖然無疑的,印度和中國的佛教徒在拉薩是有過辯論,但對這次辯論的態度與重要性,學者之間頗有爭論。根據一派的學者,所謂中國與西藏僧侶之間的論戰,「是在西藏國王的面前舉行一次非常長的公開辯論(七九二~九四)而做決定。」蓮華戒(Kamalashila)「被西藏政府從印度請來」,做他們的代表,「在辯論結束時,蓮華戒被判贏得勝利。西藏人對這件事傳統的簡單敘述,其他學者有不同的意見。Yoshiro Imaeda是這些學者中最好的代表。小心研究不同的經文後,他說:「依據敦煌的中文和藏文資料,不得不這樣下結論:兩位大法師的會面非是史實,而是後代西藏史家所25553;造的稗史。」Imaeda所提出的證據如此令人信服,以致根特(Herbert Guenther)提議,「第八世紀那次辯論的故事必須完全重寫。」
有關前次禪宗與印度——西藏佛教的辯論的爭論,使我們引發另一個問題,即十三世紀的辯論,對上一次的辯論有什麼意義?八思巴對禪宗不懷敵意反而大加賞識的反應,好像更加強了Imaeda的結論。這個印象是依據下面這個事實而來的,即八思巴很了解中國與西藏之間的歷史關係。當他隨著他的伯父薩迦班24312;大(the Sakya Pandita)到蒙古朝廷時,他們「這一群人經過拉薩,在那裡年輕的八思巴出家,當了和尚,……在佛像前,第一次受戒,……被一位中國王子帶到西藏。」我們知道八思巴是西藏古代史的專家。有一本歷史書叫做西藏歷代國王系譜,傳說是他為的,這本書現在還存留於世。他對西藏古代史的確具有廣博的知識,從他和忽必烈的會話,他告訴這位蒙古皇帝有關西藏過去和中國的關係這件事,可進一步地加以證實。八思巴所說的那些都經過朝廷史官的核對與證實。
腦子裡記得這些背景,自然就會懷疑為什麼八思巴沒有說第八世紀那次辯論中,中國佛教被宣佈失敗。他若這樣說,將可能加強他的威勢,以及西藏佛教的優於中國佛教。八思巴不提第八世紀西藏密宗宣稱在辯論中獲得勝利,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在八思巴的時候,這段稗史尚未為人所知。若真是如此,則可推想這段稗史是在八思巴到元朝後才被杜撰出來的,並且由於他到元朝的成就而激起人造出這段稗史。
要言之,在第十三世紀中的七十五年代,中國禪僧與西藏喇嘛有過一次辯論。有關禪宗的歷史,性質,和範圍的問題都被問到。真理與其言詮的問題,以及公案的法則,也被提出來討論。西藏喇嘛八思巴就此題目,問了一些問題,並對答案表示賞識與恭維。一點反對也沒有。就歷史來說,這次中國禪僧與西藏喇嘛的辯論已是第二次。八思巴並未道及前一次的辯論,更加強了某些學者的看法,即西藏對上一次辯論的描述,為後代西藏史家編造出來的一段稗史。
編按:本文為作者之英文著作"The Encounter Between Ch、an and Tibetan Lamas at
Yuan Court" 許洋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