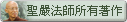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無悔前行:佛教藝術澱積者釋寬謙口述史
作者:釋寬謙
出版社:台灣商務
出版日期:2020年11月05日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23*17*1.8cm
商品編號:1150720521
ISBN:9789570532913
定價:NT$430
會員價:NT$366 (85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第一章 跨海溯源楊氏家族
↑TOP
臺灣宜蘭是我的家鄉,但我在臺北市出生、長大、就學,小時候常常隨著外婆往返宜蘭、臺北之間。一路陪伴我長大的是家父塑造的佛像、外婆常去的宜蘭念佛會,以及家族濃厚的親情。
大陸、臺灣,楊家與兩地的因緣
先祖仗義搭救陌生女子牽起姻緣
家父楊英風的朋友林今開先生,著有《狂人百相》,筆調活潑,很有歷史概念。一九九○年家父在北京生了一場大病,讓林先生很緊張,家父病癒以後,林先生發心要替我們尋找族譜。
林先生前往中國大陸探尋,從宜蘭追到泉州,發現故居有個地方名為「佛壇」,在當地找了許多資料,寫成《八千里路雲和月》,自家父上溯到祖父、再更上幾代,紀錄我們家族是如何來到臺灣,可惜來不及出版,他就過世了。二○○二至二○一一年,我們與新竹交通大學合作出版三十冊的《楊英風全集》,將此書收入第二十八冊。我很佩服他一一溯源查詢的精神,他說歷史像影印機一樣,自然會複製到下一代。我出家的時候,以為家族內沒有出家人,卻查到楊家在前幾代就有人在「佛壇」出家。
根據林先生查訪的家族故事,楊家第一代先祖一直想來臺灣發展,但苦無機會,某天在家鄉見到有位女子被人非禮,出手搭救,不慎將非禮女子之人打倒,驚動鄉人,於是就匆匆忙忙逃離大陸到臺灣。這女子出自文人家庭,因為有此難堪的遭遇,在家鄉很難立足,尋思託身當時搭救她的人,不斷打聽下才得知恩人已去了臺灣,女子立刻想方設法來臺。當時單身女子是很難渡海到臺灣,她就將自己裝在雞籠裡,當成貨品隨船到臺灣來,在臺灣上岸後,熱心人士把她直接送到先祖家裡。
這位女子和先祖結婚後,從此相夫教子,而繡花、繪畫都是她的專長;先祖乃是種田人家,閒暇時幫人蓋房子,先祖母就協助他點綴裝飾屋面。我想手藝基因就是這樣遺傳到家父身上。家父是來臺的第七代,我不曉得林先生如何訪談得知這樣的故事,但確實有根有據,也可見家父的藝術天分其來有自。
根據家父的紀錄:「祖先楊聘,於一七二九年,清朝雍正年間,從福建遠渡到臺灣,與宜蘭開拓之父吳沙,共同在新世界注入了新開拓者的熱情。」將近兩百年後,祖父楊朝木同樣擁有先祖的冒險精神,在亞洲大動亂的一九三○年代,帶著祖母陳鴛鴦與孩子,如鮭魚返鄉般前進中國發展。
祖父母赴中國經商一別三十年
祖父是開創型的性格,到了中國大陸先在上海經營碾米廠,接著去北京開戲院,後來更遠赴東北發展。一九四九年來不及返回臺灣,滯留於大陸,直到一九七九年才離開中國大陸回到臺灣,但依然抱持創業理想,處處尋找商機,不知老之將至。
祖父母在中國的事業曾經臻至巔峰,他們度過了中國最後的精華時代,過得很富裕,家裡佣人不知凡幾,倆人生了三兄弟,都非常文靜,親友都覺得家裡似乎養了三位千金,不過祖母規定他們在家裡一定要講閩南語。
祖母與外婆是姊妹。外婆是三姊,名為陳水鴨;祖母排行第四,原名鴛鴦,後來改叫瀕洲。祖母是現代女性,她不肯纏足;而外婆則認命纏足,是內向的傳統女子,沒有讀書,守在宜蘭。祖母出外讀書,到上海、東北,和祖父在北京經營戲院。外婆擔心祖父母到了中國大陸發展事業不回家鄉,要求將他們的大兒子,也就是家父留在故鄉,由外婆照顧。因此,祖母於一九二六年在臺灣生下了家父後,便跟隨祖父去中國發展事業,隔一、兩年才回來宜蘭探望親戚,尤其是兒子。這在當時落後的宜蘭,總會引起一陣騷動,家父看著自己的母親,穿著旗袍裝點著亮片,就彷彿從天邊飛回來的一隻「鳳凰」。
每當又要離去,祖母就跟兒子(家父)指著天空的月亮:「阿母欲去的所在,你會當看著同一個月娘!咱倆人看著的是同一個月娘喔!阿母無論何時,都會佇月娘看著阿風你喲!」
從那天起,每當夜深人靜時,家父就獨自走到院子裡,目不轉睛地凝視著月亮。似乎在月亮中,看到了阿母攬鏡梳髮的形影,她身穿高雅、優美的旗袍身形,彷彿月娘派來的使者。家父腦海中重疊的影像,不是別的,而是浮現於月亮的母親背影,這正是家父「鳳凰系列」的創作原形。月亮也引導家父的眼界關注到宇宙天際,得以將沉緬於思念母親的煎熬及狹隘心態之苦,轉為對大自然的大愛,因而能從拘泥中解放、並且展現化煩惱為自在的特質。母親的永恆形象——月中的優雅身影,牽引家父的創作走向大愛的「宇宙真理」。
等到家父小學畢業,祖父母堅持要帶他到北京受教育,外婆又擔心他們不再回來,遂將自己的女兒李定,許配給妹妹的兒子(家父)。家父到中國讀書後,因為外公生病,受命回來結婚沖喜,這一次回來臺灣,就與祖父母睽違三十年,造化真是難以捉摸。
臺灣俗諺:「鴛鴦水鴨倆相隨。」但人間戰亂離散了這對姊妹,死生不能再見。祖母與外婆生離死別的這一段歲月,歷經了日治、抗戰與國共分裂,祖父母羈留大陸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想辦法離開中國。戒嚴期間依照規定,大陸居民不能直接回來臺灣,要在第三地住滿十年,幸好二叔楊景天住在美國,祖父母先到美國依親,家父奔走聯繫處理後,簽下保證祖父母回臺灣後不再離開臺灣的切結書,方得以讓二老提前歸來故鄉。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一別三十年,親人重聚,恍如隔世。祖父母從美國回來時,我們整個家族總動員,租了一輛遊覽車去機場迎接兩位老人家。
但那年仲夏,外婆剛剛過世,家裡設有靈堂,擔心祖母見此光景,會受到巨大的衝擊,所以先安排他們暫住表哥家。然而,手足親情的魂縈夢繫,讓祖母到了三更半夜依然睡不著,要求我們立即帶她去臺南看姊姊。這時我們不得不講出真相,一聽到姊姊已經過世,祖母慟心地昏厥過去。等了三十年,就只差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生死契闊,就此錯失,真是令人扼腕,人間至情悲戚莫過於此!
外婆、祖母這一對姊妹,是家父生命中重要的女性,也是家父創作的泉源與推手。外婆更於家父母結婚後,協助家母帶孫子、煮三餐、料理家務。
祖母回到臺灣之後,於一九八三年過世。家父與祖母一生聚少離多,但緣淺情深,童年時想念在北京的母親,只能仰望月亮的柔輝,代替母親的溫暖擁抱。祖母過世,我再度萌生出家念頭,兩相衝擊,家父遂創作了〈分合隨緣〉,呈現出對生離死別的深沉感悟。〈分合隨緣〉是由兩件大作品構成,可以成為一組,也可以獨立分開為兩件。作品體現法義,又充滿感動力量,動態的分合構件如飛碟般的斜鏡面,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彷彿道盡了楊家母子、鴛鴦水鴨姊妹此世情緣的生滅,以及父女相聚別離的去來,思念深遠的悠悠。
家父的身教與言教
家父回臺灣結婚、白手起家,祖父母在北京的產業,完全無法帶回臺灣,大陸變色後,音訊全無。一九四七至一九六○年,正是臺灣經濟窮困的年代,雖然「豐年社」雜誌美編的工作薪水不錯,但是一家九口,再加上阿姨的孩子們亦得挹注教育費用,經濟並不寬裕。然而一九六一年家父為日月潭教師會館完成的大浮雕創作,促使他辭去待遇優渥的工作,發願當一位專業藝術家。
家母不擅理財,對家庭經濟的協助不大,家事還得外婆幫忙。家中一直沒有工作室,雖然處在經濟拮据的惡劣環境中,但家父總是努力不懈、克服困難陸續完成大大小小的藝術作品。當時家父最好的工作室,就是建築製圖桌,在一張張的方眼紙上,完成原創作品的構思。
家父一九四○年代曾經在北京輔仁大學讀書,輔仁大學一九六一年於臺北復校後,于斌樞機主教希望家父以校友的身分去羅馬,代表學校向教皇致謝,感恩教皇協助復校。可是家中經濟不寬裕,怎有餘力去羅馬,不過于斌樞機主教說,只要有心去自然有辦法。很巧,當時菲律賓僑領請家父為他塑造肖像並翻鑄為銅像,這筆如及時雨般的收入,解決了家中經濟問題,父親順利前往羅馬。因緣時節不是巧合,而是點滴累積而來。
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家父在羅馬,而我正在讀小學的階段。這三年我們常常寫信給他,先在黑板上寫:「爸爸,我們想念您!」然後拍一張照片,寄去給他。記得家父出國時,在飛機上寫的明信片中提醒當年還是小學生的我,要多吃青菜,字裡行間盡是溫暖的叮嚀。孩子的想念、父親的慈愛在《楊英風全集》的書信篇處處可見,實屬傳統家庭中少見的「暖男」。出家前的我可是「滴菜不沾」,所以當我決定出家時,跌破許多人的眼鏡!
親情與藝術的澆灌
家父母結婚後,搬到臺北居住,曾經住過齊東街,後來搬到重慶南路。齊東街有很多日式宿舍,有一處立為「楊英風故居」,不過現在已經找不到了。家父的三姨就是我外婆,家族親戚眾多,家父、家母比其他親戚早到臺北,所以宜蘭親戚到臺北就先住我家,要買房子也都先跟家母借款,當時父母都還沒想到為自己買房子。家父既是創作的藝術家,更是家族的照顧者、接濟者,同時是無比孝順的長子。
初識佛法的來由
我有一個阿姨叫李邁,她家就住在宜蘭雷音寺的斜對面,外婆與阿姨都會參加雷音寺的共修會。繞佛時,外婆常常把我背在背上,如此一來,我的視角就比一般人高,眼睛看著大家繞佛,耳朵聽到阿彌陀佛的佛號,綿綿不斷,佛號繞梁三日不絕於耳。那時候我才三、四歲,但印象非常深刻,鮮明的畫面與聲音直到現在還是難以忘懷。
外婆纏小腳,膝蓋與腳力都不夠強健,因為力氣不大,繞佛時為了背起我,都是先把我拽進水槽上,再藉由水槽的高度將我背到她的背上。我們一老一少,在佛堂裡留下溫馨畫面,外婆必然不知道當年這樣一拽、一抱、一背、一繞,讓我日後與如來家業形影不離。外婆橋、外婆橋,是帶我通往寺院的一座橋。
因為外婆是虔誠的佛教徒,又有一位會塑造佛像的女婿,也一直有供養寺廟佛像的心願,所以小時候我常常見到家父與出家法師往來。例如法源講寺的覺心法師、法濟寺的印心法師,他們兩位是師兄弟,當時家父正為這兩座寺院塑造佛菩薩像。六、七歲的時候,我就常在法源講寺、法濟寺之間來來去去。家父工作時,我們就穿梭在佛像、菩薩像間,大佛彷彿是我們的大玩伴,我們常常坐在大佛的腿上,摸一摸佛手,或是藏身在佛背後,玩起捉迷藏。佛菩薩尊像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和藹親切的大朋友,更有很深的感情,也因為法源講寺有家父塑造的佛像,而成為我出家寺院的首選,因為眼前的佛菩薩像,就彷彿是家父陪伴在我的身邊,加上覺心法師又是家父的好友,很自然的就成為我的剃度師父。
爽朗大膽的本性
年尾出生的我,依規定要晚一年入學,家母只好先送我去就讀幼稚園。家兄奉琛唸國語實小,順理成章我應該要讀國語實小附設幼稚園,但是我堅持不要讀這間。無可奈何之下,家母只好帶著我到處找幼稚園。當時總統府後面有一間公務人員子女就讀的貴族學校——靜心幼稚園,我一看立即就說:「我要讀這一間。」然而,從南海路到博愛路交界的貴陽街是一段不算短的距離,上下課是需要接送的,但家母仍將我送到這裡讀書,由此可見,家父母對孩子的尊重。我常說我很溫柔,但是很堅持,而且從小就展現了這樣的特質
就讀幼稚園期間,常常由家父騎著單車載我去上學,家父吹著口哨,我就坐在前方橫桿上的小藤椅,迎著風看東看西,當時重慶南路都是田野風光。如今高樓臨立,歲月更迭,滄海桑田,已非昔日。
有一段時間家父和他的學生們去日月潭工作,改由家母接送。有一天放學,我一直等不到家母來接我,眼看著一個個小朋友都回家了,牆上只剩下我的名牌卡,左看右盼,依然等不到人,我就拿著卡片去找門房,指著卡片上的住家地址,請他幫我叫一輛三輪車載我回家。就這樣,我一個人坐著三輪車,好像坐在又寬又深的沙發上,路上很顛簸,我身體太小,伸手搆不到兩邊的扶手,但我一點也不緊張,反而有自由自在的感覺。一路上搖搖晃晃地經過總統府、法院、自由之家,最後回到南海路的家。一到家,家母一臉驚訝地說:「妳怎麼這麼厲害!會自己回來。」這一件事,讓我充滿信心與歡喜。
當時家父安排家兄跟許常惠音樂家學小提琴,由住在家裡的國立藝專學生周義雄負責接送。我常常看著家兄哭著出門,又哭著回來,很不情願去學琴,倒是我非常好奇,於是提議陪家兄去學琴,當我學出了興趣時,家兄卻堅持不肯去上課,讓我也沒機會繼續學習,因此拉小提琴一直是我未完成的美夢。
幼稚園畢業,回到原來的學區國語實小就讀,學區中以外省小孩居多,所以我的國語發音還不錯。記得當時常常有很多外國人坐在教室後面,跟著我們一起上國語課,大家一起玩,國語就在遊戲當中學起來了。國語的讀音跟閩南語全然不同,例如國語ㄥ和ㄣ的音要分清楚,該不該用唇音,像「陳」與「程」就不一樣,還有我們臺灣人對ㄈ跟ㄏ也常搞不清楚。
當時除了國語實小,還有北師附小、女師附小,這三所學校有點像姐妹校。尤其國語實小,從來不受升學壓力的影響,並沒有補習,全方位五育都沒缺少,在我們那個時代,學校不惡補是很難的,國語實小實施正常教學,美術、音樂都沒忽略,至今我還是覺得國語實小最好。國語實小與建國中學只有一牆之隔,我們打躲避球、打籃球,打著打著常常會把球丟到建中校園內。記得讀小學三年級到六年級時,下課後還會走到建國中學老師宿舍區,與一位音樂老師學鋼琴呢!
小學畢業那年,因為小提琴的夢還未了,我很勇敢的去找許常惠老師,執意請他幫忙買了一把小提琴,他當時已經不教小孩子拉琴,就把我交給他的新婚夫人教導,我又認真學了一段時間,終於認清自己不是音樂家的料,才總算放棄不學。自己雖當不成演奏家,但還是可以成為一位欣賞者。
家父有一位學生李正義,在國立藝專畢業後,進入功學社工作,因此贈送許多音樂會入場券給我們,我常常一個人搭著○東公車到終點站國際學舍,聆聽音樂會。當時的國際學舍算是位處臺北市的邊緣地帶,記得一到晚上就一片漆黑,我依然樂於前往欣賞音樂。
大陸、臺灣,楊家與兩地的因緣
先祖仗義搭救陌生女子牽起姻緣
家父楊英風的朋友林今開先生,著有《狂人百相》,筆調活潑,很有歷史概念。一九九○年家父在北京生了一場大病,讓林先生很緊張,家父病癒以後,林先生發心要替我們尋找族譜。
林先生前往中國大陸探尋,從宜蘭追到泉州,發現故居有個地方名為「佛壇」,在當地找了許多資料,寫成《八千里路雲和月》,自家父上溯到祖父、再更上幾代,紀錄我們家族是如何來到臺灣,可惜來不及出版,他就過世了。二○○二至二○一一年,我們與新竹交通大學合作出版三十冊的《楊英風全集》,將此書收入第二十八冊。我很佩服他一一溯源查詢的精神,他說歷史像影印機一樣,自然會複製到下一代。我出家的時候,以為家族內沒有出家人,卻查到楊家在前幾代就有人在「佛壇」出家。
根據林先生查訪的家族故事,楊家第一代先祖一直想來臺灣發展,但苦無機會,某天在家鄉見到有位女子被人非禮,出手搭救,不慎將非禮女子之人打倒,驚動鄉人,於是就匆匆忙忙逃離大陸到臺灣。這女子出自文人家庭,因為有此難堪的遭遇,在家鄉很難立足,尋思託身當時搭救她的人,不斷打聽下才得知恩人已去了臺灣,女子立刻想方設法來臺。當時單身女子是很難渡海到臺灣,她就將自己裝在雞籠裡,當成貨品隨船到臺灣來,在臺灣上岸後,熱心人士把她直接送到先祖家裡。
這位女子和先祖結婚後,從此相夫教子,而繡花、繪畫都是她的專長;先祖乃是種田人家,閒暇時幫人蓋房子,先祖母就協助他點綴裝飾屋面。我想手藝基因就是這樣遺傳到家父身上。家父是來臺的第七代,我不曉得林先生如何訪談得知這樣的故事,但確實有根有據,也可見家父的藝術天分其來有自。
根據家父的紀錄:「祖先楊聘,於一七二九年,清朝雍正年間,從福建遠渡到臺灣,與宜蘭開拓之父吳沙,共同在新世界注入了新開拓者的熱情。」將近兩百年後,祖父楊朝木同樣擁有先祖的冒險精神,在亞洲大動亂的一九三○年代,帶著祖母陳鴛鴦與孩子,如鮭魚返鄉般前進中國發展。
祖父母赴中國經商一別三十年
祖父是開創型的性格,到了中國大陸先在上海經營碾米廠,接著去北京開戲院,後來更遠赴東北發展。一九四九年來不及返回臺灣,滯留於大陸,直到一九七九年才離開中國大陸回到臺灣,但依然抱持創業理想,處處尋找商機,不知老之將至。
祖父母在中國的事業曾經臻至巔峰,他們度過了中國最後的精華時代,過得很富裕,家裡佣人不知凡幾,倆人生了三兄弟,都非常文靜,親友都覺得家裡似乎養了三位千金,不過祖母規定他們在家裡一定要講閩南語。
祖母與外婆是姊妹。外婆是三姊,名為陳水鴨;祖母排行第四,原名鴛鴦,後來改叫瀕洲。祖母是現代女性,她不肯纏足;而外婆則認命纏足,是內向的傳統女子,沒有讀書,守在宜蘭。祖母出外讀書,到上海、東北,和祖父在北京經營戲院。外婆擔心祖父母到了中國大陸發展事業不回家鄉,要求將他們的大兒子,也就是家父留在故鄉,由外婆照顧。因此,祖母於一九二六年在臺灣生下了家父後,便跟隨祖父去中國發展事業,隔一、兩年才回來宜蘭探望親戚,尤其是兒子。這在當時落後的宜蘭,總會引起一陣騷動,家父看著自己的母親,穿著旗袍裝點著亮片,就彷彿從天邊飛回來的一隻「鳳凰」。
每當又要離去,祖母就跟兒子(家父)指著天空的月亮:「阿母欲去的所在,你會當看著同一個月娘!咱倆人看著的是同一個月娘喔!阿母無論何時,都會佇月娘看著阿風你喲!」
從那天起,每當夜深人靜時,家父就獨自走到院子裡,目不轉睛地凝視著月亮。似乎在月亮中,看到了阿母攬鏡梳髮的形影,她身穿高雅、優美的旗袍身形,彷彿月娘派來的使者。家父腦海中重疊的影像,不是別的,而是浮現於月亮的母親背影,這正是家父「鳳凰系列」的創作原形。月亮也引導家父的眼界關注到宇宙天際,得以將沉緬於思念母親的煎熬及狹隘心態之苦,轉為對大自然的大愛,因而能從拘泥中解放、並且展現化煩惱為自在的特質。母親的永恆形象——月中的優雅身影,牽引家父的創作走向大愛的「宇宙真理」。
等到家父小學畢業,祖父母堅持要帶他到北京受教育,外婆又擔心他們不再回來,遂將自己的女兒李定,許配給妹妹的兒子(家父)。家父到中國讀書後,因為外公生病,受命回來結婚沖喜,這一次回來臺灣,就與祖父母睽違三十年,造化真是難以捉摸。
臺灣俗諺:「鴛鴦水鴨倆相隨。」但人間戰亂離散了這對姊妹,死生不能再見。祖母與外婆生離死別的這一段歲月,歷經了日治、抗戰與國共分裂,祖父母羈留大陸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想辦法離開中國。戒嚴期間依照規定,大陸居民不能直接回來臺灣,要在第三地住滿十年,幸好二叔楊景天住在美國,祖父母先到美國依親,家父奔走聯繫處理後,簽下保證祖父母回臺灣後不再離開臺灣的切結書,方得以讓二老提前歸來故鄉。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一別三十年,親人重聚,恍如隔世。祖父母從美國回來時,我們整個家族總動員,租了一輛遊覽車去機場迎接兩位老人家。
但那年仲夏,外婆剛剛過世,家裡設有靈堂,擔心祖母見此光景,會受到巨大的衝擊,所以先安排他們暫住表哥家。然而,手足親情的魂縈夢繫,讓祖母到了三更半夜依然睡不著,要求我們立即帶她去臺南看姊姊。這時我們不得不講出真相,一聽到姊姊已經過世,祖母慟心地昏厥過去。等了三十年,就只差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生死契闊,就此錯失,真是令人扼腕,人間至情悲戚莫過於此!
外婆、祖母這一對姊妹,是家父生命中重要的女性,也是家父創作的泉源與推手。外婆更於家父母結婚後,協助家母帶孫子、煮三餐、料理家務。
祖母回到臺灣之後,於一九八三年過世。家父與祖母一生聚少離多,但緣淺情深,童年時想念在北京的母親,只能仰望月亮的柔輝,代替母親的溫暖擁抱。祖母過世,我再度萌生出家念頭,兩相衝擊,家父遂創作了〈分合隨緣〉,呈現出對生離死別的深沉感悟。〈分合隨緣〉是由兩件大作品構成,可以成為一組,也可以獨立分開為兩件。作品體現法義,又充滿感動力量,動態的分合構件如飛碟般的斜鏡面,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彷彿道盡了楊家母子、鴛鴦水鴨姊妹此世情緣的生滅,以及父女相聚別離的去來,思念深遠的悠悠。
家父的身教與言教
家父回臺灣結婚、白手起家,祖父母在北京的產業,完全無法帶回臺灣,大陸變色後,音訊全無。一九四七至一九六○年,正是臺灣經濟窮困的年代,雖然「豐年社」雜誌美編的工作薪水不錯,但是一家九口,再加上阿姨的孩子們亦得挹注教育費用,經濟並不寬裕。然而一九六一年家父為日月潭教師會館完成的大浮雕創作,促使他辭去待遇優渥的工作,發願當一位專業藝術家。
家母不擅理財,對家庭經濟的協助不大,家事還得外婆幫忙。家中一直沒有工作室,雖然處在經濟拮据的惡劣環境中,但家父總是努力不懈、克服困難陸續完成大大小小的藝術作品。當時家父最好的工作室,就是建築製圖桌,在一張張的方眼紙上,完成原創作品的構思。
家父一九四○年代曾經在北京輔仁大學讀書,輔仁大學一九六一年於臺北復校後,于斌樞機主教希望家父以校友的身分去羅馬,代表學校向教皇致謝,感恩教皇協助復校。可是家中經濟不寬裕,怎有餘力去羅馬,不過于斌樞機主教說,只要有心去自然有辦法。很巧,當時菲律賓僑領請家父為他塑造肖像並翻鑄為銅像,這筆如及時雨般的收入,解決了家中經濟問題,父親順利前往羅馬。因緣時節不是巧合,而是點滴累積而來。
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六年家父在羅馬,而我正在讀小學的階段。這三年我們常常寫信給他,先在黑板上寫:「爸爸,我們想念您!」然後拍一張照片,寄去給他。記得家父出國時,在飛機上寫的明信片中提醒當年還是小學生的我,要多吃青菜,字裡行間盡是溫暖的叮嚀。孩子的想念、父親的慈愛在《楊英風全集》的書信篇處處可見,實屬傳統家庭中少見的「暖男」。出家前的我可是「滴菜不沾」,所以當我決定出家時,跌破許多人的眼鏡!
親情與藝術的澆灌
家父母結婚後,搬到臺北居住,曾經住過齊東街,後來搬到重慶南路。齊東街有很多日式宿舍,有一處立為「楊英風故居」,不過現在已經找不到了。家父的三姨就是我外婆,家族親戚眾多,家父、家母比其他親戚早到臺北,所以宜蘭親戚到臺北就先住我家,要買房子也都先跟家母借款,當時父母都還沒想到為自己買房子。家父既是創作的藝術家,更是家族的照顧者、接濟者,同時是無比孝順的長子。
初識佛法的來由
我有一個阿姨叫李邁,她家就住在宜蘭雷音寺的斜對面,外婆與阿姨都會參加雷音寺的共修會。繞佛時,外婆常常把我背在背上,如此一來,我的視角就比一般人高,眼睛看著大家繞佛,耳朵聽到阿彌陀佛的佛號,綿綿不斷,佛號繞梁三日不絕於耳。那時候我才三、四歲,但印象非常深刻,鮮明的畫面與聲音直到現在還是難以忘懷。
外婆纏小腳,膝蓋與腳力都不夠強健,因為力氣不大,繞佛時為了背起我,都是先把我拽進水槽上,再藉由水槽的高度將我背到她的背上。我們一老一少,在佛堂裡留下溫馨畫面,外婆必然不知道當年這樣一拽、一抱、一背、一繞,讓我日後與如來家業形影不離。外婆橋、外婆橋,是帶我通往寺院的一座橋。
因為外婆是虔誠的佛教徒,又有一位會塑造佛像的女婿,也一直有供養寺廟佛像的心願,所以小時候我常常見到家父與出家法師往來。例如法源講寺的覺心法師、法濟寺的印心法師,他們兩位是師兄弟,當時家父正為這兩座寺院塑造佛菩薩像。六、七歲的時候,我就常在法源講寺、法濟寺之間來來去去。家父工作時,我們就穿梭在佛像、菩薩像間,大佛彷彿是我們的大玩伴,我們常常坐在大佛的腿上,摸一摸佛手,或是藏身在佛背後,玩起捉迷藏。佛菩薩尊像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和藹親切的大朋友,更有很深的感情,也因為法源講寺有家父塑造的佛像,而成為我出家寺院的首選,因為眼前的佛菩薩像,就彷彿是家父陪伴在我的身邊,加上覺心法師又是家父的好友,很自然的就成為我的剃度師父。
爽朗大膽的本性
年尾出生的我,依規定要晚一年入學,家母只好先送我去就讀幼稚園。家兄奉琛唸國語實小,順理成章我應該要讀國語實小附設幼稚園,但是我堅持不要讀這間。無可奈何之下,家母只好帶著我到處找幼稚園。當時總統府後面有一間公務人員子女就讀的貴族學校——靜心幼稚園,我一看立即就說:「我要讀這一間。」然而,從南海路到博愛路交界的貴陽街是一段不算短的距離,上下課是需要接送的,但家母仍將我送到這裡讀書,由此可見,家父母對孩子的尊重。我常說我很溫柔,但是很堅持,而且從小就展現了這樣的特質
就讀幼稚園期間,常常由家父騎著單車載我去上學,家父吹著口哨,我就坐在前方橫桿上的小藤椅,迎著風看東看西,當時重慶南路都是田野風光。如今高樓臨立,歲月更迭,滄海桑田,已非昔日。
有一段時間家父和他的學生們去日月潭工作,改由家母接送。有一天放學,我一直等不到家母來接我,眼看著一個個小朋友都回家了,牆上只剩下我的名牌卡,左看右盼,依然等不到人,我就拿著卡片去找門房,指著卡片上的住家地址,請他幫我叫一輛三輪車載我回家。就這樣,我一個人坐著三輪車,好像坐在又寬又深的沙發上,路上很顛簸,我身體太小,伸手搆不到兩邊的扶手,但我一點也不緊張,反而有自由自在的感覺。一路上搖搖晃晃地經過總統府、法院、自由之家,最後回到南海路的家。一到家,家母一臉驚訝地說:「妳怎麼這麼厲害!會自己回來。」這一件事,讓我充滿信心與歡喜。
當時家父安排家兄跟許常惠音樂家學小提琴,由住在家裡的國立藝專學生周義雄負責接送。我常常看著家兄哭著出門,又哭著回來,很不情願去學琴,倒是我非常好奇,於是提議陪家兄去學琴,當我學出了興趣時,家兄卻堅持不肯去上課,讓我也沒機會繼續學習,因此拉小提琴一直是我未完成的美夢。
幼稚園畢業,回到原來的學區國語實小就讀,學區中以外省小孩居多,所以我的國語發音還不錯。記得當時常常有很多外國人坐在教室後面,跟著我們一起上國語課,大家一起玩,國語就在遊戲當中學起來了。國語的讀音跟閩南語全然不同,例如國語ㄥ和ㄣ的音要分清楚,該不該用唇音,像「陳」與「程」就不一樣,還有我們臺灣人對ㄈ跟ㄏ也常搞不清楚。
當時除了國語實小,還有北師附小、女師附小,這三所學校有點像姐妹校。尤其國語實小,從來不受升學壓力的影響,並沒有補習,全方位五育都沒缺少,在我們那個時代,學校不惡補是很難的,國語實小實施正常教學,美術、音樂都沒忽略,至今我還是覺得國語實小最好。國語實小與建國中學只有一牆之隔,我們打躲避球、打籃球,打著打著常常會把球丟到建中校園內。記得讀小學三年級到六年級時,下課後還會走到建國中學老師宿舍區,與一位音樂老師學鋼琴呢!
小學畢業那年,因為小提琴的夢還未了,我很勇敢的去找許常惠老師,執意請他幫忙買了一把小提琴,他當時已經不教小孩子拉琴,就把我交給他的新婚夫人教導,我又認真學了一段時間,終於認清自己不是音樂家的料,才總算放棄不學。自己雖當不成演奏家,但還是可以成為一位欣賞者。
家父有一位學生李正義,在國立藝專畢業後,進入功學社工作,因此贈送許多音樂會入場券給我們,我常常一個人搭著○東公車到終點站國際學舍,聆聽音樂會。當時的國際學舍算是位處臺北市的邊緣地帶,記得一到晚上就一片漆黑,我依然樂於前往欣賞音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