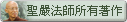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佛陀:一個覺醒的人
Buddha
譯者:林宏濤
出版社:如果出版
出版日期:2022年02月23日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21*14.8*1.9cm
商品編號:1151800091
ISBN:9786267045169
定價:NT$400
會員價:NT$340 (85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導論
↑TOP
有些佛教徒或許會說,撰寫悉達多.喬達摩的傳記是「非佛事」。在他們看來,權威再怎麼偉大,都不應該崇拜它:佛教徒應該發心自力解脫,而不是依賴一個有領導魅力的領袖。西元九世紀的一個禪師──他創立了臨濟宗──甚至對弟子說:「見佛殺佛!」以強調獨立於權威人物之外是很重要的事。喬達摩或許不贊成這麼暴力的觀點,但是他終其一生都在對抗個人的崇拜,而一直要轉移弟子們對他的依賴。其實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生命和人格,而是他的教法。他相信他已經證得了銘刻於最深層的存在結構裡的真理。那就是一個「法」(dhamma);這個字有許多涵義,但是原本指的是諸神、人類和動物生命的根本法則。透過這個真理的發現,喬達摩證得菩提,並且體會到甚深的內在轉變;在生死流轉中,他得到安穩且不受後有。喬達摩因而成佛,也就是成為覺者或智者。他認為任何弟子都可以證得相同的菩提,只要他們遵循這個道。但是如果人們開始崇拜喬達摩這個人,他們就會忘失其道業,那麼這個崇拜就會變成一個道具,為導致無謂的依賴,那只會是個障道因緣。
佛教的經典裡便忠於這個精神,其中似乎很少告訴我們喬達摩的生活和性格的細節。因此我們顯然很難撰寫一本合乎現代標準的佛陀傳記,因為我們資料很少是有史可徵的。證明有個稱為佛教的宗教存在的第一個外在證據,是阿育王(Aṣoka)的刻敕,他在大約西元前二六九到二三二年間統治北印度的孔雀王朝(Mauryan)。但是他比佛陀晚了兩百年。史不足徵的結果,使得有些十九世紀的西方學者,甚至懷疑喬達摩這個歷史人物的存在。他們認為他只是當時盛行的數論(Sāṃkhya)哲學的人格化,或是太陽崇拜的象徵。不過現代學者已經拋棄這種懷疑論的立場,而主張即使佛典中少有如「福音般的真理」,我們還是可以合理相信悉達多.喬達摩的確存在,而他的弟子們也盡其所能地保存對於他的生平和教法的回憶。
在發掘佛陀的故事時,我們依據卷帙浩繁的佛典,它們以多種亞洲語言寫成,在圖書館裡得佔好幾層書架。當然這些經典的集成相當複雜,其中許多部分的地位也有爭議。一般相信最有用的是巴利文(Pāli)經典,那是北印度某個起源不詳的方言,似乎很接近摩揭陀語(Magadhan),喬達摩可能也使用這種語言。佛教徒把這些聖典保存在斯里蘭卡、緬甸和泰國,它們均屬於上座部佛教。直到阿育王的時代,書寫文字才開始普及,然而巴利文經典始終以口傳保存,而且在西元前一世紀時,可能都還沒有文字記載。那麼,這些聖典是如何集成的呢?
保存佛陀的生平和教法的傳說,似乎是從他涅槃後不久的西元前四八三年開始。當時的佛教僧侶過著遊行的生活;他們遊行過恆河平原的許多城市和鄉鎮,傳授人們證得菩提和離苦得樂的教法。然而在雨季時,他們無法上路,於是聚集安居於各個精舍,在雨安居期間,僧眾討論教法和修行的問題。巴利文經典說,佛滅後不久,僧侶召開結集佛陀經律的大會。事隔五十年,北印度東區的僧眾似乎還能記得他們偉大的導師,其他人則以更正式的方法結集他們的見證。他們不可以寫下來,但是瑜伽的修行給了他們非常好的記憶力。於是他們發展出記誦佛陀說法和戒律細節的方法。或許正如佛陀所說所制,他們也以偈頌的方式記說他的教法,甚至可以唱誦;他們也發展出特定的表述形式和反覆唱誦的風格(這在現今的經典裡仍然可見),以幫助比丘們記憶。他們把經教和戒律區分為性質不同但相互重疊的部分,有些比丘則負責記誦這些文集以流傳後世。
佛滅約百年後,僧團召開第二次結集大會,這次結集的經典似乎很接近現在的巴利文佛典的形式。我們經常稱之為「三藏」(Tipiṭaka),因為經典寫成之後會安置在三個篋子裡:分別為《經藏》(Sutta piṭaka)、《律藏》(Vinaya piṭaka)、以及《論藏》。這三藏各自又細分如下:
一、《經藏》,包含五部(nikāya),是為佛說:
(一)《長部》(Dīgha Nikāya),是三十四部長篇論述,主要是關於比丘之修行、在家眾的義務、以及印度在西元前五世紀時宗教生活之種種面向。不過其中也有關於佛的種種具足的解說(《自歡喜經》﹝Sampasādaniya﹞)以及佛陀的晚年(《大般涅槃經》﹝Mahaparinibbāṇa﹞)。
(二)《中部》(Majjhima Nikāya),是為一百五十二部中篇經典(suttas)。包括佛陀的許多故事、求道的過程、早期的說法,以及部分核心的教義。
(三)《相應部》(Saṁyutta Nikāya),共五品(二八八九經),根據主題分類,論述如八正道以及十二因緣之類的問題。
(四)《增支部》(Aṇguttara Nikāya),共十一集,大部分在其他經典都出現過。
(五)《小部》(Khuddaka-Nikāya),次要經典之集成,包括著名的《法句經》(Dhammapada),是佛陀的雋語偈詩集;《自說經》(Udāna)則是如來之警語,大部分是偈頌的形式,其中有因緣總序,闡明每個人如何得以解脫;《經集》(Sutta-Nipāta),也是偈頌集,包括佛陀的某些傳說;以及《本生經》(Jātaka),關於佛陀及其弟子前世的故事,以說明人們的「業」(kamma)如何影響到他們未來的存在。
二、《律藏》,記載佛所制定之諸戒律。分為三大部:
(一)《經分別》(Sutta Vibhanga),列舉了二百二十七條戒,犯戒者必須在每半月之集會裡懺悔,經典裡也說明制戒之因緣。
(二)《犍度》(Khandhakha),又分為大品(Mahāvagga)和小品(Cullavagga),包括受戒、安居和儀式的規定,也有制戒因緣的說明。在這些說明裡,都保存了許多關於佛陀的重要傳說。
(三)《附隨》(Parivāra),戒條之解釋和分類。
而《論藏》(Abhidhamma Piṭaka)則偏重哲學和教義的分析,和傳記寫作比較沒有關係。
第二次結集之後,佛教發生了派系分立的運動,分裂為許多部派。每個部派都保存了這些經典,但是都經過重新整理,以配合他們自己的教義。一般說來,似乎沒有任何文獻被摒棄,即使其中有增補和改作。上座部的巴利文經典當然不是「三藏」的唯一版本,卻是唯一完整保存下來的經典。不過印度某些失佚的文獻片段,可以在後來中譯和藏譯經典裡發現,其中有我們所見最早的梵文經典。所以即使這些經典是在西元五到六世紀才迻譯,這大約是在佛滅的千年之後,其中有些部分仍然相當古老,可以和巴利文聖典對觀。
從以上的簡單說明,可以歸結出我們引用經典資料的若干立場。第一、經典皆聲明為佛所說,而沒有比丘們的增補。口傳的方式使我們無法知道個別的作者;佛教經典也不同於《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寫作,每部福音書都有作者個人風格的觀點。對於佛典結集和編纂的比丘們以及後來的抄寫者,我們一無所知。第二、巴利文經典自然是反映上座部的觀點,而且可能為了論爭而歪曲原典精神。第三、儘管比丘們有經過瑜伽訓練的記憶力,這種口傳方式難免有瑕疵。許多文獻可能已經失佚,有些被誤解,而比丘們後來的觀點也顯然投射到佛陀身上。我們無法分辨哪些故事和教法是真正佛說的,哪些是偽造的。經典沒有辦法給與我們滿足現代科學史學標準的資訊。它們只能說是反映了巴利文聖典形成時(也就是佛滅後三代之間)關於悉達多的傳說。後來西藏和中國的經典當然也包含某些古老文獻,但是它們也代表著這些傳說更加晚近的發展。而且事實上,現在發掘最古老的巴利文經典,也不過大約五百年前的歷史。
但是我們不必因此就洩氣。經典裡的確有些似乎可信的歷史資料。我們對於西元前五世紀的北印度所知甚多,正如耆那教(Jains)的經典所述,耆那教和佛陀大約在同一個時代。這些經典明確提到吠陀(Veda)宗教,而這是後來撰寫經論的佛教徒大部分都避而不談的;我們也知道許多歷史人物,像是摩揭陀國的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也知道城市生活的興起,以及該時期的政治、經濟和制度,正如考古學家、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所發現的。因此,學者們現在相信有些經典可能是出自原始佛教時期,而我們確實也很難接受十九世紀時認為佛陀只是佛教的杜撰的人物的說法。而且由於整個教法都有其一致性和融貫性,指向一個原初的智慧,使得我們也很難將之視為集體的創作。經典裡部分的話語當然有可能是出自悉達多.喬達摩,雖然我們無法確定是哪些。
從巴利文聖典,我們還看到一個重要的事實:聖典裡頭沒有關於佛陀生平的連續性敘事。佛陀的軼事只是教法的點綴,作為敷演教義和戒律的緣起。佛陀在說法時,有時候會對弟子談到他早年的生活或他的證道。但是絕對不像是在猶太教或基督宗教聖經的摩西或耶穌那樣有完整的年代解說。後來的佛教徒的確寫了詳盡而前後相續的佛陀傳記。我們有藏譯的《普曜經》(Lalita-Vistara)(西元三世紀),以及巴利文的《本生經因緣總序》(Nidāna Kathā)(西元五世紀),後者是對於《本生經》(Jātaka)的經釋。由西元五世紀的佛音(Buddhaghosa)確立最後形式的經釋,也可以幫助讀者釐訂經典裡散見各處的不連貫事件的年代順序。但是即使這些晚出的故事也有闕文。其中對於佛陀證道後四十五年間的傳法幾乎沒有詳細的敘事。《普曜經》止於佛陀的初轉法輪,而《本生經因緣總序》則談到佛教在拘薩羅國(Kosala)首都舍衛城(Sāvatthī)建立第一所精舍為止,那是佛陀剛開始四處遊化的時期。在佛陀的傳法裡,有二十年的時間沒有任何事蹟記載。
這些似乎可以指出,那些主張歷史性的悉達多故事並不重要的佛教徒,他們是對的。而北印度的人民對於我們所謂的歷史確實也不感興趣:他們更關心的是歷史事件的意義。其結果是,大部分西方人認為不可或缺的資料,在經典裡卻付之闕如。我們甚至不確定佛陀活在哪個世紀。傳統上認為他於西元前四八三年涅槃,但是中國的文獻卻認為他直到西元前三六八年才入滅。如果連佛教徒自己都不關心佛陀的生平,那麼我們為什麼要為悉達多的傳記傷腦筋呢?
但是並不完全是如此。學者們現在相信,後來延伸的傳記是以早期關於喬達摩生平的敘述為藍本,那是在第二次結集時誦成的,現在已經佚失。再者,經典顯示出最早的佛教徒非常重視喬達摩生平裡的若干關鍵時期:他的誕生、出家、成等正覺、初轉法輪以及入滅。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我們或許對於喬達摩生平的若干層面不得其門而入,但是我們可以相信,這些關鍵事件所描繪的梗概應該無誤。佛陀總是強調他的教法完全是於現法自證現證的。他不曾探究其他人的觀點或是發展什麼抽象的理論。他是從自己的生命歷史裡得到結論的。他教導他的弟子們說,如果他們想證道,就必須出離成為托缽僧,並且像他一樣修瑜伽行。他的生活和言教是密不可分的。他的哲學基本上是自傳式的,聖典和經釋裡所描繪的佛陀生平輪廓,是作為其他佛教徒的典範和鼓勵。正如他所說的:「見我者即見法,見法者即見我。」
任何主要的宗教人物都有個特色。現代的新約學者證明,我們對於歷史上的耶穌的認識其實比我們自認為的還要少得多。「福音的真理」並不是像我們假設的那樣無懈可擊。但是這並無礙於幾百萬人遵主聖範,把他的憐憫和受難的經歷當作新生活的指引。耶穌當然存在,但是他在福音書裡的故事表現為某種典範。基督信徒在挖掘自己的問題核心時,總會回想到他。的確,只有在人們經歷某種意義下的人格轉化,才有可能完全瞭解耶穌。佛陀也是如此,直到二十世紀,他都可能是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的教法在印度盛行了一千五百年,然後傳到西藏、中亞、中國、韓國、日本、斯里蘭卡以及東南亞。對於數百萬人而言,他已經是人類情境的典範。
因此,理解佛陀大抵上和他的教法印契的生平,可以幫助我們所有人了解人類的困境。但是二十一世紀的傳記通常不會這麼寫;我們無法從這樣的傳記裡追溯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也無法發現佛陀生平裡任何有爭議性的新事實,因為沒有任何經典裡的事件可以真正說是在歷史上實際發生過。歷史只是告訴我們有這些傳說,而我們只能概括接受巴利文經典在佛滅後一百年所發展的形式。現在,許多讀者會發現這傳說的若干側面並不可信:喬達摩生平裡比較俗世且在歷史上可信的事件,經常夾雜著諸神和神通變現的故事。而現代的歷史評論通常有個拇指定律,他們會把神蹟的事件解釋為後人的穿鑿附會之說。
但是如果我們也這樣解釋巴利文聖典,就會扭曲了這些傳說。我們會無法確定說,相較於所謂的預兆和奇蹟,比較正常的事件是否更加接近原始的傳說。開展這些聖典的比丘們,當然會相信諸神的存在,即使他們視之為有限的存有者;而且我們也會看到,他們也開始把諸神視為人類心理狀態的投射。他們同時相信,瑜伽深行可以使瑜祇獲得「悉地成就」(siddhi)(神通);修習瑜伽可以訓練心靈行種種神通,正如奧林匹克運動員訓練出來的體能,可以給與他常人無法企及的力量。人們想像瑜伽行者有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等,結集聖典的比丘們會認為佛陀想當然爾地也會這些事,即使佛陀自己對神通頗有微詞,認為應該避免行神通。而我們會看到,「神通的故事」通常是用來告誡弟子,說明炫耀大威德力並沒有什麼意義。
巴利文經典裡記載的許多故事都有個譬喻或象徵性的意義。早期的佛教徒重視的是聖典裡的意義,而不是歷史上真實的細節。我也發現,在後來的傳記中,像是《本生經因緣總序》,在關於喬達摩的決定出家和證道的事件上,有別於巴利文聖典裡簡略而學術性的敘述,它解釋得更加仔細。這些後出的故事比聖典充斥著更多神話的元素:天人出現、大地震動、城門被天人神奇地打開。同樣地,如果想像這些神蹟的細節是後來的人附會到原始傳說的,那會是個錯誤。這些晚出而有連貫性的傳記,可能是根據在佛滅後百年間創作、而後失佚的生平傳說,大概就在巴利文聖典集成之時。早期的佛教徒並不在意這些明顯有神話色彩的故事和聖典的差異。它們只是對於這些事件的不同詮釋,突顯故事的精神和心理意義。
但是這些神話和奇蹟顯示,即使是相信佛陀應該僅僅被視為一個導師和典範的上座部佛教,也開始把他當作超人。而更加普及的大乘佛教則是真正把喬達摩給神化了。人們過去認為上座部代表佛教比較純粹的形式,而大乘是其轉訛。但是現在的學者則認為兩者同樣的真實。上座部始終強調瑜伽的重要,崇拜那些成為阿羅漢的比丘們,他們像佛陀一樣,都已成等正覺。但是把佛陀尊為人類生死流轉中的永恆臨在以及崇拜對象的大乘佛教,卻也保存了在巴利文聖典裡同樣強調的其他價值,特別是慈悲心的重要性。他們覺得上座部太過狹隘而不知變通,而阿羅漢只是自私地追求自己的證道。他們偏好崇拜菩薩(Bodhisatta)的形象,菩薩是授記將要成佛的男人或女人,為了把解脫道傳給「眾生」,雖久證菩提而不取涅槃。而我們會看到,佛陀認為比丘們也應該如此。兩者都抓住重要的長處,也都失去了某些東西。
佛教的經典裡便忠於這個精神,其中似乎很少告訴我們喬達摩的生活和性格的細節。因此我們顯然很難撰寫一本合乎現代標準的佛陀傳記,因為我們資料很少是有史可徵的。證明有個稱為佛教的宗教存在的第一個外在證據,是阿育王(Aṣoka)的刻敕,他在大約西元前二六九到二三二年間統治北印度的孔雀王朝(Mauryan)。但是他比佛陀晚了兩百年。史不足徵的結果,使得有些十九世紀的西方學者,甚至懷疑喬達摩這個歷史人物的存在。他們認為他只是當時盛行的數論(Sāṃkhya)哲學的人格化,或是太陽崇拜的象徵。不過現代學者已經拋棄這種懷疑論的立場,而主張即使佛典中少有如「福音般的真理」,我們還是可以合理相信悉達多.喬達摩的確存在,而他的弟子們也盡其所能地保存對於他的生平和教法的回憶。
在發掘佛陀的故事時,我們依據卷帙浩繁的佛典,它們以多種亞洲語言寫成,在圖書館裡得佔好幾層書架。當然這些經典的集成相當複雜,其中許多部分的地位也有爭議。一般相信最有用的是巴利文(Pāli)經典,那是北印度某個起源不詳的方言,似乎很接近摩揭陀語(Magadhan),喬達摩可能也使用這種語言。佛教徒把這些聖典保存在斯里蘭卡、緬甸和泰國,它們均屬於上座部佛教。直到阿育王的時代,書寫文字才開始普及,然而巴利文經典始終以口傳保存,而且在西元前一世紀時,可能都還沒有文字記載。那麼,這些聖典是如何集成的呢?
保存佛陀的生平和教法的傳說,似乎是從他涅槃後不久的西元前四八三年開始。當時的佛教僧侶過著遊行的生活;他們遊行過恆河平原的許多城市和鄉鎮,傳授人們證得菩提和離苦得樂的教法。然而在雨季時,他們無法上路,於是聚集安居於各個精舍,在雨安居期間,僧眾討論教法和修行的問題。巴利文經典說,佛滅後不久,僧侶召開結集佛陀經律的大會。事隔五十年,北印度東區的僧眾似乎還能記得他們偉大的導師,其他人則以更正式的方法結集他們的見證。他們不可以寫下來,但是瑜伽的修行給了他們非常好的記憶力。於是他們發展出記誦佛陀說法和戒律細節的方法。或許正如佛陀所說所制,他們也以偈頌的方式記說他的教法,甚至可以唱誦;他們也發展出特定的表述形式和反覆唱誦的風格(這在現今的經典裡仍然可見),以幫助比丘們記憶。他們把經教和戒律區分為性質不同但相互重疊的部分,有些比丘則負責記誦這些文集以流傳後世。
佛滅約百年後,僧團召開第二次結集大會,這次結集的經典似乎很接近現在的巴利文佛典的形式。我們經常稱之為「三藏」(Tipiṭaka),因為經典寫成之後會安置在三個篋子裡:分別為《經藏》(Sutta piṭaka)、《律藏》(Vinaya piṭaka)、以及《論藏》。這三藏各自又細分如下:
一、《經藏》,包含五部(nikāya),是為佛說:
(一)《長部》(Dīgha Nikāya),是三十四部長篇論述,主要是關於比丘之修行、在家眾的義務、以及印度在西元前五世紀時宗教生活之種種面向。不過其中也有關於佛的種種具足的解說(《自歡喜經》﹝Sampasādaniya﹞)以及佛陀的晚年(《大般涅槃經》﹝Mahaparinibbāṇa﹞)。
(二)《中部》(Majjhima Nikāya),是為一百五十二部中篇經典(suttas)。包括佛陀的許多故事、求道的過程、早期的說法,以及部分核心的教義。
(三)《相應部》(Saṁyutta Nikāya),共五品(二八八九經),根據主題分類,論述如八正道以及十二因緣之類的問題。
(四)《增支部》(Aṇguttara Nikāya),共十一集,大部分在其他經典都出現過。
(五)《小部》(Khuddaka-Nikāya),次要經典之集成,包括著名的《法句經》(Dhammapada),是佛陀的雋語偈詩集;《自說經》(Udāna)則是如來之警語,大部分是偈頌的形式,其中有因緣總序,闡明每個人如何得以解脫;《經集》(Sutta-Nipāta),也是偈頌集,包括佛陀的某些傳說;以及《本生經》(Jātaka),關於佛陀及其弟子前世的故事,以說明人們的「業」(kamma)如何影響到他們未來的存在。
二、《律藏》,記載佛所制定之諸戒律。分為三大部:
(一)《經分別》(Sutta Vibhanga),列舉了二百二十七條戒,犯戒者必須在每半月之集會裡懺悔,經典裡也說明制戒之因緣。
(二)《犍度》(Khandhakha),又分為大品(Mahāvagga)和小品(Cullavagga),包括受戒、安居和儀式的規定,也有制戒因緣的說明。在這些說明裡,都保存了許多關於佛陀的重要傳說。
(三)《附隨》(Parivāra),戒條之解釋和分類。
而《論藏》(Abhidhamma Piṭaka)則偏重哲學和教義的分析,和傳記寫作比較沒有關係。
第二次結集之後,佛教發生了派系分立的運動,分裂為許多部派。每個部派都保存了這些經典,但是都經過重新整理,以配合他們自己的教義。一般說來,似乎沒有任何文獻被摒棄,即使其中有增補和改作。上座部的巴利文經典當然不是「三藏」的唯一版本,卻是唯一完整保存下來的經典。不過印度某些失佚的文獻片段,可以在後來中譯和藏譯經典裡發現,其中有我們所見最早的梵文經典。所以即使這些經典是在西元五到六世紀才迻譯,這大約是在佛滅的千年之後,其中有些部分仍然相當古老,可以和巴利文聖典對觀。
從以上的簡單說明,可以歸結出我們引用經典資料的若干立場。第一、經典皆聲明為佛所說,而沒有比丘們的增補。口傳的方式使我們無法知道個別的作者;佛教經典也不同於《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約翰福音》的寫作,每部福音書都有作者個人風格的觀點。對於佛典結集和編纂的比丘們以及後來的抄寫者,我們一無所知。第二、巴利文經典自然是反映上座部的觀點,而且可能為了論爭而歪曲原典精神。第三、儘管比丘們有經過瑜伽訓練的記憶力,這種口傳方式難免有瑕疵。許多文獻可能已經失佚,有些被誤解,而比丘們後來的觀點也顯然投射到佛陀身上。我們無法分辨哪些故事和教法是真正佛說的,哪些是偽造的。經典沒有辦法給與我們滿足現代科學史學標準的資訊。它們只能說是反映了巴利文聖典形成時(也就是佛滅後三代之間)關於悉達多的傳說。後來西藏和中國的經典當然也包含某些古老文獻,但是它們也代表著這些傳說更加晚近的發展。而且事實上,現在發掘最古老的巴利文經典,也不過大約五百年前的歷史。
但是我們不必因此就洩氣。經典裡的確有些似乎可信的歷史資料。我們對於西元前五世紀的北印度所知甚多,正如耆那教(Jains)的經典所述,耆那教和佛陀大約在同一個時代。這些經典明確提到吠陀(Veda)宗教,而這是後來撰寫經論的佛教徒大部分都避而不談的;我們也知道許多歷史人物,像是摩揭陀國的頻婆娑羅王(Bimbisāra),也知道城市生活的興起,以及該時期的政治、經濟和制度,正如考古學家、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所發現的。因此,學者們現在相信有些經典可能是出自原始佛教時期,而我們確實也很難接受十九世紀時認為佛陀只是佛教的杜撰的人物的說法。而且由於整個教法都有其一致性和融貫性,指向一個原初的智慧,使得我們也很難將之視為集體的創作。經典裡部分的話語當然有可能是出自悉達多.喬達摩,雖然我們無法確定是哪些。
從巴利文聖典,我們還看到一個重要的事實:聖典裡頭沒有關於佛陀生平的連續性敘事。佛陀的軼事只是教法的點綴,作為敷演教義和戒律的緣起。佛陀在說法時,有時候會對弟子談到他早年的生活或他的證道。但是絕對不像是在猶太教或基督宗教聖經的摩西或耶穌那樣有完整的年代解說。後來的佛教徒的確寫了詳盡而前後相續的佛陀傳記。我們有藏譯的《普曜經》(Lalita-Vistara)(西元三世紀),以及巴利文的《本生經因緣總序》(Nidāna Kathā)(西元五世紀),後者是對於《本生經》(Jātaka)的經釋。由西元五世紀的佛音(Buddhaghosa)確立最後形式的經釋,也可以幫助讀者釐訂經典裡散見各處的不連貫事件的年代順序。但是即使這些晚出的故事也有闕文。其中對於佛陀證道後四十五年間的傳法幾乎沒有詳細的敘事。《普曜經》止於佛陀的初轉法輪,而《本生經因緣總序》則談到佛教在拘薩羅國(Kosala)首都舍衛城(Sāvatthī)建立第一所精舍為止,那是佛陀剛開始四處遊化的時期。在佛陀的傳法裡,有二十年的時間沒有任何事蹟記載。
這些似乎可以指出,那些主張歷史性的悉達多故事並不重要的佛教徒,他們是對的。而北印度的人民對於我們所謂的歷史確實也不感興趣:他們更關心的是歷史事件的意義。其結果是,大部分西方人認為不可或缺的資料,在經典裡卻付之闕如。我們甚至不確定佛陀活在哪個世紀。傳統上認為他於西元前四八三年涅槃,但是中國的文獻卻認為他直到西元前三六八年才入滅。如果連佛教徒自己都不關心佛陀的生平,那麼我們為什麼要為悉達多的傳記傷腦筋呢?
但是並不完全是如此。學者們現在相信,後來延伸的傳記是以早期關於喬達摩生平的敘述為藍本,那是在第二次結集時誦成的,現在已經佚失。再者,經典顯示出最早的佛教徒非常重視喬達摩生平裡的若干關鍵時期:他的誕生、出家、成等正覺、初轉法輪以及入滅。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我們或許對於喬達摩生平的若干層面不得其門而入,但是我們可以相信,這些關鍵事件所描繪的梗概應該無誤。佛陀總是強調他的教法完全是於現法自證現證的。他不曾探究其他人的觀點或是發展什麼抽象的理論。他是從自己的生命歷史裡得到結論的。他教導他的弟子們說,如果他們想證道,就必須出離成為托缽僧,並且像他一樣修瑜伽行。他的生活和言教是密不可分的。他的哲學基本上是自傳式的,聖典和經釋裡所描繪的佛陀生平輪廓,是作為其他佛教徒的典範和鼓勵。正如他所說的:「見我者即見法,見法者即見我。」
任何主要的宗教人物都有個特色。現代的新約學者證明,我們對於歷史上的耶穌的認識其實比我們自認為的還要少得多。「福音的真理」並不是像我們假設的那樣無懈可擊。但是這並無礙於幾百萬人遵主聖範,把他的憐憫和受難的經歷當作新生活的指引。耶穌當然存在,但是他在福音書裡的故事表現為某種典範。基督信徒在挖掘自己的問題核心時,總會回想到他。的確,只有在人們經歷某種意義下的人格轉化,才有可能完全瞭解耶穌。佛陀也是如此,直到二十世紀,他都可能是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的教法在印度盛行了一千五百年,然後傳到西藏、中亞、中國、韓國、日本、斯里蘭卡以及東南亞。對於數百萬人而言,他已經是人類情境的典範。
因此,理解佛陀大抵上和他的教法印契的生平,可以幫助我們所有人了解人類的困境。但是二十一世紀的傳記通常不會這麼寫;我們無法從這樣的傳記裡追溯實際上發生了什麼事,也無法發現佛陀生平裡任何有爭議性的新事實,因為沒有任何經典裡的事件可以真正說是在歷史上實際發生過。歷史只是告訴我們有這些傳說,而我們只能概括接受巴利文經典在佛滅後一百年所發展的形式。現在,許多讀者會發現這傳說的若干側面並不可信:喬達摩生平裡比較俗世且在歷史上可信的事件,經常夾雜著諸神和神通變現的故事。而現代的歷史評論通常有個拇指定律,他們會把神蹟的事件解釋為後人的穿鑿附會之說。
但是如果我們也這樣解釋巴利文聖典,就會扭曲了這些傳說。我們會無法確定說,相較於所謂的預兆和奇蹟,比較正常的事件是否更加接近原始的傳說。開展這些聖典的比丘們,當然會相信諸神的存在,即使他們視之為有限的存有者;而且我們也會看到,他們也開始把諸神視為人類心理狀態的投射。他們同時相信,瑜伽深行可以使瑜祇獲得「悉地成就」(siddhi)(神通);修習瑜伽可以訓練心靈行種種神通,正如奧林匹克運動員訓練出來的體能,可以給與他常人無法企及的力量。人們想像瑜伽行者有神足通、他心通、宿命通等,結集聖典的比丘們會認為佛陀想當然爾地也會這些事,即使佛陀自己對神通頗有微詞,認為應該避免行神通。而我們會看到,「神通的故事」通常是用來告誡弟子,說明炫耀大威德力並沒有什麼意義。
巴利文經典裡記載的許多故事都有個譬喻或象徵性的意義。早期的佛教徒重視的是聖典裡的意義,而不是歷史上真實的細節。我也發現,在後來的傳記中,像是《本生經因緣總序》,在關於喬達摩的決定出家和證道的事件上,有別於巴利文聖典裡簡略而學術性的敘述,它解釋得更加仔細。這些後出的故事比聖典充斥著更多神話的元素:天人出現、大地震動、城門被天人神奇地打開。同樣地,如果想像這些神蹟的細節是後來的人附會到原始傳說的,那會是個錯誤。這些晚出而有連貫性的傳記,可能是根據在佛滅後百年間創作、而後失佚的生平傳說,大概就在巴利文聖典集成之時。早期的佛教徒並不在意這些明顯有神話色彩的故事和聖典的差異。它們只是對於這些事件的不同詮釋,突顯故事的精神和心理意義。
但是這些神話和奇蹟顯示,即使是相信佛陀應該僅僅被視為一個導師和典範的上座部佛教,也開始把他當作超人。而更加普及的大乘佛教則是真正把喬達摩給神化了。人們過去認為上座部代表佛教比較純粹的形式,而大乘是其轉訛。但是現在的學者則認為兩者同樣的真實。上座部始終強調瑜伽的重要,崇拜那些成為阿羅漢的比丘們,他們像佛陀一樣,都已成等正覺。但是把佛陀尊為人類生死流轉中的永恆臨在以及崇拜對象的大乘佛教,卻也保存了在巴利文聖典裡同樣強調的其他價值,特別是慈悲心的重要性。他們覺得上座部太過狹隘而不知變通,而阿羅漢只是自私地追求自己的證道。他們偏好崇拜菩薩(Bodhisatta)的形象,菩薩是授記將要成佛的男人或女人,為了把解脫道傳給「眾生」,雖久證菩提而不取涅槃。而我們會看到,佛陀認為比丘們也應該如此。兩者都抓住重要的長處,也都失去了某些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