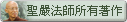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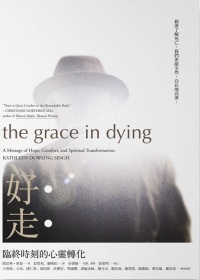
好走:臨終時刻的心靈轉化
作者:凱思林.辛
出版社:心靈工坊
語言:繁體中文
商品編號:1150190391
ISBN:9789867574480
定價:NT$460
會員價:NT$391 (85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精采書摘
↑TOP
我陪伴過數以百計的人走過臨終歷程,這一路以來我深深相信,人生這個最終階段,從感受悲劇開始,繼而要在崎嶇坎坷的心靈轉化之路上辛苦跋涉,最後攻上頂峰,沐浴在恩寵中。這條路說穿了就是從悲劇走向恩寵。雖然這一條路,有人就是走得比其他人都來得輕鬆,但它似乎是一條人人都得走的路。這麼多年下來,我慢慢練就出一隻「指月之手」,能夠「指出」這一條路何在。不過真正說來,我是以分享的方式,來談談我所觀察到的臨終過程,就像之前提過一位年輕的愛滋病患臨終前令人動容的心路歷程一樣。
我最近拜訪了一位七十六歲的老婦人維吉妮亞,長期受末期病症折磨的她,當時已經在垂死邊緣。我在病榻前陪著她,她女兒也在一旁,並且說起了母親多年來如何和末期病症搏鬥:「她帶著復仇的意志來對抗病魔。」維吉妮亞生病後依舊維持日常作息,為無數次的家庭聚會忙個不停,煮飯、打掃、歡笑、分享家中大小事,至於自己的病,能不提就不提。起初病情惡化得不明顯,後來卻急轉直下。她大限將至的那晚,我一走進她家裡,便察覺到某個「至高、超越」的覺識已經開始瀰漫滲透,在場的人早已感受到那超乎個人、遠比個我更為高深的意識充塞屋內。孩子們圍在這位垂死的女士身旁,氣氛深沉柔靜,他們的心儘管脆弱卻開放,斟滿了愛。化現在維吉妮亞這肉身裡的存有在我們眼前消解的那一刻,她的臉透出光芒,全身肌肉放鬆,看起來對這人世了無牽掛,平靜而灑脫。在她粗重的鼻息之上,彷彿是被她的氣息托起似的,浮著一片深沉的寂靜。我們被平靜和愛意所包圍,那平靜和愛意之深之濃厚,彷彿觸摸得到。在場的每個人都無可否認地深感震懾,心凝神注,沉浸在完善、完整、接納、安全和莊嚴的感受裡。
事後維吉妮亞的女兒告訴我,母親病逝前最後幾個星期,儘管因為要告別家人而難過,仍舊對即將展開的旅程充滿好奇。「我真想知道那一路上風景如何」,維吉妮亞跟家人這麼說。母親辭世後,女兒們也感覺欣慰,因為她走得如此安詳,也因為她對死亡之旅的疑惑終於得到答案。維吉妮亞離開人世,卻為留下來的人帶來全然的喜樂和徹底的療癒。
和我一樣親炙死亡現場的人,一再述說著同樣的體驗。死亡不僅震撼人,而且親臨其中會讓人蛻變。然而我們也很清楚,得知罹患末期病症,不管是當事人本身或家屬,都無可避免地覺得這是莫大的悲劇,對此我們深感同情。乍聞噩耗的那一刻,人們既深感哀痛,又難以置信,而接下來的臥病歲月,精神和肉體上更是飽受煎熬折磨。
我們必須好好來探究人感覺悲劇降臨之後,最終如何能體受恩寵。
我們可以從常用來描述悲劇及恩寵的體驗的文字來一窺究竟,雖然這兩種經驗基本上都是難以言喻的。古希臘人創造了一個能夠讓人類盡情抒發悲劇感的文化。希臘悲劇內容不外乎人類遭受的災厄、禍害和苦難,充塞著慾望受挫的困頓、不幸與悲嘆。這些悲劇形式上是戲劇,主人翁總有某種偉大的特質,卻在命運的撥弄下,因為自身某種缺陷而遇上災厄,無可避免地走上窮途末路或死亡。由此看來,古希臘人所洞察的,不折不扣正是心智自我努力活在自編自演的虛幻戲碼裡。在我們一手打造、有人我之分的世界裡,自己都是主角,也都有美好的特質,這特質是我們本性裡固有的,但我們的本性裡也有缺陷,那就是自絕於存有本源之外。我們活在這種謬誤或偏狹的狀態,遭受無情命運摧殘,使得虛妄的自我終究走上毀滅一途,並哀嘆遭遇劫厄的不幸。在悲劇這類呈現人類心靈內在運作的藝術形式裡,劇中主角別無選擇地承受命運的安排,任憑遠大於個我的力量擺佈。從更寬闊的角度來看,悲劇裡的災厄和磨難竟有著撥亂反「正」的意味。
希臘悲劇也指出,人之所以受苦,是為人處世逾越了分寸的緣故。在古希臘人看來,分寸拿捏得宜非常重要,而西方文明的基本概念,大半源自古希臘。人逾越分寸,是因為誤以為自己是部分或整體,無視於宇宙的本質是「部分」和「整體」大小相生、相互含藏。逾越分寸就會失衡脫序,破壞和諧圓融的狀態。逾越分寸就會陷入幻相,而這正是心智自我的困境,也是大多數人在大限將至時的處境。當我們失去了「內在的分寸」,就會活得支離破碎、孤單疏離。
我們花了好些篇幅探討人的生得權、死亡權,以及時時召喚我們的超個體向度。知道人有這些權利之後,我們也必須誠實地看清楚,自己就像浪跡天涯的遊子,過著四處漂泊的生活,遠離了存有本源這個家園。
這是一個悲劇性的生命狀態。我們就是在這般悲劇性的狀態裡,聆聽醫師宣判我們罹患末期病症、藥石罔效。這宣判讓我們赫然發覺,自己一直活得很可悲。就某個程度來說,被宣判罹患末期病症本身並不可悲,反倒是為了消化這項宣判,我們發現了自身生命狀態的可悲。雷凡就如此形容人對死亡的恐懼:「假想的個體所假想的失落。」
當人聽到是「我」罹患了「藥石罔效」的末期病症,這麼深度的醒悟,語言是進不到心裡去的,因此多說無益,甚至會徒增惱怒。雖然人的存在是多向度的,但在這麼深度的痛苦中,聽到「生命還有更開闊的層次」這類的話,一點安慰的效果都沒有。照見對方的生命處境、在當下相攜相伴,是我們得以撫慰彼此的方式。當人聽到自己罹患末期病症,肯定是要痛徹心扉,不管那當時所感受到的痛苦或恐懼強不強烈、切不切身,這般痛楚需要的是真正的慈悲。
臨終過程是一條典型的厄逆之路(via negativa)。「厄逆之路」的概念,是我小時候從天主教密契傳統裡聽來的。這個詞很自然地勾起我負面的聯想:一條歧嶇不平的路,說不定還險阻橫逆重重,刻意要來考驗我們。多年下來我發現,這條路確實不好走,真是難為了生而為人的我們,有時候這路程之艱辛困苦,讓我們不禁為必須孤單在這條路上摸索跋涉的自己和眾生感到悲憫。
隨著人生的歷練變多,省思的能力增加,我們對「厄逆」的理解愈發成熟深刻,能夠體會老子說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的道理。「厄逆之路」一詞從概念來說,反映的絕不僅是生而為人的痛苦和悲哀,它也反映出返歸之路「簡約即豐饒」(less is more)的特質。厄逆之路出現在先前提過的心識演化轉捩點,它是催生改變的乘具,心靈轉化的道路。在此,心靈轉化是以割捨的方式進行。隨著一道道分別心陸續癒合,心靈整全的程度愈來愈深,我們逐步將非本真的東西拋諸身後。弔詭的是,當我們愈來愈能割捨,我們會發現,割捨反而有所得,當我們把無足輕重的事從注意力裡移除,反而更有作為,愈能反璞歸真。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說是去除假象、顯露真實的過程。有人問米開朗基羅是如何雕出「大衛像」時,他答道:「大衛早就在那大理石裡,我只要把多餘的部分去除掉就行了。」
對美感體驗或創造歷程愈有瞭解,也愈能體會「厄逆之路」。以繪畫和音樂為例,不論是創作或欣賞,當我們體驗到藝術品的整體性,亦即不僅感受到顏色及形狀,或節奏及和聲之外,也同時感受到烘托主題的必要留白或「陰性」空間(”negative” spaces)時,美感的體驗於焉誕生。佛家以「大空」(Great Void)稱呼存有本源,便是深諳箇中道理。布伯(Martin Buber)則稱之為「居間」,使萬物產生關聯的凝結力。能夠領略整體性、領略事物的完形、領略留白所蘊藏的兼容並蓄的特性,就會感受到美。
生命的化育,絲毫不下於藝術創作。從存有本源脫身而出,到發展出個我意識的這段演化弧裡,我們以注意力為媒介,從「背景」裡創造出「形象」。在返歸之道上,也就是個我回歸存有本源的這段演化弧裡,我們把注意力放到了「陰性」的部分,亦即存有本源的空性,藉此把「形象」回歸「背景」之中。這是充滿美感的作為,也是一種創造活動,就像所有曠世傑作,往往饒富意蘊。這道理很簡單,因為重新變得完整、回歸本真(the Essential)的歷程,正是創造人的過程——人是首先自我體現,繼而要體現神的存在。
臨終過程加速了心識轉化這自然、漸進而根本的過程,而這個過程通常是出現在選擇走上返歸之道的人身上。在臨死經驗裡與末期病症搏鬥,心靈從而蛻變轉化的過程,正是不折不扣的一條厄逆之路。走在這條坎坷路上,我們吃盡苦頭,剔除虛幻不實、非關本真的一切,心識和我性從而邁向嶄新的次元。與末期病症共存是「為道日損」的一種體現。我們每天都會割捨一些東西,也許是某些執念,也許是某些愛惡,我們對自身的虛幻認同或自我界定一天天剝落。與末期病症共存讓人從裡到外全面受苦。
從知道患重病的那一刻起,人就開始受苦。在候診室等待、看診、打針、動手術、侵入式治療到裝義肢,無一不是對敏感身軀的折磨。聽醫師說明病情也很不是滋味,不論他∕她態度是溫和或冷酷。接下來的好幾個禮拜,我們把醫師說的話揣在心上,像是捧著一顆小巧的水晶球仔細端詳,拚命想從裡頭看出一絲希望,找出一絲意義,更是一種折騰。
親身經歷過病痛折磨的知名新聞記者卡森斯(Norman Cousins)仔細地描述生病的痛苦:
最先感覺到的是無助──這重病沒救了。然後下意識裡開始擔心自己恐怕沒法恢復正常,這擔憂的感覺一出來,就在我和世界之間築起了一道牆,把一個多采多姿、充塞各種美妙聲音、希望無限的世界隔絕在外。我不想讓人看成是自怨自艾的人,也不想再加重家人心理的負擔,他們知道我生這個病心裡已經夠難受的了;多了這兩項顧慮,我又變得更孤立。我心裡很矛盾,既害怕孤單,但又想自己靜一靜。我開始變得沒自信,說不定是下意識裡覺得生這個病曝露了我個人的缺陷。我擔心有人背著我做了什麼決定,擔心我想知道的他們沒有全盤告知,但又怕知道那些事。想到要接受侵入式的治療,我渾身毛骨悚然,也怕自己就要變成一疊數據資料,從此面貌模糊。看到陌生人帶著針筒和藥水瓶走近身邊,心裡就氣憤,這些人不是把據稱是仙丹妙藥的東西打入你的血管裡,就是彷彿要抽光你的血似地抽個不停。躺在病床上被推過慘白的走廊,進到檢驗室接受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精密機器、閃光和旋轉圓盤的檢查時,總感到痛苦不安。我渴望人與人真實接觸的溫暖──這渴望如此深沉、強烈、持續──卻不可得,留給我無盡的空虛。
知道自己藥石罔效的那一剎那,生病時分(the time of sickness)來到終點,就此邁入臨終時分(the time of dying),這才是真的讓我們屈服的一刻。把不治之症的宣判整合到想法、情緒和經驗裡,會讓我們陷入一場大悲劇,內心至極。
我們感到巨大的失落。我們失去了希望和夢想,再也沒法完成未實現的抱負,不能去體驗期待中的事。我們就要失去摯愛的人,失去與他們相處的時光,也不能參加以前順理成章會參加的活動,也喪失了原先用來證明自己的身分與價值的能力。要和所珍惜的一切告別,揮別親朋好友、人生回憶、鍾愛而熟悉的內心世界,以及愛我們的人溫柔的眼神和撫觸,我們感到痛苦。要放下自我感和生活所賴以為繫、屬不清的每件事每個人,我們悲慟不已。更難受的是,我們看不到未來,甚至無奈地承認:「我這輩子從沒做過真正想做的事。」
我們因為病情急遽惡化而受苦,生活自理能力受到影響,還得時常調適應變。不停有新的變化出現,等著我們去承受和接納。「我已經不能工作,現在得要接受不能出去散步。」「我已經沒法出去散步,現在得要接受不能下床走動。」「我已經沒法下床走動,現在得接受必須插尿管。」「我已經必須插尿管,現在得要接受皮膚開始龜裂。」「我的皮膚已經龜裂,現在得接受我徹底無依無靠。」「我已經徹底無依無靠,現在得接受我就要死了。」
想到自己再也回不去熟悉的生活,那些讓我們目光停駐、心神留戀的一切,真是會讓人痛徹心扉。我陪伴過的臨終病人當中,有人因為捨不得一尊親手雕塑的雕像而傷心,有人因為再也看不到樹蔭濃密、綠草如茵的風景而難過,有人則為了不知何時才會出世的孫子而悲傷;也有人因為他的年代即將告終、世人不可能如實體會他這一代人的見解、世界觀和經歷而哀傷;很多人一想到要離開所愛的人就悲慟難當。有位女士想到十歲的女兒將跟幼年喪母的自己一樣,要面對失去母親的無底深淵便止不住啜泣。這位女士極其疼愛女兒和五歲的兒子,這一雙兒女帶給她歡笑,她全心為孩子奉獻,如今卻要眼睜睜看著自己被迫離開兒女,這種痛心無以言喻。
很多我陪伴過的臨終病人,在接受放射性治療和化療一連串駭人的療程後告訴我,「癌症把我擊垮了。」他們難忍悲傷嚎啕大哭,「我就要死了」的念頭啃噬著他們。但也有少數人會在月圓的夜晚勉強撐起身坐著,欣賞月光。我看著他們沐浴在月光下,感受到他們柔弱的心因為離別在即而破碎。
「我不敢相信我就要死了!」數不清有多少人沉痛地向我哭訴。
看著別人一如往常地各自為生活忙碌,想像自己已經遭神離棄,揣摩著死亡那一刻會是如何,這種痛苦何等椎心刺骨。總之,打從聽到噩耗起,直到我們徹底臣服的那一刻止,人除了受苦別無其他,而這正是悲劇的本質。在臨終過程裡體驗悲劇的這段期間,人會痛苦,會悲傷,而且會謙卑地放開我們出於單純而往往是可愛的人性所珍愛和信賴的一切。
從體驗悲劇到感受恩寵的轉化之中,強大的精神動力開始起作用,特別是希望和意義所激發的精神動力,以及苦難所激發的精神動力。
我最近拜訪了一位七十六歲的老婦人維吉妮亞,長期受末期病症折磨的她,當時已經在垂死邊緣。我在病榻前陪著她,她女兒也在一旁,並且說起了母親多年來如何和末期病症搏鬥:「她帶著復仇的意志來對抗病魔。」維吉妮亞生病後依舊維持日常作息,為無數次的家庭聚會忙個不停,煮飯、打掃、歡笑、分享家中大小事,至於自己的病,能不提就不提。起初病情惡化得不明顯,後來卻急轉直下。她大限將至的那晚,我一走進她家裡,便察覺到某個「至高、超越」的覺識已經開始瀰漫滲透,在場的人早已感受到那超乎個人、遠比個我更為高深的意識充塞屋內。孩子們圍在這位垂死的女士身旁,氣氛深沉柔靜,他們的心儘管脆弱卻開放,斟滿了愛。化現在維吉妮亞這肉身裡的存有在我們眼前消解的那一刻,她的臉透出光芒,全身肌肉放鬆,看起來對這人世了無牽掛,平靜而灑脫。在她粗重的鼻息之上,彷彿是被她的氣息托起似的,浮著一片深沉的寂靜。我們被平靜和愛意所包圍,那平靜和愛意之深之濃厚,彷彿觸摸得到。在場的每個人都無可否認地深感震懾,心凝神注,沉浸在完善、完整、接納、安全和莊嚴的感受裡。
事後維吉妮亞的女兒告訴我,母親病逝前最後幾個星期,儘管因為要告別家人而難過,仍舊對即將展開的旅程充滿好奇。「我真想知道那一路上風景如何」,維吉妮亞跟家人這麼說。母親辭世後,女兒們也感覺欣慰,因為她走得如此安詳,也因為她對死亡之旅的疑惑終於得到答案。維吉妮亞離開人世,卻為留下來的人帶來全然的喜樂和徹底的療癒。
和我一樣親炙死亡現場的人,一再述說著同樣的體驗。死亡不僅震撼人,而且親臨其中會讓人蛻變。然而我們也很清楚,得知罹患末期病症,不管是當事人本身或家屬,都無可避免地覺得這是莫大的悲劇,對此我們深感同情。乍聞噩耗的那一刻,人們既深感哀痛,又難以置信,而接下來的臥病歲月,精神和肉體上更是飽受煎熬折磨。
我們必須好好來探究人感覺悲劇降臨之後,最終如何能體受恩寵。
我們可以從常用來描述悲劇及恩寵的體驗的文字來一窺究竟,雖然這兩種經驗基本上都是難以言喻的。古希臘人創造了一個能夠讓人類盡情抒發悲劇感的文化。希臘悲劇內容不外乎人類遭受的災厄、禍害和苦難,充塞著慾望受挫的困頓、不幸與悲嘆。這些悲劇形式上是戲劇,主人翁總有某種偉大的特質,卻在命運的撥弄下,因為自身某種缺陷而遇上災厄,無可避免地走上窮途末路或死亡。由此看來,古希臘人所洞察的,不折不扣正是心智自我努力活在自編自演的虛幻戲碼裡。在我們一手打造、有人我之分的世界裡,自己都是主角,也都有美好的特質,這特質是我們本性裡固有的,但我們的本性裡也有缺陷,那就是自絕於存有本源之外。我們活在這種謬誤或偏狹的狀態,遭受無情命運摧殘,使得虛妄的自我終究走上毀滅一途,並哀嘆遭遇劫厄的不幸。在悲劇這類呈現人類心靈內在運作的藝術形式裡,劇中主角別無選擇地承受命運的安排,任憑遠大於個我的力量擺佈。從更寬闊的角度來看,悲劇裡的災厄和磨難竟有著撥亂反「正」的意味。
希臘悲劇也指出,人之所以受苦,是為人處世逾越了分寸的緣故。在古希臘人看來,分寸拿捏得宜非常重要,而西方文明的基本概念,大半源自古希臘。人逾越分寸,是因為誤以為自己是部分或整體,無視於宇宙的本質是「部分」和「整體」大小相生、相互含藏。逾越分寸就會失衡脫序,破壞和諧圓融的狀態。逾越分寸就會陷入幻相,而這正是心智自我的困境,也是大多數人在大限將至時的處境。當我們失去了「內在的分寸」,就會活得支離破碎、孤單疏離。
我們花了好些篇幅探討人的生得權、死亡權,以及時時召喚我們的超個體向度。知道人有這些權利之後,我們也必須誠實地看清楚,自己就像浪跡天涯的遊子,過著四處漂泊的生活,遠離了存有本源這個家園。
這是一個悲劇性的生命狀態。我們就是在這般悲劇性的狀態裡,聆聽醫師宣判我們罹患末期病症、藥石罔效。這宣判讓我們赫然發覺,自己一直活得很可悲。就某個程度來說,被宣判罹患末期病症本身並不可悲,反倒是為了消化這項宣判,我們發現了自身生命狀態的可悲。雷凡就如此形容人對死亡的恐懼:「假想的個體所假想的失落。」
當人聽到是「我」罹患了「藥石罔效」的末期病症,這麼深度的醒悟,語言是進不到心裡去的,因此多說無益,甚至會徒增惱怒。雖然人的存在是多向度的,但在這麼深度的痛苦中,聽到「生命還有更開闊的層次」這類的話,一點安慰的效果都沒有。照見對方的生命處境、在當下相攜相伴,是我們得以撫慰彼此的方式。當人聽到自己罹患末期病症,肯定是要痛徹心扉,不管那當時所感受到的痛苦或恐懼強不強烈、切不切身,這般痛楚需要的是真正的慈悲。
臨終過程是一條典型的厄逆之路(via negativa)。「厄逆之路」的概念,是我小時候從天主教密契傳統裡聽來的。這個詞很自然地勾起我負面的聯想:一條歧嶇不平的路,說不定還險阻橫逆重重,刻意要來考驗我們。多年下來我發現,這條路確實不好走,真是難為了生而為人的我們,有時候這路程之艱辛困苦,讓我們不禁為必須孤單在這條路上摸索跋涉的自己和眾生感到悲憫。
隨著人生的歷練變多,省思的能力增加,我們對「厄逆」的理解愈發成熟深刻,能夠體會老子說的「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的道理。「厄逆之路」一詞從概念來說,反映的絕不僅是生而為人的痛苦和悲哀,它也反映出返歸之路「簡約即豐饒」(less is more)的特質。厄逆之路出現在先前提過的心識演化轉捩點,它是催生改變的乘具,心靈轉化的道路。在此,心靈轉化是以割捨的方式進行。隨著一道道分別心陸續癒合,心靈整全的程度愈來愈深,我們逐步將非本真的東西拋諸身後。弔詭的是,當我們愈來愈能割捨,我們會發現,割捨反而有所得,當我們把無足輕重的事從注意力裡移除,反而更有作為,愈能反璞歸真。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以說是去除假象、顯露真實的過程。有人問米開朗基羅是如何雕出「大衛像」時,他答道:「大衛早就在那大理石裡,我只要把多餘的部分去除掉就行了。」
對美感體驗或創造歷程愈有瞭解,也愈能體會「厄逆之路」。以繪畫和音樂為例,不論是創作或欣賞,當我們體驗到藝術品的整體性,亦即不僅感受到顏色及形狀,或節奏及和聲之外,也同時感受到烘托主題的必要留白或「陰性」空間(”negative” spaces)時,美感的體驗於焉誕生。佛家以「大空」(Great Void)稱呼存有本源,便是深諳箇中道理。布伯(Martin Buber)則稱之為「居間」,使萬物產生關聯的凝結力。能夠領略整體性、領略事物的完形、領略留白所蘊藏的兼容並蓄的特性,就會感受到美。
生命的化育,絲毫不下於藝術創作。從存有本源脫身而出,到發展出個我意識的這段演化弧裡,我們以注意力為媒介,從「背景」裡創造出「形象」。在返歸之道上,也就是個我回歸存有本源的這段演化弧裡,我們把注意力放到了「陰性」的部分,亦即存有本源的空性,藉此把「形象」回歸「背景」之中。這是充滿美感的作為,也是一種創造活動,就像所有曠世傑作,往往饒富意蘊。這道理很簡單,因為重新變得完整、回歸本真(the Essential)的歷程,正是創造人的過程——人是首先自我體現,繼而要體現神的存在。
臨終過程加速了心識轉化這自然、漸進而根本的過程,而這個過程通常是出現在選擇走上返歸之道的人身上。在臨死經驗裡與末期病症搏鬥,心靈從而蛻變轉化的過程,正是不折不扣的一條厄逆之路。走在這條坎坷路上,我們吃盡苦頭,剔除虛幻不實、非關本真的一切,心識和我性從而邁向嶄新的次元。與末期病症共存是「為道日損」的一種體現。我們每天都會割捨一些東西,也許是某些執念,也許是某些愛惡,我們對自身的虛幻認同或自我界定一天天剝落。與末期病症共存讓人從裡到外全面受苦。
從知道患重病的那一刻起,人就開始受苦。在候診室等待、看診、打針、動手術、侵入式治療到裝義肢,無一不是對敏感身軀的折磨。聽醫師說明病情也很不是滋味,不論他∕她態度是溫和或冷酷。接下來的好幾個禮拜,我們把醫師說的話揣在心上,像是捧著一顆小巧的水晶球仔細端詳,拚命想從裡頭看出一絲希望,找出一絲意義,更是一種折騰。
親身經歷過病痛折磨的知名新聞記者卡森斯(Norman Cousins)仔細地描述生病的痛苦:
最先感覺到的是無助──這重病沒救了。然後下意識裡開始擔心自己恐怕沒法恢復正常,這擔憂的感覺一出來,就在我和世界之間築起了一道牆,把一個多采多姿、充塞各種美妙聲音、希望無限的世界隔絕在外。我不想讓人看成是自怨自艾的人,也不想再加重家人心理的負擔,他們知道我生這個病心裡已經夠難受的了;多了這兩項顧慮,我又變得更孤立。我心裡很矛盾,既害怕孤單,但又想自己靜一靜。我開始變得沒自信,說不定是下意識裡覺得生這個病曝露了我個人的缺陷。我擔心有人背著我做了什麼決定,擔心我想知道的他們沒有全盤告知,但又怕知道那些事。想到要接受侵入式的治療,我渾身毛骨悚然,也怕自己就要變成一疊數據資料,從此面貌模糊。看到陌生人帶著針筒和藥水瓶走近身邊,心裡就氣憤,這些人不是把據稱是仙丹妙藥的東西打入你的血管裡,就是彷彿要抽光你的血似地抽個不停。躺在病床上被推過慘白的走廊,進到檢驗室接受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精密機器、閃光和旋轉圓盤的檢查時,總感到痛苦不安。我渴望人與人真實接觸的溫暖──這渴望如此深沉、強烈、持續──卻不可得,留給我無盡的空虛。
知道自己藥石罔效的那一剎那,生病時分(the time of sickness)來到終點,就此邁入臨終時分(the time of dying),這才是真的讓我們屈服的一刻。把不治之症的宣判整合到想法、情緒和經驗裡,會讓我們陷入一場大悲劇,內心至極。
我們感到巨大的失落。我們失去了希望和夢想,再也沒法完成未實現的抱負,不能去體驗期待中的事。我們就要失去摯愛的人,失去與他們相處的時光,也不能參加以前順理成章會參加的活動,也喪失了原先用來證明自己的身分與價值的能力。要和所珍惜的一切告別,揮別親朋好友、人生回憶、鍾愛而熟悉的內心世界,以及愛我們的人溫柔的眼神和撫觸,我們感到痛苦。要放下自我感和生活所賴以為繫、屬不清的每件事每個人,我們悲慟不已。更難受的是,我們看不到未來,甚至無奈地承認:「我這輩子從沒做過真正想做的事。」
我們因為病情急遽惡化而受苦,生活自理能力受到影響,還得時常調適應變。不停有新的變化出現,等著我們去承受和接納。「我已經不能工作,現在得要接受不能出去散步。」「我已經沒法出去散步,現在得要接受不能下床走動。」「我已經沒法下床走動,現在得接受必須插尿管。」「我已經必須插尿管,現在得要接受皮膚開始龜裂。」「我的皮膚已經龜裂,現在得接受我徹底無依無靠。」「我已經徹底無依無靠,現在得接受我就要死了。」
想到自己再也回不去熟悉的生活,那些讓我們目光停駐、心神留戀的一切,真是會讓人痛徹心扉。我陪伴過的臨終病人當中,有人因為捨不得一尊親手雕塑的雕像而傷心,有人因為再也看不到樹蔭濃密、綠草如茵的風景而難過,有人則為了不知何時才會出世的孫子而悲傷;也有人因為他的年代即將告終、世人不可能如實體會他這一代人的見解、世界觀和經歷而哀傷;很多人一想到要離開所愛的人就悲慟難當。有位女士想到十歲的女兒將跟幼年喪母的自己一樣,要面對失去母親的無底深淵便止不住啜泣。這位女士極其疼愛女兒和五歲的兒子,這一雙兒女帶給她歡笑,她全心為孩子奉獻,如今卻要眼睜睜看著自己被迫離開兒女,這種痛心無以言喻。
很多我陪伴過的臨終病人,在接受放射性治療和化療一連串駭人的療程後告訴我,「癌症把我擊垮了。」他們難忍悲傷嚎啕大哭,「我就要死了」的念頭啃噬著他們。但也有少數人會在月圓的夜晚勉強撐起身坐著,欣賞月光。我看著他們沐浴在月光下,感受到他們柔弱的心因為離別在即而破碎。
「我不敢相信我就要死了!」數不清有多少人沉痛地向我哭訴。
看著別人一如往常地各自為生活忙碌,想像自己已經遭神離棄,揣摩著死亡那一刻會是如何,這種痛苦何等椎心刺骨。總之,打從聽到噩耗起,直到我們徹底臣服的那一刻止,人除了受苦別無其他,而這正是悲劇的本質。在臨終過程裡體驗悲劇的這段期間,人會痛苦,會悲傷,而且會謙卑地放開我們出於單純而往往是可愛的人性所珍愛和信賴的一切。
從體驗悲劇到感受恩寵的轉化之中,強大的精神動力開始起作用,特別是希望和意義所激發的精神動力,以及苦難所激發的精神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