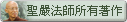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
小乗仏教思想論
作者:木村泰賢
譯者:釋依觀
出版社:台灣商務
出版日期:2020年06月05日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2*17*3cm
商品編號:1150720491
ISBN:9789570532722
定價:NT$630
會員價:NT$536 (85折)
序/後記
< 回商品頁序
↑TOP
深入經藏,融合現代哲學與心理學觀點的《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木村泰賢著作新譯本導讀
江燦騰(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
前東京帝大第一「印度哲學」講座教授木村泰賢原著的《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新譯本,同樣是由臺灣專譯日本佛學名著的釋依觀比丘尼翻譯完成,同樣由我推薦給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所以新到任不久的張曉蕊總編輯,也同意由我為此新譯本寫一篇導讀之文。
不過這已是我為木村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五本新譯本寫介紹文了,所以我想在此新譯本解說文中,提供給本書讀者更多與本書相關的學術史溯源解說。因為幾十年來的實際接觸與教學研究經驗,讓我深深感到當代臺灣佛教界信仰活動高度興盛之後的認知隱憂:極度缺乏對佛學教理具有現代理解的問題意識與相關佛教思維的學術史認知。因而才導致臺灣當代很多熱門佛教團體或組織,多數信徒就會因其被一再洗腦而逐漸形成對於指導者無條件的深度信仰認同,同時也讓其本身成為特定信仰意識形態的行為操縱,令人為之扼腕與嘆息。所以,在本文的解說中,我希望能提供一些有關木村本書新譯本的學術史溯源之歷史認知,讓有志者得以有所借鏡。
讀者須知,本書原著是屬於印度佛教的時期,介於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之間,歷時約五百年左右的──部派分裂時期的各種佛教詮釋教理──以現代性體系呈現的新詮釋論書。或者我們可以說,這是有關部派佛教時期最著名的現代型教理概論著作:它是如同北傳的世親著《俱舍論》或如南傳的覺音著《清淨道論》那樣經典等級的作品,二十世紀現代版新綜合詮釋論書。因而,木村泰賢的生命後期,主要的體系性教理著作,就是這本全書草稿完成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晚上的《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
但是,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凌晨三點,木村突然心肌梗塞猝逝時,此一草稿仍未公諸於世,而只是用鉛筆,快速且潦草地寫在教學講義的一堆稿紙上被存放著,木村有可能是還要修訂與增補,所以沒有急著直接出版。
之後,先經由跟他十年之久的女門生正木春枝全部謄寫,再交由木村的研究生西義雄、坂本幸男整合與編輯,並在一些經論引述的出處上,改為出自《大正藏》或《國譯一切經》上的頁碼,於一九三五年先由明治書院出版單行本,書名《小乘佛教思想論》;兩年後,即一九三七年,又再納入同書院出版的《木村泰賢全集》第五冊出版。
不過此處,我必須先提及一個有關此書出版時間的修正問題。因在二○一八年二月出版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新譯本》的解說之文中,我曾把本書的出版時間提早十年,其實是錯誤的,正確應是在一九三五年才首次出版才對。
但是,有關本書的介紹,除了在其納入全集時,曾在書末附有坂本幸男的簡單全書內容介紹之外,之後只有戰後從大陸來臺的釋演培法師,曾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在新竹市福嚴精舍,首次譯出本書中譯本時,根據木村原書的短序內容,將其改寫一篇稍微擴大的譯序之文,並刪去木村原序全文,所以事實上他也沒有增加任何新的解說資訊。
演培法師當時也表示他自己才剛學習日文,而且當時工具書較缺乏,可能因為如此,其譯文才無法將木村著作的精采表現出來。
所以,我才建議由釋依觀比丘尼重譯全書,並同時更正成現在通用的中文譯名,並由我負責重新回溯原書的論述與出版相關歷程的學術史解說。又因本書是木村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的有關教理的綜合解說,所以我建議此次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新譯本時,使用木村的原有書名《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而不要用《小乘佛教思想論》,以免帶有傳統大乘佛教徒,歷來對小乘佛教的貶抑。臺灣商務印書館編輯部也同意了這一改名,讓我深感興奮。但是,同時我要擔負的解說責任,也因此頓感沉重不少。
讀者須知,長期以來,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當代的東亞現代佛學研究,主要推動重鎮,當數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的印度哲學研究所。如今我們可以引述當代日本著名東大佛教學者齋藤明教授〔案:齋藤明教授是一九五○年生於日本東京,現任東京大學佛教學教授、國際佛教學會理事,前任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理事長(二○○八年至二○一四年),師從高崎直道、狄雍等著名學者,既有日本傳統的佛教情懷與治學精神,又通達歐洲的學術理念與研究風格,是當代日本佛教學界最具代表性的傑出學者之一〕,於二○一五年五月十七日接受《澎湃新聞》特約記者何歡歡的專訪,他在訪問中談及木村泰賢,看看他對於木村在東京帝大任教時期的巨大學術成就的讚美,以及他對當時號稱「日本佛教學者雙璧」──木村與宇井伯壽──兩者不同思辨風格所做出的客觀比較。齋藤明教授是這麼說的:
最早在現代國立大學裡教授佛教學的是村上專精(生於一八五一年,逝於一九二九年,淨土真宗僧侶)和木村泰賢(生於一八八一年,逝於一九三○年,曹洞宗僧侶)。村上教授是東京帝國大學「印度哲學」教席的第一代教授(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木村教授則早在一九一二年就以講師身分代時任東京帝大梵文學教授的高楠順次郎開設「印度哲學宗教史」課程。一九一七年任助教授,一九二○年赴歐美留學,一九二三年回國後升任「印度哲學」教授。木村教授才華横溢,被公認為最優秀的學者,當時推選他擔任校長的呼聲很高,可惜英年早逝。隨後,木村教授的同門師弟宇井伯壽(生於一八八二年,逝於一九六三年,曹洞宗僧侶)接替了這一教席。相比之下,木村教授研究中的哲學思辨與宗教關懷要比宇井教授強一些,但宇井教授有著非常強烈的語文學(Philology,日語的文獻學之意)情懷,而且研究領域非常廣泛,一手建立起我們這一學科的基本方法論——以語文學為基礎來研究佛教。
由此可見木村在當時堪稱是日本、甚至是全東亞最頂尖的印度佛學思想研究學者之一。他最大的佛教學術貢獻,主要就是能率先開創關於部派佛教論書的文獻學研究。而他之所以能得東大博士學位與能擔當東大的「印度哲學」第一講座教授的原因,就是源自他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一書的著述與出版。
況且,在當時歐洲佛教學者中,能與木村泰賢教授此一研究,進行互相對話與互爭長短的,只有比利時的佛教大學者蒲仙(De la Vallée Poussin)、英國的巴利文佛教論書權威學者戴維斯夫人(Mrs. Rhys Davids)、蘇聯佛教大學者舍爾巴茨基(Theodor Ippolitovich Stcherbatsky)與另一英國名學者凱思(Arthur Berriedale Keith)而已。但只有蒲仙與戴維斯夫人的著作,是早於木村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出版,所以木村在研究中主要的參考著作,就是此兩人的著作。
至於凱思的《印度和錫蘭佛教哲學》(Buddhist philosophy in India and Ceyl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3)與舍爾巴茨基的《佛教的中心概念與法的意義》(The Central Conception of Buddhism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Dharma”. L., Royal Asiatic soc., 1923, 112 c.,中譯本的書名為《小乘佛學》)都出版於一九二三年,所以是比木村的博士論文出版晚一年。
然而,當木村於一九二六年九月初完成其《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一書的全書草稿時,仍只在書中引用蒲仙與戴維斯夫人的著作,再加上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心理學教授兼哲學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與德國實驗心理學開創者馮特博士(Wilhelm Maximilian Wundt)的相關心理學著作而已。原因是,木村之所以能在日本佛學界率先研究阿毘達磨論中的佛教心理學,主要是受到戴維斯夫人的著作影響,而蒲仙則是開創西方研究部派佛教論書與進行翻譯的最著名學者,因此必須加以引用此兩者之著述,才符合學術常軌做法。但也因此,木村在《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中,才能有那些獨到的佛教心理論解說的相關章節論述。
在此同時,他也另外陸續發表有關佛教心理論解說的論文。由此可知,像此種能夠熟練集合專業化研究與論述普及化兩者,讓其彼此形成相互支援的雙刀流論述模式,木村不但最為擅長,並且盡全力從事。而主要其目的,就是為了讓初入門讀佛教書籍的廣大社會讀者,能夠沒有文字與概念兩重障礙的容易理解其書內容。這也是木村的著作在當時日本社會上最暢銷、迴響最大,遠遠超越當時日本其他專業佛教學者,其原因在此。
然而,或許有些本書的讀者會質疑:上述本文的解說,真的符合木村本人的原有意圖嗎?我的回答是,其根據主要是來自木村在《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的序言中幾段自白:
對於阿含思想作組織性的論理的論述,尤其論及彼與時代精神交涉的方面,可以說筆者意在組成一種新形式的阿毘達磨論書。
關於原始佛教雖有種種研究,但對於思想上的處理,大抵只是就經典文句的表面作解釋,如同昔時阿毘達磨論師之所為,大多未能推至其內在的意義。更且昔時阿毘達磨論師雖以阿含部聖典(以及律部)為其基礎,但僅止於從種種觀點揭示其根本主張,大抵欠缺批判的精神,對於問題所在,經常是詳其末節卻失其大體,就今日而言,其不足之處實是不少。
因此,本書所採取的立場是,雖也採用昔時阿毘達磨論師之精神,但立於今日學問的見地,直接探究原始佛教思想,又為避免煩瑣,故僅止於闡明其根本立腳地而已。如是的研究法,在原始佛教之研究盛行之今日,至少作為一種見解,應是可以接受的。
基本上,上述的幾段摘述內容,雖是出現在木村《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的序言,但同樣也適用於本書《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情況。讀者過去對於木村著作的思維邏輯常患的一個錯誤,就是按照《木村泰賢全集》六冊先後順序來理解,所以容易對於本書《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論述體系及其所要達成的「新阿毘達摩佛教思想論書」思辨邏輯的作用,無法精確掌握。
事實上,只要細讀《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全書的內容,就會發現木村經常提到之前的《六派哲學》、《原始佛教思想論》與《阿毘達磨論之研究》中的相關章節(現在都改為標明是臺灣商務印書館新譯本的各書出處頁碼)。其原因如下:
一、因為要處理《原始佛教思想論》或《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兩書所涉及與奧義書或前期吠陀文化有所關聯或影響的內容時,就必須先提及《六派哲學》;之後此《原始佛教思想論》的相關內容,又再構成《阿毘達磨論之研究》與《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兩者的論述源流。也就是說,當木村在詮釋《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全書內容時,他其實既論述了思想歷史的發展狀況,也同時將其與時代特有的論書題材,進行了系統性地關聯論述。
就像歷史的佛陀,主要出現在他的《原始佛教思想論》中的簡要介紹;至於神化的佛陀與菩薩的新思維,他就改為放在《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佛陀論〉來進行相關探討。再者,在原始佛教中,眾所周知,佛陀曾拒絕討論宇宙成立要素與現實世間觀的問題,但在《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論述主題中,卻是必須根據原有論書的內容來討論,同時也必須說明其與印度本土早期婆羅門宗教文化的相關性或對比性。因此他就根據這樣的原則來論述與建構其書體系。
二、在東京帝大的現代佛學研究,其實是在「印度哲學」的新學科體系下來進行教學與研究。如此一來,就完全顛覆傳統佛教獨尊與正道的至高神聖地位。可是,明治憲法規定國家神道與天皇至上,作為日本國家精神的神聖象徵。因此,包括日本國內的基督教大學在內,都不能在學校中教導或傳播宗教信仰課程,但是可以教授宗教哲學、宗教歷史或宗教倫理學。於是,東京帝大開設「印度哲學」教學與研究,若與當時的國際學術潮流相比,雖在起步時間上略晚,但在木村擔任第一講座時期,就幾乎同步發展、甚至超前。原因就是日本傳統漢譯佛典的經論教學,不但從古迄今一直持續傳承,而且知識基礎深厚,所以可以成為現代佛學研究的豐富學術資源,反之西方佛教學者由於多數不懂漢文,便無法充分利用。因而,木村的《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之可以超越傳統日本佛學界對於《俱舍論》的研究模式,同時也獲益於此一傳統教學資源,原因在此。
三、至於有關上述這些現代佛學的研究方法與相關批判思辨態度,局部與整體的搭配之間,乃至從歷史研究、教理研究和現代社會實踐之間,如何擇取與思考的大原則問題,他在一九二六年七月於甲子社出版小冊子《佛教研究的大方針》,都有最詳盡的解說。此小冊子是木村前一年在東京都芝區增上寺所舉辨的第一屆東亞佛教大會上所發表的有關現代東亞佛學研究方法學的主題演說全文,而這是木村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初完成其《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全部書稿之前的力作。所以,不難透過此文來了解目前如何從事現代佛學研究的精華思考真相。
但在木村於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凌晨三點突然去世之後,當年七月的《宗教研究》第七卷第四號,出版「木村教授追悼號」,距離他去世還不到二個足月,但仍有眾多相關佛教學者為其撰文悼念。當中,除了木村曾公開在著作批評過他的論述不確的金倉圓照,以及與木村治學路數不太對盤的宮本正尊,兩人之文略有微詞之外,多數都高度肯定木村的學術卓越成就、廣大包容的學者風範、特殊明快行文組織與學術論斷等。其中,特別有一篇是與木村有長期接觸和密切交換學術意見的鈴木宗忠所寫,他談及自己所了解的木村學術研究與建構問題。因木村曾對他提到,他所致力的就是一種「佛教的神學」或者是一種「組織佛教學」的建構。最初,我對這兩個名詞感到很費解,後來我查了日本國會圖書館的相關藏書之後,我就明白了。這是由於木村把原始佛教的經典類比基督教的福音書,於是部派佛教的論書自然等於基督教解釋福音書的神學了。並且,我們還可以明白下列幾種情況:
一、木村的「組織佛教學」,是源自一八九○年由中西牛郎所著的《組織佛教論》一書。中西牛郎著述此書的目的,是要呼籲日本佛教徒與佛教高僧一起思考,如何適應現代世界思潮衝擊處境下的革新認知方式與相關內涵的綱要書,書中有五大篇,列舉各領域所需研究的主題與範圍。由於這是當時唯一的《組織佛教論》著作,所以在其之後的木村所提及「組織佛教學」論述構想及其思維概念,顯然曾受其影響。
二、早在木村之前,姉崎正治雖未標明是「組織佛教學」論述構想及其思維概念,但在其從東大畢業後的初期著作、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印度宗教史考》一書,就是接近此類的論述建構與書寫。之後,一九一三年木村與其師高楠順次郎共著《印度哲學宗教史》一書時,在其序言中所提出的五階段論述構想,本質上只是將姉崎大量吸收當時西方宗教學與印度宗教史的既有成果,寫成長達數千年的古今印度宗教發展史的建構內容,進行五階段的不同主題論述而已。
一八九九年姉崎吸收德國黑格爾左派(Linkshegelianer)的基督教福音聖經批判學的經驗,出版批判性的《佛教聖典史論》一書,書中批判性地檢討原始佛教經典與阿毘達磨論書之間的文獻學複雜交涉問題。此一《佛教聖典史論》批判學研究概念,以及一九一○年出版的《根本佛教》一書,基本上都被木村所追隨。至於一九一○年姉崎譯出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的《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的第一卷時,木村立刻吸收其唯意志中的盲目意志概念,用來解釋原始佛教的無明深層意涵,這就是由叔本華書中繼承下來的。木村並於同年六月、七月兩期的《哲學雜誌》上,首次發表其最具原創性的佛學研究論文〈作為原始佛教歸結點的印度唯意志論的發展歷程概況〉。之後木村於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原始佛教思想論》中,所引爆的最大爭議點,就是關於無明的主知論與唯意志論的不同路線之爭。
三、可是,木村的「組織佛教學」詮釋體系,實際運用上的相關著作典範,其實是來自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的新康德主義(Neo-Kantianism)的領航人之一——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撰寫了當時享譽世界學界的《哲學史教程》(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Tübingen, 1914)一書,以及《近代德意志人的精神生活哲學》(Die Philosophie im deutschen Geistesleben des XIX. Jahrhunderts, Tübingen 1909)一書。由於文德爾班在其《哲學史教程》的副標題上,特別標明是「以哲學問題與哲學概念的形成與發展」為論述主軸,所以木村借鏡於文德爾班在《哲學史教程》的相關哲學史模式,就構成了木村「組織佛教學」詮釋體系的《原始佛教思想論》的類似論述模式,因而木村的《原始佛教思想論》與在他之前主要繼承對象的姉崎著《根本佛教》一書,兩者所以有所不同,就是在法義的論述上,姉崎是根據原始佛教苦、集、滅、道四聖諦來依次論述,木村的《原始佛教思想論》則是採用文德爾班在《哲學史教程》的論述模式。因而,木村雖極大獲益於姉崎《根本佛教》一書的成果,可是卻能展現出自己《原始佛教思想論》獨特論述風貌。
至於文德爾班在其《近代德意志人的精神生活哲學》所探討的類型近代德意志人的哲學不同路線,就成為木村構思《原始佛教思想論》及《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書中分類建構的內容,當然不是全然地複製,而是提供了木村構思全書架構的方向。因而,木村的「組織佛教學」終於在其《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一書,達到最成熟的境界。
目前,在本書新譯本中,從緒論開始的論辯原始佛教思想與阿毘達磨佛教思想之別的學術史檢討,是概括重述木村在其博士論文中的導論成果。然後,按佛、法、僧三者的先後順序,開始展開各種神化佛陀的辯證歷程,然後是各類菩薩的演變狀況,之後開始討論宇宙構成的要素、世界觀、心理論、倫理論、修道論六大主題。至於如何討論,我在本文之前已提過了,此處不再重複。
假如讀者了解以上的學術史溯源,並將其用來理解在戰後出現於臺灣本土的唯一一本關於部派佛教思想的論師與論書巨著——就是釋印順法師於其高徒演培譯出木村《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第十年——在台北市出版的《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1967)。將其與木村的這本新譯本相比,兩者至少有四大區別:
一、木村全書很少引述長段的論述內容,並且涉及各類名詞或概念時,一定用現代語言解釋。所以全書論述呈現邏輯清楚的思辨歷程,行文流暢、易懂、知識性廣而精要、現代感與親切感十足交織。
二、木村有討論各種神化佛陀的辯證歷程,然後是各類菩薩的演變狀況,之後開始討論宇宙構成的要素、世界觀、心理論、倫理論、修道論六大主題。反之,印順法師在其《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完全不涉及各種神化佛陀的辯證歷程或菩薩各種化身狀況,而是在其之後出版的《初期大乘的起源與開展》一書,才納入這些主題。至於世界觀、心理論的部分,《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也幾乎不涉及。
三、木村的書,是在世界性的佛教研究潮流中,展開自己的第一線體系性論述。印順法師除了幾處引述木村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的幾條資料之外,最倚重的是他自己的解讀。
四、木村的書容易讀,印順法師的書,除了特別厲害的佛教學者之外,多數讀者讀後,除會一再讚嘆之外,幾乎無從對其有所評論。
所以,在本文的最後,我建議讀者將兩書都找來讀一讀,就知道我以上所說有無道理。
江燦騰(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
前東京帝大第一「印度哲學」講座教授木村泰賢原著的《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新譯本,同樣是由臺灣專譯日本佛學名著的釋依觀比丘尼翻譯完成,同樣由我推薦給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所以新到任不久的張曉蕊總編輯,也同意由我為此新譯本寫一篇導讀之文。
不過這已是我為木村在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第五本新譯本寫介紹文了,所以我想在此新譯本解說文中,提供給本書讀者更多與本書相關的學術史溯源解說。因為幾十年來的實際接觸與教學研究經驗,讓我深深感到當代臺灣佛教界信仰活動高度興盛之後的認知隱憂:極度缺乏對佛學教理具有現代理解的問題意識與相關佛教思維的學術史認知。因而才導致臺灣當代很多熱門佛教團體或組織,多數信徒就會因其被一再洗腦而逐漸形成對於指導者無條件的深度信仰認同,同時也讓其本身成為特定信仰意識形態的行為操縱,令人為之扼腕與嘆息。所以,在本文的解說中,我希望能提供一些有關木村本書新譯本的學術史溯源之歷史認知,讓有志者得以有所借鏡。
讀者須知,本書原著是屬於印度佛教的時期,介於原始佛教與大乘佛教之間,歷時約五百年左右的──部派分裂時期的各種佛教詮釋教理──以現代性體系呈現的新詮釋論書。或者我們可以說,這是有關部派佛教時期最著名的現代型教理概論著作:它是如同北傳的世親著《俱舍論》或如南傳的覺音著《清淨道論》那樣經典等級的作品,二十世紀現代版新綜合詮釋論書。因而,木村泰賢的生命後期,主要的體系性教理著作,就是這本全書草稿完成於一九二六年一月九日晚上的《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
但是,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凌晨三點,木村突然心肌梗塞猝逝時,此一草稿仍未公諸於世,而只是用鉛筆,快速且潦草地寫在教學講義的一堆稿紙上被存放著,木村有可能是還要修訂與增補,所以沒有急著直接出版。
之後,先經由跟他十年之久的女門生正木春枝全部謄寫,再交由木村的研究生西義雄、坂本幸男整合與編輯,並在一些經論引述的出處上,改為出自《大正藏》或《國譯一切經》上的頁碼,於一九三五年先由明治書院出版單行本,書名《小乘佛教思想論》;兩年後,即一九三七年,又再納入同書院出版的《木村泰賢全集》第五冊出版。
不過此處,我必須先提及一個有關此書出版時間的修正問題。因在二○一八年二月出版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新譯本》的解說之文中,我曾把本書的出版時間提早十年,其實是錯誤的,正確應是在一九三五年才首次出版才對。
但是,有關本書的介紹,除了在其納入全集時,曾在書末附有坂本幸男的簡單全書內容介紹之外,之後只有戰後從大陸來臺的釋演培法師,曾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在新竹市福嚴精舍,首次譯出本書中譯本時,根據木村原書的短序內容,將其改寫一篇稍微擴大的譯序之文,並刪去木村原序全文,所以事實上他也沒有增加任何新的解說資訊。
演培法師當時也表示他自己才剛學習日文,而且當時工具書較缺乏,可能因為如此,其譯文才無法將木村著作的精采表現出來。
所以,我才建議由釋依觀比丘尼重譯全書,並同時更正成現在通用的中文譯名,並由我負責重新回溯原書的論述與出版相關歷程的學術史解說。又因本書是木村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的有關教理的綜合解說,所以我建議此次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新譯本時,使用木村的原有書名《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而不要用《小乘佛教思想論》,以免帶有傳統大乘佛教徒,歷來對小乘佛教的貶抑。臺灣商務印書館編輯部也同意了這一改名,讓我深感興奮。但是,同時我要擔負的解說責任,也因此頓感沉重不少。
讀者須知,長期以來,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到當代的東亞現代佛學研究,主要推動重鎮,當數東京帝國大學(現東京大學)的印度哲學研究所。如今我們可以引述當代日本著名東大佛教學者齋藤明教授〔案:齋藤明教授是一九五○年生於日本東京,現任東京大學佛教學教授、國際佛教學會理事,前任日本印度學佛教學會理事長(二○○八年至二○一四年),師從高崎直道、狄雍等著名學者,既有日本傳統的佛教情懷與治學精神,又通達歐洲的學術理念與研究風格,是當代日本佛教學界最具代表性的傑出學者之一〕,於二○一五年五月十七日接受《澎湃新聞》特約記者何歡歡的專訪,他在訪問中談及木村泰賢,看看他對於木村在東京帝大任教時期的巨大學術成就的讚美,以及他對當時號稱「日本佛教學者雙璧」──木村與宇井伯壽──兩者不同思辨風格所做出的客觀比較。齋藤明教授是這麼說的:
最早在現代國立大學裡教授佛教學的是村上專精(生於一八五一年,逝於一九二九年,淨土真宗僧侶)和木村泰賢(生於一八八一年,逝於一九三○年,曹洞宗僧侶)。村上教授是東京帝國大學「印度哲學」教席的第一代教授(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木村教授則早在一九一二年就以講師身分代時任東京帝大梵文學教授的高楠順次郎開設「印度哲學宗教史」課程。一九一七年任助教授,一九二○年赴歐美留學,一九二三年回國後升任「印度哲學」教授。木村教授才華横溢,被公認為最優秀的學者,當時推選他擔任校長的呼聲很高,可惜英年早逝。隨後,木村教授的同門師弟宇井伯壽(生於一八八二年,逝於一九六三年,曹洞宗僧侶)接替了這一教席。相比之下,木村教授研究中的哲學思辨與宗教關懷要比宇井教授強一些,但宇井教授有著非常強烈的語文學(Philology,日語的文獻學之意)情懷,而且研究領域非常廣泛,一手建立起我們這一學科的基本方法論——以語文學為基礎來研究佛教。
由此可見木村在當時堪稱是日本、甚至是全東亞最頂尖的印度佛學思想研究學者之一。他最大的佛教學術貢獻,主要就是能率先開創關於部派佛教論書的文獻學研究。而他之所以能得東大博士學位與能擔當東大的「印度哲學」第一講座教授的原因,就是源自他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一書的著述與出版。
況且,在當時歐洲佛教學者中,能與木村泰賢教授此一研究,進行互相對話與互爭長短的,只有比利時的佛教大學者蒲仙(De la Vallée Poussin)、英國的巴利文佛教論書權威學者戴維斯夫人(Mrs. Rhys Davids)、蘇聯佛教大學者舍爾巴茨基(Theodor Ippolitovich Stcherbatsky)與另一英國名學者凱思(Arthur Berriedale Keith)而已。但只有蒲仙與戴維斯夫人的著作,是早於木村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出版,所以木村在研究中主要的參考著作,就是此兩人的著作。
至於凱思的《印度和錫蘭佛教哲學》(Buddhist philosophy in India and Ceylon,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3)與舍爾巴茨基的《佛教的中心概念與法的意義》(The Central Conception of Buddhism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Dharma”. L., Royal Asiatic soc., 1923, 112 c.,中譯本的書名為《小乘佛學》)都出版於一九二三年,所以是比木村的博士論文出版晚一年。
然而,當木村於一九二六年九月初完成其《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一書的全書草稿時,仍只在書中引用蒲仙與戴維斯夫人的著作,再加上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心理學教授兼哲學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與德國實驗心理學開創者馮特博士(Wilhelm Maximilian Wundt)的相關心理學著作而已。原因是,木村之所以能在日本佛學界率先研究阿毘達磨論中的佛教心理學,主要是受到戴維斯夫人的著作影響,而蒲仙則是開創西方研究部派佛教論書與進行翻譯的最著名學者,因此必須加以引用此兩者之著述,才符合學術常軌做法。但也因此,木村在《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中,才能有那些獨到的佛教心理論解說的相關章節論述。
在此同時,他也另外陸續發表有關佛教心理論解說的論文。由此可知,像此種能夠熟練集合專業化研究與論述普及化兩者,讓其彼此形成相互支援的雙刀流論述模式,木村不但最為擅長,並且盡全力從事。而主要其目的,就是為了讓初入門讀佛教書籍的廣大社會讀者,能夠沒有文字與概念兩重障礙的容易理解其書內容。這也是木村的著作在當時日本社會上最暢銷、迴響最大,遠遠超越當時日本其他專業佛教學者,其原因在此。
然而,或許有些本書的讀者會質疑:上述本文的解說,真的符合木村本人的原有意圖嗎?我的回答是,其根據主要是來自木村在《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的序言中幾段自白:
對於阿含思想作組織性的論理的論述,尤其論及彼與時代精神交涉的方面,可以說筆者意在組成一種新形式的阿毘達磨論書。
關於原始佛教雖有種種研究,但對於思想上的處理,大抵只是就經典文句的表面作解釋,如同昔時阿毘達磨論師之所為,大多未能推至其內在的意義。更且昔時阿毘達磨論師雖以阿含部聖典(以及律部)為其基礎,但僅止於從種種觀點揭示其根本主張,大抵欠缺批判的精神,對於問題所在,經常是詳其末節卻失其大體,就今日而言,其不足之處實是不少。
因此,本書所採取的立場是,雖也採用昔時阿毘達磨論師之精神,但立於今日學問的見地,直接探究原始佛教思想,又為避免煩瑣,故僅止於闡明其根本立腳地而已。如是的研究法,在原始佛教之研究盛行之今日,至少作為一種見解,應是可以接受的。
基本上,上述的幾段摘述內容,雖是出現在木村《原始佛教思想論》一書的序言,但同樣也適用於本書《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情況。讀者過去對於木村著作的思維邏輯常患的一個錯誤,就是按照《木村泰賢全集》六冊先後順序來理解,所以容易對於本書《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論述體系及其所要達成的「新阿毘達摩佛教思想論書」思辨邏輯的作用,無法精確掌握。
事實上,只要細讀《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全書的內容,就會發現木村經常提到之前的《六派哲學》、《原始佛教思想論》與《阿毘達磨論之研究》中的相關章節(現在都改為標明是臺灣商務印書館新譯本的各書出處頁碼)。其原因如下:
一、因為要處理《原始佛教思想論》或《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兩書所涉及與奧義書或前期吠陀文化有所關聯或影響的內容時,就必須先提及《六派哲學》;之後此《原始佛教思想論》的相關內容,又再構成《阿毘達磨論之研究》與《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兩者的論述源流。也就是說,當木村在詮釋《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全書內容時,他其實既論述了思想歷史的發展狀況,也同時將其與時代特有的論書題材,進行了系統性地關聯論述。
就像歷史的佛陀,主要出現在他的《原始佛教思想論》中的簡要介紹;至於神化的佛陀與菩薩的新思維,他就改為放在《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佛陀論〉來進行相關探討。再者,在原始佛教中,眾所周知,佛陀曾拒絕討論宇宙成立要素與現實世間觀的問題,但在《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論述主題中,卻是必須根據原有論書的內容來討論,同時也必須說明其與印度本土早期婆羅門宗教文化的相關性或對比性。因此他就根據這樣的原則來論述與建構其書體系。
二、在東京帝大的現代佛學研究,其實是在「印度哲學」的新學科體系下來進行教學與研究。如此一來,就完全顛覆傳統佛教獨尊與正道的至高神聖地位。可是,明治憲法規定國家神道與天皇至上,作為日本國家精神的神聖象徵。因此,包括日本國內的基督教大學在內,都不能在學校中教導或傳播宗教信仰課程,但是可以教授宗教哲學、宗教歷史或宗教倫理學。於是,東京帝大開設「印度哲學」教學與研究,若與當時的國際學術潮流相比,雖在起步時間上略晚,但在木村擔任第一講座時期,就幾乎同步發展、甚至超前。原因就是日本傳統漢譯佛典的經論教學,不但從古迄今一直持續傳承,而且知識基礎深厚,所以可以成為現代佛學研究的豐富學術資源,反之西方佛教學者由於多數不懂漢文,便無法充分利用。因而,木村的《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之可以超越傳統日本佛學界對於《俱舍論》的研究模式,同時也獲益於此一傳統教學資源,原因在此。
三、至於有關上述這些現代佛學的研究方法與相關批判思辨態度,局部與整體的搭配之間,乃至從歷史研究、教理研究和現代社會實踐之間,如何擇取與思考的大原則問題,他在一九二六年七月於甲子社出版小冊子《佛教研究的大方針》,都有最詳盡的解說。此小冊子是木村前一年在東京都芝區增上寺所舉辨的第一屆東亞佛教大會上所發表的有關現代東亞佛學研究方法學的主題演說全文,而這是木村在一九二六年九月初完成其《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全部書稿之前的力作。所以,不難透過此文來了解目前如何從事現代佛學研究的精華思考真相。
但在木村於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凌晨三點突然去世之後,當年七月的《宗教研究》第七卷第四號,出版「木村教授追悼號」,距離他去世還不到二個足月,但仍有眾多相關佛教學者為其撰文悼念。當中,除了木村曾公開在著作批評過他的論述不確的金倉圓照,以及與木村治學路數不太對盤的宮本正尊,兩人之文略有微詞之外,多數都高度肯定木村的學術卓越成就、廣大包容的學者風範、特殊明快行文組織與學術論斷等。其中,特別有一篇是與木村有長期接觸和密切交換學術意見的鈴木宗忠所寫,他談及自己所了解的木村學術研究與建構問題。因木村曾對他提到,他所致力的就是一種「佛教的神學」或者是一種「組織佛教學」的建構。最初,我對這兩個名詞感到很費解,後來我查了日本國會圖書館的相關藏書之後,我就明白了。這是由於木村把原始佛教的經典類比基督教的福音書,於是部派佛教的論書自然等於基督教解釋福音書的神學了。並且,我們還可以明白下列幾種情況:
一、木村的「組織佛教學」,是源自一八九○年由中西牛郎所著的《組織佛教論》一書。中西牛郎著述此書的目的,是要呼籲日本佛教徒與佛教高僧一起思考,如何適應現代世界思潮衝擊處境下的革新認知方式與相關內涵的綱要書,書中有五大篇,列舉各領域所需研究的主題與範圍。由於這是當時唯一的《組織佛教論》著作,所以在其之後的木村所提及「組織佛教學」論述構想及其思維概念,顯然曾受其影響。
二、早在木村之前,姉崎正治雖未標明是「組織佛教學」論述構想及其思維概念,但在其從東大畢業後的初期著作、一八九八年出版的《印度宗教史考》一書,就是接近此類的論述建構與書寫。之後,一九一三年木村與其師高楠順次郎共著《印度哲學宗教史》一書時,在其序言中所提出的五階段論述構想,本質上只是將姉崎大量吸收當時西方宗教學與印度宗教史的既有成果,寫成長達數千年的古今印度宗教發展史的建構內容,進行五階段的不同主題論述而已。
一八九九年姉崎吸收德國黑格爾左派(Linkshegelianer)的基督教福音聖經批判學的經驗,出版批判性的《佛教聖典史論》一書,書中批判性地檢討原始佛教經典與阿毘達磨論書之間的文獻學複雜交涉問題。此一《佛教聖典史論》批判學研究概念,以及一九一○年出版的《根本佛教》一書,基本上都被木村所追隨。至於一九一○年姉崎譯出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的《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的第一卷時,木村立刻吸收其唯意志中的盲目意志概念,用來解釋原始佛教的無明深層意涵,這就是由叔本華書中繼承下來的。木村並於同年六月、七月兩期的《哲學雜誌》上,首次發表其最具原創性的佛學研究論文〈作為原始佛教歸結點的印度唯意志論的發展歷程概況〉。之後木村於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原始佛教思想論》中,所引爆的最大爭議點,就是關於無明的主知論與唯意志論的不同路線之爭。
三、可是,木村的「組織佛教學」詮釋體系,實際運用上的相關著作典範,其實是來自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的新康德主義(Neo-Kantianism)的領航人之一——文德爾班(Wilhelm Windelband)撰寫了當時享譽世界學界的《哲學史教程》(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 Tübingen, 1914)一書,以及《近代德意志人的精神生活哲學》(Die Philosophie im deutschen Geistesleben des XIX. Jahrhunderts, Tübingen 1909)一書。由於文德爾班在其《哲學史教程》的副標題上,特別標明是「以哲學問題與哲學概念的形成與發展」為論述主軸,所以木村借鏡於文德爾班在《哲學史教程》的相關哲學史模式,就構成了木村「組織佛教學」詮釋體系的《原始佛教思想論》的類似論述模式,因而木村的《原始佛教思想論》與在他之前主要繼承對象的姉崎著《根本佛教》一書,兩者所以有所不同,就是在法義的論述上,姉崎是根據原始佛教苦、集、滅、道四聖諦來依次論述,木村的《原始佛教思想論》則是採用文德爾班在《哲學史教程》的論述模式。因而,木村雖極大獲益於姉崎《根本佛教》一書的成果,可是卻能展現出自己《原始佛教思想論》獨特論述風貌。
至於文德爾班在其《近代德意志人的精神生活哲學》所探討的類型近代德意志人的哲學不同路線,就成為木村構思《原始佛教思想論》及《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書中分類建構的內容,當然不是全然地複製,而是提供了木村構思全書架構的方向。因而,木村的「組織佛教學」終於在其《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一書,達到最成熟的境界。
目前,在本書新譯本中,從緒論開始的論辯原始佛教思想與阿毘達磨佛教思想之別的學術史檢討,是概括重述木村在其博士論文中的導論成果。然後,按佛、法、僧三者的先後順序,開始展開各種神化佛陀的辯證歷程,然後是各類菩薩的演變狀況,之後開始討論宇宙構成的要素、世界觀、心理論、倫理論、修道論六大主題。至於如何討論,我在本文之前已提過了,此處不再重複。
假如讀者了解以上的學術史溯源,並將其用來理解在戰後出現於臺灣本土的唯一一本關於部派佛教思想的論師與論書巨著——就是釋印順法師於其高徒演培譯出木村《阿毘達磨佛教思想論》的第十年——在台北市出版的《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1967)。將其與木村的這本新譯本相比,兩者至少有四大區別:
一、木村全書很少引述長段的論述內容,並且涉及各類名詞或概念時,一定用現代語言解釋。所以全書論述呈現邏輯清楚的思辨歷程,行文流暢、易懂、知識性廣而精要、現代感與親切感十足交織。
二、木村有討論各種神化佛陀的辯證歷程,然後是各類菩薩的演變狀況,之後開始討論宇宙構成的要素、世界觀、心理論、倫理論、修道論六大主題。反之,印順法師在其《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完全不涉及各種神化佛陀的辯證歷程或菩薩各種化身狀況,而是在其之後出版的《初期大乘的起源與開展》一書,才納入這些主題。至於世界觀、心理論的部分,《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也幾乎不涉及。
三、木村的書,是在世界性的佛教研究潮流中,展開自己的第一線體系性論述。印順法師除了幾處引述木村的《阿毘達磨論之研究》的幾條資料之外,最倚重的是他自己的解讀。
四、木村的書容易讀,印順法師的書,除了特別厲害的佛教學者之外,多數讀者讀後,除會一再讚嘆之外,幾乎無從對其有所評論。
所以,在本文的最後,我建議讀者將兩書都找來讀一讀,就知道我以上所說有無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