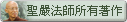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遊心法海六十年 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合刊
作者:印順導師
出版社:正聞出版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5x21cm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50250371
ISBN:9789570366471
定價:NT$120
會員價:NT$102 (85折)
已搶購一空
目前無法購買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二 修學之歷程
↑TOP
一 暗中摸索
六十年的漫長歲月,我在佛法中的進修,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
十四年(二十歲),我讀到馮夢楨的『莊子序』:「然則莊文、郭注,其佛 法之先驅耶」,而引起了探究佛法的動機。出家前的我,生活圈子極小,不知佛 法到底是什麼。探求佛法,只能到附近幾處小廟中去求,得到了『金剛經石(成 金)注』,『龍舒淨土文』,『人天眼目』殘本等。前二部,讀了有點了解,卻 覺得意義並不相同。讀了『人天眼目』,只知禪宗有五家宗派而已。無意中,在 商務印書館的目錄中,發現有佛書,於是購到了『成唯識論學記』,『相宗綱要 』,『三論宗綱要』。因『三論宗綱要』而知道三論,設法購得『中論』與『三 論玄義』;其後又求到了嘉祥的三論疏。我沒有良好的國文基礎,卻修學這精深 的法門,艱苦是可想而知的!記得初讀『中論』(青目注本),可說完全不了解。然而,不了解所以更愛好,只怪自己的學力不足,佛法是那樣的高深,使我嚮 往不已!那時,不知道佛法有辭典。在商務本的『辭源』中,發現佛法的術語極 多,但沒有錢買,就一條條的摘錄下來。經過這一番抄錄,對一般佛學常識,倒 大有幫助,但這樣的費時費力,簡直是愚不可及!我的修學佛法,一切在摸索中 進行,沒有人指導,讀什麼經論,是全憑因緣來決定的。一開始,就以三論、唯 識法門為探究對象,當然事倍而功半。經四、五年的閱讀思惟,多少有一點了解 ,也就發現了:佛法與現實佛教界間的距離。我的故鄉,寺廟中的出家人(沒有 女眾),沒有講經說法的,有的是為別人誦經、禮懺;生活與俗人沒有太多的差 別。在家信佛的,只是求平安,求死後的幸福。少數帶髮的女眾,是「先天」、 「無為」等道門,在寺廟裏修行,也說他是佛教。理解到的佛法,與現實佛教界 差距太大,這是我學佛以來,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這到底是佛法傳來中國,年 代久遠,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變質?還是在印度就是這樣──高深的法義,與通 俗的迷妄行為相結合呢!我總是這樣想:鄉村佛法衰落,一定有佛法興盛的地方 。為了佛法的信仰,真理的探求,我願意出家,到外地去修學。將來修學好了, 宣揚純正的佛法。當時意解到的純正佛法,當然就是三論與唯識。
二 求法閱藏
十九年秋天,我在普陀山福泉庵出家了。一般的寺院,是不可能專心修學的 ,修學也沒有人指導。所以二十年春天,在師長的同意下,到廈門閩南佛學院求 學。院長是太虛大師,而實際的主持者,是大醒、芝峰二位法師。一學期中,聽 了『三論玄義』,『雜集論』與『俱舍論』的小部分,就因病而休學了。在家時 的暗中摸索,是從三論、唯識入門的;恰好那時的閩院,也著重三論與唯識,所 以在這一學團中,思想非常契合。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對我有重大的啟發性 。讀『大乘宗地引論』與『佛法總抉擇談』,對虛大師博通諸宗而加以善巧的融 會貫通,使我無限的佩服。我那年的創作──『抉擇三時教』,對於智光的三時 教,唯識宗的三時教,抉擇而予以融貫,就是學習虛大師的融貫手法。民國以來 ,由於「南歐(陽漸)北韓(清淨)」的提倡唯識,唯識宗受到了學界的重視。虛大師的思想,根源在『楞嚴』、『起信』,但也推重法相唯識,所以說:知「 整僧之在律,而攝化學者世間,需以法相」(『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書後』); 「立言善巧,建義顯了,以唯識為最」(『起信論唯識釋』)。梅光羲作『相宗 新舊二譯不同論』,虛大師有『書後』,都推重玄奘的新譯。鎮江守培長老,作 『讀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之意見』,以為舊的相宗(「地論」,「攝論」)都對 ,新的相宗都不對。不但玄奘不對,窺基不對,說「護法妄立有宗」,連世親菩 薩也有問題。在同學們不滿守老的氣氛下,我起來反駁,寫了長篇的『評破守培 上人讀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之意見』,為唯識宗作辯護者,當然是新的都對,舊 的都不對。虛大師的融貫善巧,我是由衷欽佩的;但對內學院刊行的『內學』, 梁啟超的『起信論考證』,也有濃厚的興趣。對於大乘佛法,我贊同內學院的見 解,只有法性(三論)與法相(唯識)二宗。虛大師所提倡的佛教改革運動,我 原則上是贊成的,但覺得不容易成功。出家以來,多少感覺到,現實佛教界的問 題,根本是思想問題。我不像虛大師那樣,提出「教理革命」;卻願意多多理解教理,對佛教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
那年下學期,住福建名剎──鼓山湧泉寺。年底回閩院,醒公命我為同學們 講『十二門論』。由於相宗二譯不同論的論辯,漸漸引起了自己內心的反省:這 是千百年來的老問題,舊譯與新譯的思想對立,難道都出於譯者的意見?還是遠 源於印度論師的不同見解,或論師所依的經典不同呢?這是佛法中的大問題,我 沒有充分理解,又那裏能夠決了!同時偶然的因緣,引起自己的警覺:我是發心 求法而來的,學不到半年,就在這裏當法師,未免不知慚愧!覺得不能老是這樣 下去,還是自求充實的好。就這樣,離開廈門而回到了普陀。
從二十一年夏天,到二十五年年底,除了在武昌佛學院(那時名義是「世界 佛學苑圖書館」)專修三論章疏半年,又到閩院半年,及其他事緣外,都住在普 陀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足足有三年。那時候,看大藏經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 。這裏的環境,是這一生中覺得最理想的。白天閱讀大藏經,晚上還是研讀三論 與唯識。三年閱藏的時間,對我來說,實在所得不多。因為清刻的大藏經,七千餘卷,每天要讀七、八卷(每卷平均約九千字)。這只是快讀一遍,說不上思惟 、了解。記憶力不強的我,讀過後是一片茫然。不過閱藏也還是有所得的:從所 讀的大藏經中,發見佛法的多采多姿,真可說「百花爭放」,「千巖競秀」!這 是佛教的大寶藏,應該是探求無盡的。知道法門廣大,所以不再局限於三論與唯 識。對於大乘佛法,覺得虛大師說得對,應該有「法界圓覺」一大流。大乘經不 是論書那樣的重於理論,到處都勸發修持,是重於實踐的。還有,讀到『阿含經 』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而不如部分大乘經,表現於 信仰與理想之中。這對於探求佛法的未來動向,起著重要的作用。
二十六年上學期,住在武昌佛學院。讀到了日本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合編 的『印度哲學宗教史』;木村泰賢著的『原始佛教思想論』;還有墨禪所譯的, 結城令聞所著的,關於心意識的唯識思想史(書名已記不清,譯本也因戰亂而沒 有出版)。這幾部書,使我探求佛法的方法,有了新的啟發。對於歷史、地理、 考證,我沒有下過功夫,卻有興趣閱讀。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與流變,漸成為我探求佛法的方針。覺得惟有這樣,才能使佛法與中國現 實佛教界間的距離,正確的明白出來。
三 思想確定
二十七年七月,因日軍的逐漸逼近武漢,到了四川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身 體雖比前更差,不過多住在山上,環境與氣候好些,身體也覺得舒服些。二十九 年,住貴陽的大覺精舍。三十年初秋到三十三年夏天,住四川合江的法王學院。 三十五年春天,離開了四川,先後安住在縉雲山的,約有四年。這次離川,與演 培、妙欽同行,經西北公路而東返的。因病在開封佛學社住了三個月,等到想動 身時,蘭封的鐵路被八路破壞了,不得不折返武昌。三十六年正月,回到了江浙 ,遇上了虛大師的圓寂。為了編纂『太虛大師全書』,住奉化雪竇寺一年餘。三 十七年,住杭州香山洞半年;冬天到了廈門南普陀寺。三十八年夏天,到了香港 。四十一年秋天,又離香港到臺灣。從入川到來臺,共有十四年。這是國家動亂 多難的十四年!而我,是身體最虛弱(曾虛脫三次),生活最清苦,行止最不定,而也是寫作最勤、講說最多的十四年。
一、二十九年,讀到虛大師所講的:『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教』,『我的佛教 改進運動略史』,『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每篇都引起我深深的思惟 。大師分佛教為三期,所說的「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依天 乘行果」,不就是大師所說:「融攝魔梵(天),漸喪佛真之泛神(天)秘密乘 」(『致常惺法師書』)嗎?「中國所說的是大乘教,但所修的卻是小乘行」, 為什麼會如此?思想與行為,真可以毫無關聯嗎!在大師的講說中,得到了一些 新的啟發,也引起了一些新的思考。我雖然曾在佛學院求學,但我的進修,主要 是自修。虛大師給我思想上的啟發,也是從文字中來的。自從在漢藏教理院,遇 到了法尊法師,才覺得有同學之樂。法尊法師是我的老學長,讀他從藏文譯出的 :『菩提道次第廣論』,『辨了義不了義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現觀莊 嚴論略釋』,月稱的『入中論』等,可說得益不少!空宗為什麼要說緣起是空, 唯識宗非說依他起是有不可,問題的根本所在,才有了進一步的理解。我為『密宗道次第廣論』潤文,也就請問過、討論過裏面的一些問題。問問西藏佛教,修 學的情形,甚至談到「飲智慧湯」(活佛的小便),「捉妖」等怪事,也增長知 識不少。有兩點不妨一提:一、由於我的請求,譯出了『七十空性論』,論中有 一段文字,文義前後不相合,經審細推究,斷定藏文原典有了「錯簡」。將這段 文字移在前面,就完全吻合了。二、他編寫『西藏政教史』(書名已記不明白) ,從達朗瑪滅法到西藏佛法重興,這中間的年代,對照中國歷史,始終不能配合 。原來他所依的西藏史料,是以干支紀年的,中間空了六十年,無話可說。如中 間多六十年,那麼西藏所記的年代(干支),就與中國的完全相合了。法尊法師 的記憶力強,理解力也強,是我一生中得益很多的學長。他的思想,已經西藏佛 教化了,與我的意見,距離得非常遠,但彼此對論,或者辯詰,從沒有引起不愉 快,這是值得珍視的友誼!
二、在這長期動亂不安中,我開始成部的寫作,與講說而由別人記錄成書。 一方面,有幾位同學──演培、續明、妙欽他們,希望我作些課外的講說;一方面,是我對全體佛法的看法,逐漸凝定,也有了表示意見的意欲。如三十年所寫 的『佛在人間』,『佛教是無神論的宗教』,『法海探珍』,都是闡揚佛法的人 間性,反對天(神)化;探求佛法本質,而捨棄過了時的方便。「佛法與現實佛 教界有距離」,是一向存在於內心的問題。出家來八年的修學,知道為中國文化 所歪曲的固然不少,而佛法的漸失本真,在印度由來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所 以不能不將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這一時期的寫作與講說,也就重在分 別解說,確定印度經論本義,並探求其思想的演化。當時,我分大乘法義為三論 ──性空唯名論,虛妄唯識論,真常唯心論。這一分類,大致與虛大師的大乘三 宗──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相同。在『法海探珍』中,曾以三 法印──諸法無我,諸行無常,涅槃寂靜,作為三系思想的不同所依。著重於三 系的分解,所以寫的與講的,著重於此。如屬於性空唯名論的,有『金剛般若波 羅蜜經講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中觀論頌講記』,『中觀今論』,『性空學探源』。屬於虛妄唯識論的,有『攝大乘論講記』,『唯識學探源』,『解深密經』。屬於真常唯心論的,有『勝鬘經講記』,『大乘起信論講記』,『阿跋多羅楞伽寶經』。我在師友間,是被看作三論宗的,而第一部寫作,是 『唯識學探源』;第一部講錄成書的,是『攝大乘論講記』,這可以證明一般的 誤解了!在所講的經中,『解深密經』僅講『勝義了義』章,在演培的『解深密 經語體釋』裏,可能含有我的部分意見。『楞伽經』,沒有講圓滿。後來在臺灣 又講了二次,應該有記錄,但沒有成書。現在僅保留我對『楞伽』全經的科判 ──五門,二十章,五十一節的名目。我的講解,從不會拈出一字一句,發揮自 己的高見,也沒有融會貫通。雖然所說的未必正確,但只希望闡明經論的本義。 為了理解三系經論的差別,所以講解時,站在超宗派的立場,而不是照著自己的 見解去解釋一番。以現在的理解來說,『性空學探源』一書,雖搜集了不少資料 ,而說到「探源」,似乎差一點!
三、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根源與流變,就不能不注意到 佛教的史地。大乘三系,也還是開展、流行、演化於某時某地的。妙欽編了一部『中國佛教史略』,我加以補充修正,使中國佛教史與印度佛教史相關聯,作為 二人的合編。從佛教典籍中,論證釋迦族是屬於印度東方的,所以是東方的沙門 文化,有反對印度阿利安人傳統的真常梵我論的特性,這就是『佛教之興起與東 方印度』一文的主要意義。『太虛大師年譜』,是近代佛教大師,有關近代中國 佛教的種種史實。最重要的一部,當然是三十一年所寫的『印度之佛教』。印度 佛教史的流變,我分判為五期:一、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二、菩薩傾向之聲聞 分流;三、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四、如來傾向之菩薩分流;五、如來為本之梵 佛一體。印度佛教的先後五期,從創立到衰滅,正如人的一生,自童年、少年、 壯年、老年到死亡。我以為,佛法不能沒有方便,不能不求時地的適應,但「對 於方便,或為正常之適應,或為畸形之發展,或為毒素之羼入,必嚴為料簡,正 不能率以方便二字混濫之」。覺得「中國佛教,為圓融、方便、真常、唯心、他 力、頓證之所困,已奄奄無生氣;神秘、欲樂之說,自西(康、藏)而東,又日 有泛濫之勢」(『自序』)。『印度之佛教』是史的敘述,但不只是敘述,而有評判取捨的立場。所以這部書的出版,有人同情,也有人痛恨不已。不過痛恨者 ,只是在口頭傳說中咒咀,而真能給以批評的,是虛大師與王恩洋居士(還有教 外人一篇)。我稱印度佛教末期為「佛梵一體」,與虛大師所判攝的「依天乘行 果」,大致相同。虛大師的批評重心在:我以人間的佛陀──釋迦為本;以性空 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三系,為大乘佛法的開展與分化。而虛大師是大 乘別有法源(在『阿含經』以外)的,是中國佛教傳統,以『楞嚴』、『起信』 等為準量,也就是以真常唯心──法界圓覺為根本的。虛大師所以主張,『大乘 起信論』造於龍樹『中論』等以前,以維持真常唯心為大乘根本的立場。不過, 說『起信論』的造作,比龍樹作『中論』等更早,怕不能得到研究佛教史者的同 意!其實,我對印度的佛教,也不是揚龍樹而貶抑他宗的。我是說:「佛後之佛 教,乃次第發展而成者。其方便之適應,理論之闡述,如不適於今者,或偏激者 ,或適應低級趣味者,則雖初期者猶當置之,況龍樹論乎?乃至後之密宗乎!其 正常深確者,適於今者,則密宗而有此,猶當取而不捨,而況真常系之經論乎!其取捨之標準,不以傳於中國者為是,不以盛行中國者為是,著眼於釋尊之特見 、景行,此其所以異(於大師)乎」(『敬答議印度佛教史』)!存有揚清抑濁 ,淘沙取金的意趣,沒有說千百年來所傳,一切都是妙方便,這就難怪有人要不 滿了。王恩洋是著名的唯識學者,他不滿真常唯心論,稱之為「入篡正統」,那 是不承認他是佛法的。對於末期的秘密乘,當然沒有好感。他所以要批評『印度 之佛教』,只是為了辨論空宗與有宗,誰是了義的,更好的。我寫了『空有之間 』,以表示我的意見。以上幾種,都是自己寫作的。
四、我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中說:「立本於根本(即初期)佛教之 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 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那時,我多讀「阿含」、「戒律」、「阿毘達磨 」,不滿晚期之神秘欲樂,但立場是堅持大乘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錫 蘭等南方佛教,以為他們所傳的三藏,是王舍城結集的原本;以為大乘佛教,是 印度教化的,非佛說的。這種意見,多少傳入當時的抗戰後方,而引起某些人的疑惑。我為續明他們,討論這個問題,後來題為『大乘是佛說論』(依現在看來 ,說得不太完善)。慧松法師留學錫蘭返國,法舫法師在錫蘭邊學邊教,都有以 傳入錫蘭的為純正佛法,而輕視印度所有,傳入中國佛教的傾向。所以為慧松寫 『!2扆!2菨文集序』,表示我的意見;因法舫法師而寫『與巴利語系學者論大乘』。 我到臺灣來,有人說我反對大乘,那不是惡意,就是誤會了!
五、大乘佛法,我以性空為主,兼攝唯識與真常。在精神上、行為上,倡導 青年佛教與人間佛教。在歷史上,大乘佛教的開展,確與青年大眾有關。所以依 『華嚴經』的「入法界品」,善財童子的求法故事,寫了一部『青年佛教與佛教 青年』。(現在編入『妙雲集』,已分為三部分:『青年佛教運動小史』,『青 年佛教參訪記』,『雜華雜記』)。不過我所說的青年佛教,是:「菩薩不是不 識不知的幼稚園(生)。……青年佛教所表現的佛教青年,是在真誠、柔和、生 命力充溢的情意中,融合了老年的人生的寶貴經驗」(『雜華雜記』)。因為, 如對佛法缺乏正確而深刻的勝解,那末青年佛教的勇往直前,隨宜方便,不可避免的會落入俗化與神化的深坑。虛大師說「人生佛教」,是針對重鬼重死的中國 佛教。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勢異常嚴重,也嚴重影響到中國佛教,所 以我不說「人生」而說「人間」。希望中國佛教,能脫落神化,回到現實的人間 。我講「人間佛教」,現存『人間佛教緒言』,『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 ,『人性』,『人間佛教要略』。在預想中,這只是全部的「序論」,但由於離 開了香港,外緣紛繁,沒有能繼續講出。
六、三十三年下學期,在漢藏教理院講『阿含講要』。第一章「阿含經之判 攝」,提出了四『阿含經』的不同宗趣,這就是龍樹「四悉檀」的依據。這表示 了四部「阿含」的編集方針:『雜阿含經』是「第一義悉檀」,其他的或重在「 對治」,或重在啟發的「為人生善」,或是適應印度宗教以誘化「世間」。當時 所講的,主要是境相部分。三十八年在廈門,刪去第一章,自己補寫了幾章,說 明聲聞與菩薩的行果,改名為『佛法概論』。這部書,依『阿含經』;依龍樹所 決了的「阿含」深義,明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又補入龍樹所說的菩薩道──二道,五菩提。另一部『淨土新論』,是依虛大師所說:「淨為三乘共庇」,說明 佛法中的不同淨土。在「往生淨土」以外,還有「人間淨土」與「創造淨土」。 這對只要一句彌陀聖號的行者,似乎也引起了反感!
七、我的寫作,一向重於自己對佛法的理解,不大歡喜批評別人,但在這一 階段的後期,寫了三篇不太短的批評文字。一、『佛滅紀年抉擇談』:有人依『 眾聖點記』等,主張佛滅年代,以錫蘭所傳的,阿育王登位於佛滅二百十八年說 為可信。我以為:阿育王的年代,是可以考信的。從佛滅到阿育王,錫蘭所傳, 中國所傳──阿育王登位於佛滅百十六年,都只是佛弟子間的傳說如此。說到『 眾聖點記』,佛滅以來,起初並沒有書寫的戒本,試問每年結夏終了,又在那裏 去下這一點?我不滿一般偏重外來的傳說,所以加以評論,而取中國固有的傳說 。這可說是對誇大南傳的巴利語系,輕視中國所傳而引起的反感。來臺灣後,知 道還有古老的上座部所傳,阿育王登位於佛滅百六十年說,這也許更恰當些。二 、『僧裝改革評議』:當時,有人遊化錫蘭、緬甸,所以主張出家人的服色,應該一色黃,而評中國僧服為「奇形怪狀」。有些僧青年,主張廢棄固有「腐敗落 伍」的,改為與俗服沒有明顯差別的服裝。這可能造成「進(山)門做和尚,出 門充俗人的流弊」,所以寫了這篇評議。我以為,中國固有僧服的顏色,是合於 律制的,黃色只是一宗一派的服色。僧服是可以改革的,但必須合乎律制的原則 ──對外差別而表顯僧相,對內統一以表示平等。其實,僧裝改革只是形式的改 變,並不能促成僧界的清淨,佛教的復興!三、『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熊先 生的『新唯識論』,在哲學與儒學的立場,自有其地位;道不同,用不著評論。 但他在書中,一再的批評唯識與空宗。其實他所知道的空,是唯識學者──有宗 所說的空,根本不知道空宗是什麼。特別是:他的思想,如他自己所說:「大易 其至矣乎,是新論所取正也」。這明明是儒學;佛法的唯識與(唯識家所說的) 空,只是評破的對象。他卻偏要說:「本書於佛家,元屬創作」;「新論從佛學 演變而來,說我是新的佛家亦無不可耳」!這種淆混視聽的故弄玄虛,引起我評 論的決心。
六十年的漫長歲月,我在佛法中的進修,經歷了幾個不同的階段。
十四年(二十歲),我讀到馮夢楨的『莊子序』:「然則莊文、郭注,其佛 法之先驅耶」,而引起了探究佛法的動機。出家前的我,生活圈子極小,不知佛 法到底是什麼。探求佛法,只能到附近幾處小廟中去求,得到了『金剛經石(成 金)注』,『龍舒淨土文』,『人天眼目』殘本等。前二部,讀了有點了解,卻 覺得意義並不相同。讀了『人天眼目』,只知禪宗有五家宗派而已。無意中,在 商務印書館的目錄中,發現有佛書,於是購到了『成唯識論學記』,『相宗綱要 』,『三論宗綱要』。因『三論宗綱要』而知道三論,設法購得『中論』與『三 論玄義』;其後又求到了嘉祥的三論疏。我沒有良好的國文基礎,卻修學這精深 的法門,艱苦是可想而知的!記得初讀『中論』(青目注本),可說完全不了解。然而,不了解所以更愛好,只怪自己的學力不足,佛法是那樣的高深,使我嚮 往不已!那時,不知道佛法有辭典。在商務本的『辭源』中,發現佛法的術語極 多,但沒有錢買,就一條條的摘錄下來。經過這一番抄錄,對一般佛學常識,倒 大有幫助,但這樣的費時費力,簡直是愚不可及!我的修學佛法,一切在摸索中 進行,沒有人指導,讀什麼經論,是全憑因緣來決定的。一開始,就以三論、唯 識法門為探究對象,當然事倍而功半。經四、五年的閱讀思惟,多少有一點了解 ,也就發現了:佛法與現實佛教界間的距離。我的故鄉,寺廟中的出家人(沒有 女眾),沒有講經說法的,有的是為別人誦經、禮懺;生活與俗人沒有太多的差 別。在家信佛的,只是求平安,求死後的幸福。少數帶髮的女眾,是「先天」、 「無為」等道門,在寺廟裏修行,也說他是佛教。理解到的佛法,與現實佛教界 差距太大,這是我學佛以來,引起嚴重關切的問題。這到底是佛法傳來中國,年 代久遠,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變質?還是在印度就是這樣──高深的法義,與通 俗的迷妄行為相結合呢!我總是這樣想:鄉村佛法衰落,一定有佛法興盛的地方 。為了佛法的信仰,真理的探求,我願意出家,到外地去修學。將來修學好了, 宣揚純正的佛法。當時意解到的純正佛法,當然就是三論與唯識。
二 求法閱藏
十九年秋天,我在普陀山福泉庵出家了。一般的寺院,是不可能專心修學的 ,修學也沒有人指導。所以二十年春天,在師長的同意下,到廈門閩南佛學院求 學。院長是太虛大師,而實際的主持者,是大醒、芝峰二位法師。一學期中,聽 了『三論玄義』,『雜集論』與『俱舍論』的小部分,就因病而休學了。在家時 的暗中摸索,是從三論、唯識入門的;恰好那時的閩院,也著重三論與唯識,所 以在這一學團中,思想非常契合。虛大師的「人生佛教」,對我有重大的啟發性 。讀『大乘宗地引論』與『佛法總抉擇談』,對虛大師博通諸宗而加以善巧的融 會貫通,使我無限的佩服。我那年的創作──『抉擇三時教』,對於智光的三時 教,唯識宗的三時教,抉擇而予以融貫,就是學習虛大師的融貫手法。民國以來 ,由於「南歐(陽漸)北韓(清淨)」的提倡唯識,唯識宗受到了學界的重視。虛大師的思想,根源在『楞嚴』、『起信』,但也推重法相唯識,所以說:知「 整僧之在律,而攝化學者世間,需以法相」(『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書後』); 「立言善巧,建義顯了,以唯識為最」(『起信論唯識釋』)。梅光羲作『相宗 新舊二譯不同論』,虛大師有『書後』,都推重玄奘的新譯。鎮江守培長老,作 『讀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之意見』,以為舊的相宗(「地論」,「攝論」)都對 ,新的相宗都不對。不但玄奘不對,窺基不對,說「護法妄立有宗」,連世親菩 薩也有問題。在同學們不滿守老的氣氛下,我起來反駁,寫了長篇的『評破守培 上人讀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之意見』,為唯識宗作辯護者,當然是新的都對,舊 的都不對。虛大師的融貫善巧,我是由衷欽佩的;但對內學院刊行的『內學』, 梁啟超的『起信論考證』,也有濃厚的興趣。對於大乘佛法,我贊同內學院的見 解,只有法性(三論)與法相(唯識)二宗。虛大師所提倡的佛教改革運動,我 原則上是贊成的,但覺得不容易成功。出家以來,多少感覺到,現實佛教界的問 題,根本是思想問題。我不像虛大師那樣,提出「教理革命」;卻願意多多理解教理,對佛教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
那年下學期,住福建名剎──鼓山湧泉寺。年底回閩院,醒公命我為同學們 講『十二門論』。由於相宗二譯不同論的論辯,漸漸引起了自己內心的反省:這 是千百年來的老問題,舊譯與新譯的思想對立,難道都出於譯者的意見?還是遠 源於印度論師的不同見解,或論師所依的經典不同呢?這是佛法中的大問題,我 沒有充分理解,又那裏能夠決了!同時偶然的因緣,引起自己的警覺:我是發心 求法而來的,學不到半年,就在這裏當法師,未免不知慚愧!覺得不能老是這樣 下去,還是自求充實的好。就這樣,離開廈門而回到了普陀。
從二十一年夏天,到二十五年年底,除了在武昌佛學院(那時名義是「世界 佛學苑圖書館」)專修三論章疏半年,又到閩院半年,及其他事緣外,都住在普 陀佛頂山慧濟寺的閱藏樓,足足有三年。那時候,看大藏經是一般人求之不得的 。這裏的環境,是這一生中覺得最理想的。白天閱讀大藏經,晚上還是研讀三論 與唯識。三年閱藏的時間,對我來說,實在所得不多。因為清刻的大藏經,七千餘卷,每天要讀七、八卷(每卷平均約九千字)。這只是快讀一遍,說不上思惟 、了解。記憶力不強的我,讀過後是一片茫然。不過閱藏也還是有所得的:從所 讀的大藏經中,發見佛法的多采多姿,真可說「百花爭放」,「千巖競秀」!這 是佛教的大寶藏,應該是探求無盡的。知道法門廣大,所以不再局限於三論與唯 識。對於大乘佛法,覺得虛大師說得對,應該有「法界圓覺」一大流。大乘經不 是論書那樣的重於理論,到處都勸發修持,是重於實踐的。還有,讀到『阿含經 』與各部廣『律』,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真實感,而不如部分大乘經,表現於 信仰與理想之中。這對於探求佛法的未來動向,起著重要的作用。
二十六年上學期,住在武昌佛學院。讀到了日本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合編 的『印度哲學宗教史』;木村泰賢著的『原始佛教思想論』;還有墨禪所譯的, 結城令聞所著的,關於心意識的唯識思想史(書名已記不清,譯本也因戰亂而沒 有出版)。這幾部書,使我探求佛法的方法,有了新的啟發。對於歷史、地理、 考證,我沒有下過功夫,卻有興趣閱讀。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與流變,漸成為我探求佛法的方針。覺得惟有這樣,才能使佛法與中國現 實佛教界間的距離,正確的明白出來。
三 思想確定
二十七年七月,因日軍的逐漸逼近武漢,到了四川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身 體雖比前更差,不過多住在山上,環境與氣候好些,身體也覺得舒服些。二十九 年,住貴陽的大覺精舍。三十年初秋到三十三年夏天,住四川合江的法王學院。 三十五年春天,離開了四川,先後安住在縉雲山的,約有四年。這次離川,與演 培、妙欽同行,經西北公路而東返的。因病在開封佛學社住了三個月,等到想動 身時,蘭封的鐵路被八路破壞了,不得不折返武昌。三十六年正月,回到了江浙 ,遇上了虛大師的圓寂。為了編纂『太虛大師全書』,住奉化雪竇寺一年餘。三 十七年,住杭州香山洞半年;冬天到了廈門南普陀寺。三十八年夏天,到了香港 。四十一年秋天,又離香港到臺灣。從入川到來臺,共有十四年。這是國家動亂 多難的十四年!而我,是身體最虛弱(曾虛脫三次),生活最清苦,行止最不定,而也是寫作最勤、講說最多的十四年。
一、二十九年,讀到虛大師所講的:『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教』,『我的佛教 改進運動略史』,『從巴利語系佛教說到今菩薩行』,每篇都引起我深深的思惟 。大師分佛教為三期,所說的「依天乘行果趣獲得大乘果的像法時期」,「依天 乘行果」,不就是大師所說:「融攝魔梵(天),漸喪佛真之泛神(天)秘密乘 」(『致常惺法師書』)嗎?「中國所說的是大乘教,但所修的卻是小乘行」, 為什麼會如此?思想與行為,真可以毫無關聯嗎!在大師的講說中,得到了一些 新的啟發,也引起了一些新的思考。我雖然曾在佛學院求學,但我的進修,主要 是自修。虛大師給我思想上的啟發,也是從文字中來的。自從在漢藏教理院,遇 到了法尊法師,才覺得有同學之樂。法尊法師是我的老學長,讀他從藏文譯出的 :『菩提道次第廣論』,『辨了義不了義論』,『密宗道次第廣論』,『現觀莊 嚴論略釋』,月稱的『入中論』等,可說得益不少!空宗為什麼要說緣起是空, 唯識宗非說依他起是有不可,問題的根本所在,才有了進一步的理解。我為『密宗道次第廣論』潤文,也就請問過、討論過裏面的一些問題。問問西藏佛教,修 學的情形,甚至談到「飲智慧湯」(活佛的小便),「捉妖」等怪事,也增長知 識不少。有兩點不妨一提:一、由於我的請求,譯出了『七十空性論』,論中有 一段文字,文義前後不相合,經審細推究,斷定藏文原典有了「錯簡」。將這段 文字移在前面,就完全吻合了。二、他編寫『西藏政教史』(書名已記不明白) ,從達朗瑪滅法到西藏佛法重興,這中間的年代,對照中國歷史,始終不能配合 。原來他所依的西藏史料,是以干支紀年的,中間空了六十年,無話可說。如中 間多六十年,那麼西藏所記的年代(干支),就與中國的完全相合了。法尊法師 的記憶力強,理解力也強,是我一生中得益很多的學長。他的思想,已經西藏佛 教化了,與我的意見,距離得非常遠,但彼此對論,或者辯詰,從沒有引起不愉 快,這是值得珍視的友誼!
二、在這長期動亂不安中,我開始成部的寫作,與講說而由別人記錄成書。 一方面,有幾位同學──演培、續明、妙欽他們,希望我作些課外的講說;一方面,是我對全體佛法的看法,逐漸凝定,也有了表示意見的意欲。如三十年所寫 的『佛在人間』,『佛教是無神論的宗教』,『法海探珍』,都是闡揚佛法的人 間性,反對天(神)化;探求佛法本質,而捨棄過了時的方便。「佛法與現實佛 教界有距離」,是一向存在於內心的問題。出家來八年的修學,知道為中國文化 所歪曲的固然不少,而佛法的漸失本真,在印度由來已久,而且越來越嚴重。所 以不能不將心力,放在印度佛教的探究上。這一時期的寫作與講說,也就重在分 別解說,確定印度經論本義,並探求其思想的演化。當時,我分大乘法義為三論 ──性空唯名論,虛妄唯識論,真常唯心論。這一分類,大致與虛大師的大乘三 宗──法性空慧宗,法相唯識宗,法界圓覺宗相同。在『法海探珍』中,曾以三 法印──諸法無我,諸行無常,涅槃寂靜,作為三系思想的不同所依。著重於三 系的分解,所以寫的與講的,著重於此。如屬於性空唯名論的,有『金剛般若波 羅蜜經講記』,『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中觀論頌講記』,『中觀今論』,『性空學探源』。屬於虛妄唯識論的,有『攝大乘論講記』,『唯識學探源』,『解深密經』。屬於真常唯心論的,有『勝鬘經講記』,『大乘起信論講記』,『阿跋多羅楞伽寶經』。我在師友間,是被看作三論宗的,而第一部寫作,是 『唯識學探源』;第一部講錄成書的,是『攝大乘論講記』,這可以證明一般的 誤解了!在所講的經中,『解深密經』僅講『勝義了義』章,在演培的『解深密 經語體釋』裏,可能含有我的部分意見。『楞伽經』,沒有講圓滿。後來在臺灣 又講了二次,應該有記錄,但沒有成書。現在僅保留我對『楞伽』全經的科判 ──五門,二十章,五十一節的名目。我的講解,從不會拈出一字一句,發揮自 己的高見,也沒有融會貫通。雖然所說的未必正確,但只希望闡明經論的本義。 為了理解三系經論的差別,所以講解時,站在超宗派的立場,而不是照著自己的 見解去解釋一番。以現在的理解來說,『性空學探源』一書,雖搜集了不少資料 ,而說到「探源」,似乎差一點!
三、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去理解佛法的根源與流變,就不能不注意到 佛教的史地。大乘三系,也還是開展、流行、演化於某時某地的。妙欽編了一部『中國佛教史略』,我加以補充修正,使中國佛教史與印度佛教史相關聯,作為 二人的合編。從佛教典籍中,論證釋迦族是屬於印度東方的,所以是東方的沙門 文化,有反對印度阿利安人傳統的真常梵我論的特性,這就是『佛教之興起與東 方印度』一文的主要意義。『太虛大師年譜』,是近代佛教大師,有關近代中國 佛教的種種史實。最重要的一部,當然是三十一年所寫的『印度之佛教』。印度 佛教史的流變,我分判為五期:一、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二、菩薩傾向之聲聞 分流;三、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四、如來傾向之菩薩分流;五、如來為本之梵 佛一體。印度佛教的先後五期,從創立到衰滅,正如人的一生,自童年、少年、 壯年、老年到死亡。我以為,佛法不能沒有方便,不能不求時地的適應,但「對 於方便,或為正常之適應,或為畸形之發展,或為毒素之羼入,必嚴為料簡,正 不能率以方便二字混濫之」。覺得「中國佛教,為圓融、方便、真常、唯心、他 力、頓證之所困,已奄奄無生氣;神秘、欲樂之說,自西(康、藏)而東,又日 有泛濫之勢」(『自序』)。『印度之佛教』是史的敘述,但不只是敘述,而有評判取捨的立場。所以這部書的出版,有人同情,也有人痛恨不已。不過痛恨者 ,只是在口頭傳說中咒咀,而真能給以批評的,是虛大師與王恩洋居士(還有教 外人一篇)。我稱印度佛教末期為「佛梵一體」,與虛大師所判攝的「依天乘行 果」,大致相同。虛大師的批評重心在:我以人間的佛陀──釋迦為本;以性空 唯名、虛妄唯識、真常唯心──三系,為大乘佛法的開展與分化。而虛大師是大 乘別有法源(在『阿含經』以外)的,是中國佛教傳統,以『楞嚴』、『起信』 等為準量,也就是以真常唯心──法界圓覺為根本的。虛大師所以主張,『大乘 起信論』造於龍樹『中論』等以前,以維持真常唯心為大乘根本的立場。不過, 說『起信論』的造作,比龍樹作『中論』等更早,怕不能得到研究佛教史者的同 意!其實,我對印度的佛教,也不是揚龍樹而貶抑他宗的。我是說:「佛後之佛 教,乃次第發展而成者。其方便之適應,理論之闡述,如不適於今者,或偏激者 ,或適應低級趣味者,則雖初期者猶當置之,況龍樹論乎?乃至後之密宗乎!其 正常深確者,適於今者,則密宗而有此,猶當取而不捨,而況真常系之經論乎!其取捨之標準,不以傳於中國者為是,不以盛行中國者為是,著眼於釋尊之特見 、景行,此其所以異(於大師)乎」(『敬答議印度佛教史』)!存有揚清抑濁 ,淘沙取金的意趣,沒有說千百年來所傳,一切都是妙方便,這就難怪有人要不 滿了。王恩洋是著名的唯識學者,他不滿真常唯心論,稱之為「入篡正統」,那 是不承認他是佛法的。對於末期的秘密乘,當然沒有好感。他所以要批評『印度 之佛教』,只是為了辨論空宗與有宗,誰是了義的,更好的。我寫了『空有之間 』,以表示我的意見。以上幾種,都是自己寫作的。
四、我在『印度之佛教』的「自序」中說:「立本於根本(即初期)佛教之 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 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那時,我多讀「阿含」、「戒律」、「阿毘達磨 」,不滿晚期之神秘欲樂,但立場是堅持大乘的(一直到現在,還是如此)。錫 蘭等南方佛教,以為他們所傳的三藏,是王舍城結集的原本;以為大乘佛教,是 印度教化的,非佛說的。這種意見,多少傳入當時的抗戰後方,而引起某些人的疑惑。我為續明他們,討論這個問題,後來題為『大乘是佛說論』(依現在看來 ,說得不太完善)。慧松法師留學錫蘭返國,法舫法師在錫蘭邊學邊教,都有以 傳入錫蘭的為純正佛法,而輕視印度所有,傳入中國佛教的傾向。所以為慧松寫 『!2扆!2菨文集序』,表示我的意見;因法舫法師而寫『與巴利語系學者論大乘』。 我到臺灣來,有人說我反對大乘,那不是惡意,就是誤會了!
五、大乘佛法,我以性空為主,兼攝唯識與真常。在精神上、行為上,倡導 青年佛教與人間佛教。在歷史上,大乘佛教的開展,確與青年大眾有關。所以依 『華嚴經』的「入法界品」,善財童子的求法故事,寫了一部『青年佛教與佛教 青年』。(現在編入『妙雲集』,已分為三部分:『青年佛教運動小史』,『青 年佛教參訪記』,『雜華雜記』)。不過我所說的青年佛教,是:「菩薩不是不 識不知的幼稚園(生)。……青年佛教所表現的佛教青年,是在真誠、柔和、生 命力充溢的情意中,融合了老年的人生的寶貴經驗」(『雜華雜記』)。因為, 如對佛法缺乏正確而深刻的勝解,那末青年佛教的勇往直前,隨宜方便,不可避免的會落入俗化與神化的深坑。虛大師說「人生佛教」,是針對重鬼重死的中國 佛教。我以印度佛教的天(神)化,情勢異常嚴重,也嚴重影響到中國佛教,所 以我不說「人生」而說「人間」。希望中國佛教,能脫落神化,回到現實的人間 。我講「人間佛教」,現存『人間佛教緒言』,『從依機設教來說明人間佛教』 ,『人性』,『人間佛教要略』。在預想中,這只是全部的「序論」,但由於離 開了香港,外緣紛繁,沒有能繼續講出。
六、三十三年下學期,在漢藏教理院講『阿含講要』。第一章「阿含經之判 攝」,提出了四『阿含經』的不同宗趣,這就是龍樹「四悉檀」的依據。這表示 了四部「阿含」的編集方針:『雜阿含經』是「第一義悉檀」,其他的或重在「 對治」,或重在啟發的「為人生善」,或是適應印度宗教以誘化「世間」。當時 所講的,主要是境相部分。三十八年在廈門,刪去第一章,自己補寫了幾章,說 明聲聞與菩薩的行果,改名為『佛法概論』。這部書,依『阿含經』;依龍樹所 決了的「阿含」深義,明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又補入龍樹所說的菩薩道──二道,五菩提。另一部『淨土新論』,是依虛大師所說:「淨為三乘共庇」,說明 佛法中的不同淨土。在「往生淨土」以外,還有「人間淨土」與「創造淨土」。 這對只要一句彌陀聖號的行者,似乎也引起了反感!
七、我的寫作,一向重於自己對佛法的理解,不大歡喜批評別人,但在這一 階段的後期,寫了三篇不太短的批評文字。一、『佛滅紀年抉擇談』:有人依『 眾聖點記』等,主張佛滅年代,以錫蘭所傳的,阿育王登位於佛滅二百十八年說 為可信。我以為:阿育王的年代,是可以考信的。從佛滅到阿育王,錫蘭所傳, 中國所傳──阿育王登位於佛滅百十六年,都只是佛弟子間的傳說如此。說到『 眾聖點記』,佛滅以來,起初並沒有書寫的戒本,試問每年結夏終了,又在那裏 去下這一點?我不滿一般偏重外來的傳說,所以加以評論,而取中國固有的傳說 。這可說是對誇大南傳的巴利語系,輕視中國所傳而引起的反感。來臺灣後,知 道還有古老的上座部所傳,阿育王登位於佛滅百六十年說,這也許更恰當些。二 、『僧裝改革評議』:當時,有人遊化錫蘭、緬甸,所以主張出家人的服色,應該一色黃,而評中國僧服為「奇形怪狀」。有些僧青年,主張廢棄固有「腐敗落 伍」的,改為與俗服沒有明顯差別的服裝。這可能造成「進(山)門做和尚,出 門充俗人的流弊」,所以寫了這篇評議。我以為,中國固有僧服的顏色,是合於 律制的,黃色只是一宗一派的服色。僧服是可以改革的,但必須合乎律制的原則 ──對外差別而表顯僧相,對內統一以表示平等。其實,僧裝改革只是形式的改 變,並不能促成僧界的清淨,佛教的復興!三、『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熊先 生的『新唯識論』,在哲學與儒學的立場,自有其地位;道不同,用不著評論。 但他在書中,一再的批評唯識與空宗。其實他所知道的空,是唯識學者──有宗 所說的空,根本不知道空宗是什麼。特別是:他的思想,如他自己所說:「大易 其至矣乎,是新論所取正也」。這明明是儒學;佛法的唯識與(唯識家所說的) 空,只是評破的對象。他卻偏要說:「本書於佛家,元屬創作」;「新論從佛學 演變而來,說我是新的佛家亦無不可耳」!這種淆混視聽的故弄玄虛,引起我評 論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