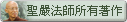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禪宗典籍《五燈會元》研究
作者:黃俊銓
出版社:法鼓文化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
規格:14.8x21 cm / 平裝 / 494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200501
ISBN:9789575984403
定價:NT$420
會員價:NT$357 (85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第一章 《五燈會元》研究綜述與思路
↑TOP
第一節 《五燈會元》研究綜述
《五燈會元》的重要性,在前文中已經提到過,然而十分遺憾的是國內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研究此語錄的專書面世。這是與其在禪宗史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完全不相稱的,以下首先略具篇幅對《五燈會元》的研究史稍加敘述。
《五燈會元》在撰成以後並不十分廣泛地流傳,但是對於整個佛教界內外,還是產生了或多或少的一些影響,這可以從《五燈會元》大量的續書,以及從當時對此書的直接和間接引用來看,比如在《五燈會元》編成後之《釋氏通鑑》(編年體佛教通史)中就曾對之有間接引用 。至於元代,佛教史的編寫則也有屢次採錄《五燈會元》的情況 ,並且有些典籍則已經對其史實做了一些訂正,比如本覺等所編《釋氏稽古略》卷三之〈邵武龍湖禪師〉條對其卒地就考證曰:
(邵武龍湖)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開元寺,龍湖僧追之。師曰:「山中已有聰禪師,吾不復歸矣。」故龍湖無開山祖師塔,惟有跨虎庵基,為古今之證。諡圓覺禪師。《五燈會元》謂師示寂於龍湖,殆非也 。
查《五燈會元》卷六之〈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條記其卒時云:
師闡化三十餘年,臨示寂,聲鐘集眾。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個歇處。住山聚眾三十年,尋常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安然而逝,塔於本山,諡圓覺禪師 。
因此,二者之間已經存在史料方面之出入了,然二者間仍以前者更為可信,因為前者史料之來源是十分清楚的,在此書卷一中有〈歷代編年釋氏通鑑採摭經傳錄〉,查其中就有:「龍湖行狀」,因而可知本覺編輯其書之時,曾經參考關於龍湖生平的第一手材料,故而其史料價值更加可靠。
另外據宋釋道璨所撰《柳塘外集》卷三〈宗門會要序〉:
宗門書自《傳燈》後傳記日出,學者既不能盡見,亦不暇周覽。閩人朋介石為書曰《宗門會要》,根以《統要》,參以《五燈》。遠而古宿之代別,近而諸方之拈頌,旁而佛鑒大圓之法語,八方珠玉,一展卷而燦焉在目,其惠後學不淺矣 。
由此看來,《宗門會要》一書之編撰,也曾經參考了《五燈會元》中的資料,然而此書今已佚失,具體情況已然不可考矣。雖然有了這樣的一些零星的記載,但就大規模的專門研究而言,則可能還要在很久以後方才出現。
關於此書在當時的研究和流傳情況,我們還可以查勘一下當時的目錄學記載。與普濟約略同時期的南宋藏書家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並沒有記載《五燈會元》,到宋末元初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七《經籍考》中,則有《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嘉泰普燈錄》,卻無《五燈會元》 。大約同時期的另一位著名目錄學家晁公武,在他的《郡齋讀書誌》卷三下〈釋書〉中,於禪宗類收錄了《宗鏡錄》、《景德傳燈錄》、《傳燈玉英集》、《天聖廣燈錄》、《分燈錄》 、《禪苑瑤林》 等,但也沒有《五燈會元》的蹤影。
約略一百年後之鄭漁仲《通志》卷六十七,〈釋家目錄〉部分,於禪宗語錄則記錄有《真門聖胄集》、《景德傳燈錄》、《傳燈玉英集》等三種,亦未見《五燈會元》之記載。元脫脫等所編《宋史藝文志》中,基本抄集了《文獻通考》之部分,故依然無之。而就內典而言,元代目前僅存的兩部藏經目錄《普寧藏目錄》和《至元法寶勘同錄》中,亦無《五燈會元》之記載,這基本可以反映其時《五燈會元》的普及情況。故而雖然一方面我們從方回的詩句裡,可以看到:「愛僧予尤愛詩僧,千偈萬頌傳《五燈》。寒山拾得兩奇絕,妙壓神秀盧慧能 。」但並不能就此得出,當時《五燈會元》已然是普及到了千家萬戶,家喻戶曉的程度了,可能只是詩家誇張的說法而已。
對於此書的研究,第一個較可注意的時期是明代。因為當時佛教的特點是早期十分興盛,而到了中期的宣宗至穆宗(公元1426-1572年)一百多年中,則呈現整體且持續的衰落狀況。這種情況到了神宗萬曆(公元1573-1619年)時期以後,有了很大的改變,佛教尤其是禪宗經歷了一次全面的復興。而在這個復興的過程中,最明顯的莫過於明代四大師的出現,也就是雲棲蓮池袾宏大師(公元1535-1615年)、紫柏真可大師(公元1543-1603年)、憨山德清大師(公元1546-1623年)、蕅益智旭大師(公元1599-1655年) 。
這種全面的佛教復興,也就必然帶來了對於某些佛教典籍的關注,在這種背景之下,對於禪宗典籍乃至對於《五燈會元》的關注和研究,也就因此而多了起來。而自從宋代以後,以在家信眾於日常世俗生活,從事佛教信仰活動為特色的居士佛教,也漸漸成為了中國佛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這樣居士也就同時參與到了《五燈會元》的傳播者和評論者的隊伍中來了。
我們先來看看,對於明代初年僧人《續傳燈錄》的編者居頂對《五燈會元》的批判:
某謹按,吳僧道原於宋景德間修《傳燈錄》三十卷,真宗特命翰林學士楊億等裁正而序之,目曰:《景德傳燈錄》。自是禪宗寢盛,相傳得法者益繁衍。仁宗天聖中,則有駙馬都尉李遵勗著《廣燈錄》,建中靖國初則有佛國白禪師為《建中靖國續燈錄》,淳熙十年淨慈明禪師纂《聯燈會要》,嘉泰中雷庵受禪師述《普燈錄》。宋季靈隱大川濟公,以前五燈為書頗繁,乃會粹成《五燈會元》。竊謂《景德傳燈錄》至矣,繼此四燈之錄,寧免得此而遺彼乎。《會元》為書,其用心固善,然不能尊《景德傳燈》為不刊之典,復取而編入之,是為重複矣。今臣幸遇聖明,光讚佛乘,遂忘其僭,纂集《續傳燈錄》……名之曰《續傳燈錄》 。
居頂亦即靈谷圓極居頂,其年代大體為明代初年之臨濟宗禪師,此人也屬於學問僧之列,故曾受敕任僧錄司左講經之職,並曾協助明版大藏經之雕印 。在上述評論中,我們看到了他對於《景德傳燈錄》的推崇和對於《五燈會元》的貶斥。其理由是:「不能尊《景德傳燈》為不刊之典。」這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批評,其實《五燈會元》本身就是以五部燈錄為基礎的,而從文本方面的分析來看,《五燈會元》對於《景德傳燈錄》的史料是異常重視的,並不存在一個不尊重的問題。故而認為「復取而編入之」就是一種重複,這是沒有看到《五燈會元》實際上是在《景德傳燈錄》基礎上,又做了很多的增加、刪節、改寫等工作,總體而言,其批評是沒有多少理論支撐的。
還有一點,就是《續傳燈錄》的重要改變和前兩部燈錄,都是以不同法脈來對紛繁複雜的眾多禪師做不同歸類。圓極居頂認為,南宗都出於慧能門下,故不應再分派別,於是不再以南嶽、青原等二系和五家七宗來編排人物,只以大鑒下多少代為軸心。這在數千人的整個系統裡,就顯得過於粗略了,也反映出他對於《五燈會元》的批評,並沒有多少可取之處。稍後成書於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的《增集續傳燈錄》的作者文琇對《五燈會元》的評價是:
余於少壯時,嘗閱秀紫芝《人天寶鑑》其序有云:「先德有善,不能昭昭於世者,後學之過也。」及觀《五燈會元》若妙峰、北澗、松源、破庵諸老宿,皆未登此書。乃有撰述之志。於是凡見禪宗典籍及塔銘行狀,自宋季及元以來,諸碩德言行超卓者遂筆之,迨今越三十餘年矣。但不能遍歷江湖訪而求之,於心未慊,故於永樂乙未,移書諸大方尊宿,幸籍靈谷幻居和尚、天童即庵和尚展轉搜討。繼而又得郡人吳道玄亦為博尋遺籍,僅有所成,遂用詮次。竊觀《續傳燈錄》於《五燈會元》後,若大鑒第十八世至二十世,曾收三世奈收之未盡。已收者亦言行太略,今於所收外,又增入之。故云《增集續傳燈錄》 。
這裡對於《五燈會元》倒並沒有什麼微詞,其所編輯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對其做些材料上的增補。比如,對於《五燈會元》未編入的一些禪師,在此書中就被編入了卷六的部分之中。有明一代,除僧人漸習《五燈會元》以外,俗人居士也對此書較為稔熟。此可以視,歸有光曾就友人未取此書而例之也 。
另外,我們還可以發現,由於明代文人日益浸淫於內典,故我們還可以在很多考證性的文字中,發現對《五燈會元》的引用 ,這都反映了明代《五燈會元》的流傳已經十分廣泛了。
關於明代《五燈會元》的流行和傳播,我們還是可以從目錄學著作中的記載,找到相關的佐證,比如,明初楊士奇所編的《文淵閣書目》卷十,《釋書錄》記錄五十七部,計三百三十六卷,其中就包括《五燈會元》。另焦理堂《國史經籍志》卷四上、錢溥《祕閣書目‧佛書門》中都錄有此書,這都說明了比起前代而言,其流通要廣泛得多了。故而我們就可以看到一般士大夫中,參習語錄遂成為常事,而其中也就包括了《五燈會元》。如明楊巍所撰《存家詩稿》卷六有《嘲儒》:「尼父不言靜,後儒何怪哉。紛紛諸語錄,皆自《五燈》來 。」
然就總體而言,和後代相比《五燈會元》之流布仍未很廣,直到清代《乾隆大藏經》時,方才得以入藏,這對於其流布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清代不但在大藏經中,將《五燈會元》收錄了進去,另外一部對中國文化影響很大的叢書《四庫全書》中,也收錄了《五燈會元》。這對於其流通的推動也是十分重大的。在《四庫全書》的諸提要部分中,與《五燈會元》相關研究的共有兩篇,第一篇是慧洪《林間錄》的提要:
《林間錄》二卷、《後集》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釋惠洪撰。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所記皆高僧嘉言善行,然多訂讚寧《高僧傳》諸書之訛。又往往自立議論,發明禪理,不盡敘錄舊事也。前有大觀元年謝逸序,稱惠洪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每得一事隨即錄之。本明上人以其所錄析為上下二帙,刻之於板。是其書乃惠洪札記而本明為之編次者。……(慧洪)所作《石門文字禪》釋家收入大藏。又普濟《五燈會元》亦多採此書,蓋惠洪雖僧律多,而聰明特絕,故於禪宗微義能得悟門。又素擅詞華,工於潤色,所述釋門典故皆斐然可觀。亦殊勝粗鄙之語,錄在佛氏書中,固猶為有益文章者矣 。
此提要之要點,在於認為《五燈會元》之編撰曾參考《林間錄》,此說實發前人所未發,由於這涉及到《五燈會元》的史源學部分,筆者會在後面的章節中,著重談到此事,然而有一點可以指出的就是此提要作者,若非對於內典稔熟於胸,則萬萬不能辦到。其二就是《四庫》中所撰《五燈會元》提要:
《五燈會元》二十卷,內府藏本,宋釋普濟撰。普濟字大川,靈隱寺僧也。其書取釋道原《景德傳燈錄》、駙馬都尉李遵勗《天聖廣燈錄》、釋維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聯燈會要》、釋正受《嘉泰普燈錄》,撮其要旨,匯為一書,故曰《五燈會元》。
以七佛為首,次四祖、五祖、六祖,南嶽青原以下各按傳法世數載入焉。蓋禪宗自慧能而後分派滋多,有良价號洞下宗;文偃號雲門宗;文益號法眼宗;靈祐、慧寂號仰宗;義元號臨濟宗,學徒傳授幾遍海內。宗門撰述亦曰以紛繁,名為以不立語言文字為不二法門,實則轇轕紛紜,愈生障礙。
蓋唐以前各尊師說,儒與釋爭。宋以後機巧日增,儒自與儒爭,釋亦自與釋爭。人我分而勝負起,議論所以多也。是書刪掇精英,去其冗雜,敘錄較為簡要。其考論宗系,分篇臚列,於釋氏之源流本末亦指掌了然,固可與《僧寶》諸傳同資,釋門之典故非諸方語錄掉弄口舌者比也 。
《四庫提要》此條解題大體仍算是十分精當,其作者據陳垣先生推測,可能是曆城周永年 。無論撰述者為何人,加上前《林間錄》之解題,所反映的佛教學術素養,都已經是十分高超的了。這種大型叢書對《五燈會元》的收錄,就某種意義而言,可以說是確立了其文獻和宗教價值的一個標誌,自此以後無論僧俗,對於此書的利用就日漸增多。清末另有一件對於《五燈會元》之研究,起到極大推動作用的事件,就是「寶祐本」的回歸和翻刻。
寶祐本之價值,不僅在於它是到目前為止《五燈會元》最早的一個版本,為文本的校訂提供了早期的文字依據。而且還由於在此本中,保留了早期的序文,更解決了像《五燈會元》的編撰者究竟為何人等,數百年來認識上的誤區,這都對以後此方面的研究,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故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佛教史的一些研究者中,有些就對此本的諸多問題都展開過討論。
尤其應該提到的是中國禪宗研究的先驅者胡適之先生,在他的文集裡就有著一系列關於此本的文章。比如〈與周法高論所謂景宋寶祐本《五燈會元》的底本的信〉、〈與黃彰健論劉世珩翻刻《五燈會元》的年代的信〉、〈記中央圖書館藏的宋寶祐本《五燈會元》附:後記四則〉、〈論劉世珩翻刻《五燈會元》的「貞治馬兒年」〉、〈記宋寶祐刻本《五燈會元》的刻工〉、〈記「恭仁山莊善本書影」裡的《五燈會元》書影〉、〈記宋槧本容安書院藏與求古樓藏貞治戊申刊本《五燈會元》〉、〈寶祐本的抄補與配補〉、〈楊守敬「留真譜」初編裡的《五燈會元》書影〉 。這些文章之寫出,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至今依然是學界的最高水平。
現略介紹一下此數篇文章之內容:
一、〈與周法高論所謂景宋寶祐本《五燈會元》的底本的信〉乃適之先生給周氏的信,主要是討論貴池劉氏影印宋寶祐的真偽,由於劉氏此本,將日本貞治年翻刻本的三件題記也照樣附於書首,故導致了胡氏的判斷失誤,這點他在後續的研究中,很快就意識到了。但胡氏此信中也敏銳地意識到,此本書首沈氏序對釐清《五燈會元》編者所具有的價值。
二、〈與黃彰健論劉世珩翻刻《五燈會元》的年代的信〉,此信討論的是和史語所,所購至元本殘頁與劉氏本的字數異同,以及《五燈會元》的傳本系統,除前述對劉氏的年代有誤外,基本是十分精當的。
三、〈記中央圖書館藏的宋寶祐本《五燈會元》附:後記四則〉,此篇討論的是中央圖書館的藏《五燈會元》的版本問題,指出此本中,八、九諸卷為寶祐本原刻,至此篇胡氏已經知悉了劉氏復刻本所附三件貞治題記,並非是寶祐本原配。後面繼前幾篇,繼續討論了此本在日本的流傳情況,以及刻工中的王錫乃淳祐二年所刻《心經》之刻工,關於寶祐本刻工的問題,筆者會在版本問題上做更深入的探討。此篇最重要的部分,是關於元刻本曾有改版的發現,胡氏將寶祐本與元刻本做了對勘,發現在後者中多有妄改的情況。此點非常遺憾,我們現通用的蘇淵雷校勘本中,對此問題卻沒有注意到。僅以〈達摩傳〉為例,胡氏就指出有四處改動,到了蘇本中僅出了一處校記 。
四、附後記四篇:
(一)後記一,特意指出對劉氏本,開始不信其為宋本,但經昌彼得等借原本後,又與周、黃、屈討論,才得以糾正在認證期間之誤判。敬佩胡適之先生,不掠人之美、不掩己之過。
(二)後記二,擬出了一個《五燈會元》的版本系統圖。
(三)後記三,乃討論《續藏經》本《五燈會元》的底本問題,指出此本乃是日本翻印明末福州刻本。又有:「後記的後記」一篇討論的是《嘉興藏》本之《五燈會元》刻本。
(四)後記四,討論日本室町時期兩種翻刻本。〈論劉世珩翻刻《五燈會元》的「貞治馬兒年」〉一文,乃是討論「寶祐本」如何傳到日本的問題,並認為貞治馬兒年實乃日本之年號。下一篇〈記宋寶祐刻本《五燈會元》的刻工〉,此本列出了「寶祐本」的刻工,但只考證了其中的王錫一人。
短文〈記「恭仁山莊善本書影」裡的《五燈會元》書影〉,記錄了所見的內藤湖南博士遺書中,室町時期翻刻本的簡要情況。〈記宋槧本容安書院藏與求古樓藏貞治戊申刊本《五燈會元》〉乃容安書院所藏宋本《五燈會元》殘頁的一個行款簡錄。《寶祐本的抄補與配補》乃記錄了今所傳「寶祐本」,乃經過某一不知名的日僧抄補配補的介紹。《楊守敬留真譜初編裡的五燈會元書影》乃介紹楊氏《留真譜》中,所錄「寶祐本」行款的一些特點。
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知道,此一系列文章對於「寶祐本」的底本、年代、刻工和當時刻印的一些細節,以及劉氏翻刻的年代等問題,都做了非常獨到的考證,這其中很多即使是在今日,也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流的成果,顯示了作者精湛的文獻功力。
此後由民國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之間,《五燈會元》之研究大體則甚為寥落,其實此一時期,佛教研究之一個大宗就是禪宗方面的研究 。故而在諸多的禪學以及禪宗史方面的重要著述之中,就難免總會涉及到《五燈會元》,這包括像印順《中國禪宗史》 、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 、顧偉康《禪宗六變》、《禪淨合一流略》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9世紀》 、洪修平《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
但就專章研究則只有陳垣先生《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四之《五燈會元》部分,此部分所論述之問題包括第一,「《會元》之體制及內容」此部分為《五燈會元》之內容和普濟所出之派系。次為,「《會元》版本及撰人問題」此節討論「寶祐本」對於《五燈會元》編者推定之意義,以及慧明是否為慶元五年,常照寺僧的問題等等。
時至八○年代以後,陳士強的著作《佛典精解》中,對《五燈會元》也有極為精彩的解題。在此部解題中,先論及《五燈會元》各藏經之收藏,次及編者問題,然後各章節的一個詳細解題,最後再以具體例證,討論《五燈會元》與另外五部燈錄之間的聯繫與區別,總之此篇是到目前為止對《五燈會元》最為詳盡的研究。
除此之外,大體上都是一些語言學方面的研究,這主要是因為禪宗語言極具特色,其淳樸、鄙野的原始特徵,對研究唐宋時代的口語極有價值,故而在漢語史研究上,非常流行對於某種燈錄的語言做專題研究,此方面的文章相對而言是比較多的。
此姑舉數例說明如下:
一、沈丹蕾所撰〈《五燈會元》的句尾語氣詞「也」〉 中,以《五燈會元》為例說明句尾語氣詞「也」的用法變化。因為在古代漢語中,主要表示靜態的肯定和判斷,而近代漢語中「也」的使用範圍擴大,增加了表示事態變動的新功能。而《五燈會元》的句尾語氣詞「也」不僅保留著它在古漢語中的用法,而且具備了與語氣詞「了」相同的表示事態變化的功能。此種研究傾向,在中國大陸也呈現同樣的局面。
二、具熙卿所撰〈《五燈會元》、《碧巖集》、《景德傳燈錄》中所見的被字句分析〉 。此文以《五燈會元》等書中的語言材料為佐證,分析宋代佛教的被動句式,在此三本禪宗著作中,被動句式主要有:「為字句」和「被字句」兩種,而以後者更為常見。並以文獻材料為基礎,分析了「被字句」的複雜結構和形式。除了這樣一種以《五燈會元》一書或幾種禪宗典籍中的材料,表態分析其語言學問題之外,另有從多部語錄之變化動態分析的方法。
三、張美蘭所撰〈論宋代禪宗的語言特色:從《祖堂集》與《五燈會元》語言的風格差異入手〉 為例,此文結合禪宗發展史和漢語語言發展史,在對《祖堂集》和《五燈會元》的文獻語言風格對比之後,側重闡述了宋代禪宗語言的語言學特點,探尋其差異出現的原因,並進一步探討其在漢語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此一語言學方面的研究文章非常多,由於與本文所研究的角度相差較大,故不再一一羅列。
除了這些佛教語言學方面的研究之外,對於《五燈會元》文獻學方面的研究則有項楚先生,項楚做為文獻學研究界的重要學者,其治學範圍較廣,餘力所及也兼治禪宗語言,對於《五燈會元》所做的研究主要是版本的校勘。其發表的作品是〈《五燈會元》點校獻疑三百例〉 、〈《五燈會元》點校獻疑續補一百例〉 。
另馮國棟博士對此方面也有研究,馮氏目前研究有兩個重點,一是燈錄史,一是佛教目錄學。關於《五燈會元》的研究則是其第一方面的成就,具體有〈《五燈會元》校點疏失類舉〉 ,此文主要是針對1984年蘇淵雷校本而發,其校正蘇本之誤近百例之多,其中包括「影宋本不誤點校本轉錄致誤例」、「未能以續藏本、龍藏本正影宋本之失例」、「不明名義點斷致誤例」、「專名號使用失誤例」等數種失誤,為一次對蘇本較為全面的清理。另一篇為〈《五燈會元》版本與流傳〉 ,此篇考察了《五燈會元》歷代的刊刻情況,對《五燈會元》的各種版本做了較為全面的描述,並在此基礎上研究了此書在歷代的流布,就總體而言,此篇文章是到目前為止對《五燈會元》版本研究較為重要的成果。
從以上《五燈會元》研究情況的總體分析來看,大體上由於其流傳方面的原因,學者對其研究之發現實為明代,到了清末民初由於新版本的發現,又進一步推動了其後的發展,為《五燈會元》研究中,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提供了可行性的解決線索。而真正具有現在學術規範研究的開拓者是陳援庵先生。此方面到了八○年代以後,則又有陳士強教授的研究。在此之外,除了漢語史方面的研究,對此方面做出貢獻則有項楚和馮國棟等的文獻學研究。這樣一種冷清的局面,是和《五燈會元》其自身價值遠遠不能相稱的,故而筆者希望能通過此文的寫作來對此稍加改變。
第二節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本文主要採取文獻學和歷史研究的方法。首先,本文採取文獻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尤其是側重於版本的校勘與研究。在校勘方面,一方面通過傳統的本校與對校法,利用不同版本之間的校對來盡量考訂《五燈會元》一千多年來,傳抄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錯誤,乃至其他有意或無意的失誤。這實際上是出於一個非常實際的需要,就是筆者希望能以更新的校勘理念、多樣的校勘手法、搜集更多的版本,以及精力的更大投入,以求能整理出一個,比目前學界所最常使用的版本,更加方便並且準確的校訂本。而本文在校勘與版本,乃至於史源學上的研究成果與實際經驗,主要是為了今後《五燈會元》的進一步整理做些材料方面的準備。
另外,本文研究方面的另一個特點,是在校勘四法之中主要利用他校法。此點乃與本文的另一個研究目的有關,即為了廓清《五燈會元》其編輯過程中,具體使用了哪些史源及其材料採擷上的標準。這種史源學上的推考,主要是為了恢復在禪宗史的宏觀背景之下,《五燈會元》編纂之時的禪宗史料存世情況。並由此考察當時禪宗不同派系之間,利用編輯史料之辦法來相互傳播,自己所在特定派系的不同宗教思想。此點在本文中,則主要牽涉到了臨濟宗的一些宗派。
比如著名的「大慧派」,此派乃由大慧宗杲所創立。非常值得研究,而且也饒有趣味的是,大慧本人以「看話禪」為特色而鳴於世。並欲焚其師之書,這本來是在中唐以降,禪宗的禪法漸漸廢弛,而禪僧則多沉迷於法語、公案,以至於多以語句之發明為參悟之道,甚至流連於祖師法語的註釋而忘返。其主張「看話禪」正是對此種繁瑣的經學主義的離棄,但是我們卻應該看到,在另一方面,熱衷於禪宗史籍編撰的又恰恰是「大慧派」傳人 。在這樣一個歷史發展的正反合裡,其中確實透露了很多的宗教和社會信息,而筆者也希望能通過,對於本文的寫作來窺其一斑。
本文的第二個研究方法,是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首先盡量將《五燈會元》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加以關照。盡最大的可能性,恢復其文本編纂時的原生狀態,期以同情默應的態度,來理解當時編著者們的心境。以此來研究當時禪宗發展,乃至臨濟宗發展的一般以及特殊情境。就實際而言,我們從禪宗歷代記錄中,所看到的史和當時真實的史之間,是存在一個很大的差距。
一方面,客觀上認為人類的任何一種記錄工具,都不可能將我們,哪怕同時代的活生生的歷史,完完整整地記錄下來;另一方面,由於記錄者本身也都是一些有思想傾向的、具有獨特視角的人,那麼在他們的記錄中,我們所看到的史,其實就很大程度而言,只不過是他們想讓我們知道的歷史,而不是那個沒有愛憎偏見的完整的史。這種情況在禪宗史中顯得尤為突出,有時候我們會發現很多的宗教家,都有「編造」歷史的習慣。以前當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我們對此總是嗤之以鼻,其實我們更應該看到即使是偽史,其背後也有真實的宗教關懷在,而後者也正是我們研究所應該關注的。
在具體的思路和研究計畫上,和一般文獻學的基本研究方法非常一致,首先筆者初期的工作重心,主要是放在各種史料的比對校勘之上,這佔據全部研究計畫一半以上的時間。筆者在此文中的絕大多數觀點,都是在這個漫長而充滿艱辛的校勘過程中逐個得來,筆者在文中所要表達的思想,也在此一過程之中慢慢成形。這也是筆者在文獻學學習的過程中,所得來的一點小小的心得,即在研究之前並沒有一個一定要表達的思想,而是讓材料自身去展現其本來就有的觀點,這就不會導致刻意去搜集材料,而產生先入為主地論證某種觀念的弊病。
在校勘學的具體方法上,前面筆者已經提到,限於本文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集中於史源學的範圍,所以採用最多的是他校法。這種方法對於文獻整理而言,最大的好處在於可以以某種經典為中心而觸類旁通,兼及某一橫向歷史切面之上的諸多宗教史料,並由此克服個案研究所最容易產生的「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弊病。
在對《五燈會元》的史源學考察之中,由於其史料最早來源於北宋初年,景德年間之《景德傳燈錄》,而《五燈會元》本身則成書於南宋即將覆滅的末期。這樣在史料的時間跨度之上,就橫亙了幾乎天水一朝的全部,也可以從中相當完整地涵括了宋代禪宗發展的全部過程。實際並不止此,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五燈會元》的史料採集,甚至有兼及北宋立朝之前的早期大德語錄的情況,這就使論文的發展具有了縱向的延展度。
在各種史料的比對校勘完成以後,剩下的工作就是對各種寫作素材,做重新的分類與剪裁,然後在此基礎之上寫作論文。文獻學研究並非是萬靈藥,其工具性的特點實乃其最大的局限。我們一方面不能估計此種文獻研究,在整個學術體系之中的基礎作用,另一方面則絕不能把文獻之研究當作學術的終結。由於筆者自身僅局限於文獻學的這一缺陷,就顯得更加放大,所以對此,筆者一直將之銘感於心。
從《五燈會元》的情況來看,我們必須知道,就實際定位,它並不是被當作一種純客觀的「史」來編纂的,而只是附著於特定宗教情感關懷之下,具有特定宗派意義,並傳達其宗教理念的傳承世系。在《五燈會元》的編者心中「歷史本身是如何?」其重要性是讓位於「歷史應該是如何?」對此點筆者一直都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否則就會偏離整個研究的基礎方向,這也是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研究思路。
《五燈會元》的重要性,在前文中已經提到過,然而十分遺憾的是國內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研究此語錄的專書面世。這是與其在禪宗史中,所處的重要地位完全不相稱的,以下首先略具篇幅對《五燈會元》的研究史稍加敘述。
《五燈會元》在撰成以後並不十分廣泛地流傳,但是對於整個佛教界內外,還是產生了或多或少的一些影響,這可以從《五燈會元》大量的續書,以及從當時對此書的直接和間接引用來看,比如在《五燈會元》編成後之《釋氏通鑑》(編年體佛教通史)中就曾對之有間接引用 。至於元代,佛教史的編寫則也有屢次採錄《五燈會元》的情況 ,並且有些典籍則已經對其史實做了一些訂正,比如本覺等所編《釋氏稽古略》卷三之〈邵武龍湖禪師〉條對其卒地就考證曰:
(邵武龍湖)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開元寺,龍湖僧追之。師曰:「山中已有聰禪師,吾不復歸矣。」故龍湖無開山祖師塔,惟有跨虎庵基,為古今之證。諡圓覺禪師。《五燈會元》謂師示寂於龍湖,殆非也 。
查《五燈會元》卷六之〈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條記其卒時云:
師闡化三十餘年,臨示寂,聲鐘集眾。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個歇處。住山聚眾三十年,尋常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安然而逝,塔於本山,諡圓覺禪師 。
因此,二者之間已經存在史料方面之出入了,然二者間仍以前者更為可信,因為前者史料之來源是十分清楚的,在此書卷一中有〈歷代編年釋氏通鑑採摭經傳錄〉,查其中就有:「龍湖行狀」,因而可知本覺編輯其書之時,曾經參考關於龍湖生平的第一手材料,故而其史料價值更加可靠。
另外據宋釋道璨所撰《柳塘外集》卷三〈宗門會要序〉:
宗門書自《傳燈》後傳記日出,學者既不能盡見,亦不暇周覽。閩人朋介石為書曰《宗門會要》,根以《統要》,參以《五燈》。遠而古宿之代別,近而諸方之拈頌,旁而佛鑒大圓之法語,八方珠玉,一展卷而燦焉在目,其惠後學不淺矣 。
由此看來,《宗門會要》一書之編撰,也曾經參考了《五燈會元》中的資料,然而此書今已佚失,具體情況已然不可考矣。雖然有了這樣的一些零星的記載,但就大規模的專門研究而言,則可能還要在很久以後方才出現。
關於此書在當時的研究和流傳情況,我們還可以查勘一下當時的目錄學記載。與普濟約略同時期的南宋藏書家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並沒有記載《五燈會元》,到宋末元初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二十七《經籍考》中,則有《景德傳燈錄》、《天聖廣燈錄》、《建中靖國續燈錄》、《嘉泰普燈錄》,卻無《五燈會元》 。大約同時期的另一位著名目錄學家晁公武,在他的《郡齋讀書誌》卷三下〈釋書〉中,於禪宗類收錄了《宗鏡錄》、《景德傳燈錄》、《傳燈玉英集》、《天聖廣燈錄》、《分燈錄》 、《禪苑瑤林》 等,但也沒有《五燈會元》的蹤影。
約略一百年後之鄭漁仲《通志》卷六十七,〈釋家目錄〉部分,於禪宗語錄則記錄有《真門聖胄集》、《景德傳燈錄》、《傳燈玉英集》等三種,亦未見《五燈會元》之記載。元脫脫等所編《宋史藝文志》中,基本抄集了《文獻通考》之部分,故依然無之。而就內典而言,元代目前僅存的兩部藏經目錄《普寧藏目錄》和《至元法寶勘同錄》中,亦無《五燈會元》之記載,這基本可以反映其時《五燈會元》的普及情況。故而雖然一方面我們從方回的詩句裡,可以看到:「愛僧予尤愛詩僧,千偈萬頌傳《五燈》。寒山拾得兩奇絕,妙壓神秀盧慧能 。」但並不能就此得出,當時《五燈會元》已然是普及到了千家萬戶,家喻戶曉的程度了,可能只是詩家誇張的說法而已。
對於此書的研究,第一個較可注意的時期是明代。因為當時佛教的特點是早期十分興盛,而到了中期的宣宗至穆宗(公元1426-1572年)一百多年中,則呈現整體且持續的衰落狀況。這種情況到了神宗萬曆(公元1573-1619年)時期以後,有了很大的改變,佛教尤其是禪宗經歷了一次全面的復興。而在這個復興的過程中,最明顯的莫過於明代四大師的出現,也就是雲棲蓮池袾宏大師(公元1535-1615年)、紫柏真可大師(公元1543-1603年)、憨山德清大師(公元1546-1623年)、蕅益智旭大師(公元1599-1655年) 。
這種全面的佛教復興,也就必然帶來了對於某些佛教典籍的關注,在這種背景之下,對於禪宗典籍乃至對於《五燈會元》的關注和研究,也就因此而多了起來。而自從宋代以後,以在家信眾於日常世俗生活,從事佛教信仰活動為特色的居士佛教,也漸漸成為了中國佛教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 ,這樣居士也就同時參與到了《五燈會元》的傳播者和評論者的隊伍中來了。
我們先來看看,對於明代初年僧人《續傳燈錄》的編者居頂對《五燈會元》的批判:
某謹按,吳僧道原於宋景德間修《傳燈錄》三十卷,真宗特命翰林學士楊億等裁正而序之,目曰:《景德傳燈錄》。自是禪宗寢盛,相傳得法者益繁衍。仁宗天聖中,則有駙馬都尉李遵勗著《廣燈錄》,建中靖國初則有佛國白禪師為《建中靖國續燈錄》,淳熙十年淨慈明禪師纂《聯燈會要》,嘉泰中雷庵受禪師述《普燈錄》。宋季靈隱大川濟公,以前五燈為書頗繁,乃會粹成《五燈會元》。竊謂《景德傳燈錄》至矣,繼此四燈之錄,寧免得此而遺彼乎。《會元》為書,其用心固善,然不能尊《景德傳燈》為不刊之典,復取而編入之,是為重複矣。今臣幸遇聖明,光讚佛乘,遂忘其僭,纂集《續傳燈錄》……名之曰《續傳燈錄》 。
居頂亦即靈谷圓極居頂,其年代大體為明代初年之臨濟宗禪師,此人也屬於學問僧之列,故曾受敕任僧錄司左講經之職,並曾協助明版大藏經之雕印 。在上述評論中,我們看到了他對於《景德傳燈錄》的推崇和對於《五燈會元》的貶斥。其理由是:「不能尊《景德傳燈》為不刊之典。」這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批評,其實《五燈會元》本身就是以五部燈錄為基礎的,而從文本方面的分析來看,《五燈會元》對於《景德傳燈錄》的史料是異常重視的,並不存在一個不尊重的問題。故而認為「復取而編入之」就是一種重複,這是沒有看到《五燈會元》實際上是在《景德傳燈錄》基礎上,又做了很多的增加、刪節、改寫等工作,總體而言,其批評是沒有多少理論支撐的。
還有一點,就是《續傳燈錄》的重要改變和前兩部燈錄,都是以不同法脈來對紛繁複雜的眾多禪師做不同歸類。圓極居頂認為,南宗都出於慧能門下,故不應再分派別,於是不再以南嶽、青原等二系和五家七宗來編排人物,只以大鑒下多少代為軸心。這在數千人的整個系統裡,就顯得過於粗略了,也反映出他對於《五燈會元》的批評,並沒有多少可取之處。稍後成書於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的《增集續傳燈錄》的作者文琇對《五燈會元》的評價是:
余於少壯時,嘗閱秀紫芝《人天寶鑑》其序有云:「先德有善,不能昭昭於世者,後學之過也。」及觀《五燈會元》若妙峰、北澗、松源、破庵諸老宿,皆未登此書。乃有撰述之志。於是凡見禪宗典籍及塔銘行狀,自宋季及元以來,諸碩德言行超卓者遂筆之,迨今越三十餘年矣。但不能遍歷江湖訪而求之,於心未慊,故於永樂乙未,移書諸大方尊宿,幸籍靈谷幻居和尚、天童即庵和尚展轉搜討。繼而又得郡人吳道玄亦為博尋遺籍,僅有所成,遂用詮次。竊觀《續傳燈錄》於《五燈會元》後,若大鑒第十八世至二十世,曾收三世奈收之未盡。已收者亦言行太略,今於所收外,又增入之。故云《增集續傳燈錄》 。
這裡對於《五燈會元》倒並沒有什麼微詞,其所編輯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對其做些材料上的增補。比如,對於《五燈會元》未編入的一些禪師,在此書中就被編入了卷六的部分之中。有明一代,除僧人漸習《五燈會元》以外,俗人居士也對此書較為稔熟。此可以視,歸有光曾就友人未取此書而例之也 。
另外,我們還可以發現,由於明代文人日益浸淫於內典,故我們還可以在很多考證性的文字中,發現對《五燈會元》的引用 ,這都反映了明代《五燈會元》的流傳已經十分廣泛了。
關於明代《五燈會元》的流行和傳播,我們還是可以從目錄學著作中的記載,找到相關的佐證,比如,明初楊士奇所編的《文淵閣書目》卷十,《釋書錄》記錄五十七部,計三百三十六卷,其中就包括《五燈會元》。另焦理堂《國史經籍志》卷四上、錢溥《祕閣書目‧佛書門》中都錄有此書,這都說明了比起前代而言,其流通要廣泛得多了。故而我們就可以看到一般士大夫中,參習語錄遂成為常事,而其中也就包括了《五燈會元》。如明楊巍所撰《存家詩稿》卷六有《嘲儒》:「尼父不言靜,後儒何怪哉。紛紛諸語錄,皆自《五燈》來 。」
然就總體而言,和後代相比《五燈會元》之流布仍未很廣,直到清代《乾隆大藏經》時,方才得以入藏,這對於其流布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清代不但在大藏經中,將《五燈會元》收錄了進去,另外一部對中國文化影響很大的叢書《四庫全書》中,也收錄了《五燈會元》。這對於其流通的推動也是十分重大的。在《四庫全書》的諸提要部分中,與《五燈會元》相關研究的共有兩篇,第一篇是慧洪《林間錄》的提要:
《林間錄》二卷、《後集》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宋釋惠洪撰。晁公武《讀書志》稱是書所記皆高僧嘉言善行,然多訂讚寧《高僧傳》諸書之訛。又往往自立議論,發明禪理,不盡敘錄舊事也。前有大觀元年謝逸序,稱惠洪與林間勝士抵掌清談,每得一事隨即錄之。本明上人以其所錄析為上下二帙,刻之於板。是其書乃惠洪札記而本明為之編次者。……(慧洪)所作《石門文字禪》釋家收入大藏。又普濟《五燈會元》亦多採此書,蓋惠洪雖僧律多,而聰明特絕,故於禪宗微義能得悟門。又素擅詞華,工於潤色,所述釋門典故皆斐然可觀。亦殊勝粗鄙之語,錄在佛氏書中,固猶為有益文章者矣 。
此提要之要點,在於認為《五燈會元》之編撰曾參考《林間錄》,此說實發前人所未發,由於這涉及到《五燈會元》的史源學部分,筆者會在後面的章節中,著重談到此事,然而有一點可以指出的就是此提要作者,若非對於內典稔熟於胸,則萬萬不能辦到。其二就是《四庫》中所撰《五燈會元》提要:
《五燈會元》二十卷,內府藏本,宋釋普濟撰。普濟字大川,靈隱寺僧也。其書取釋道原《景德傳燈錄》、駙馬都尉李遵勗《天聖廣燈錄》、釋維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聯燈會要》、釋正受《嘉泰普燈錄》,撮其要旨,匯為一書,故曰《五燈會元》。
以七佛為首,次四祖、五祖、六祖,南嶽青原以下各按傳法世數載入焉。蓋禪宗自慧能而後分派滋多,有良价號洞下宗;文偃號雲門宗;文益號法眼宗;靈祐、慧寂號仰宗;義元號臨濟宗,學徒傳授幾遍海內。宗門撰述亦曰以紛繁,名為以不立語言文字為不二法門,實則轇轕紛紜,愈生障礙。
蓋唐以前各尊師說,儒與釋爭。宋以後機巧日增,儒自與儒爭,釋亦自與釋爭。人我分而勝負起,議論所以多也。是書刪掇精英,去其冗雜,敘錄較為簡要。其考論宗系,分篇臚列,於釋氏之源流本末亦指掌了然,固可與《僧寶》諸傳同資,釋門之典故非諸方語錄掉弄口舌者比也 。
《四庫提要》此條解題大體仍算是十分精當,其作者據陳垣先生推測,可能是曆城周永年 。無論撰述者為何人,加上前《林間錄》之解題,所反映的佛教學術素養,都已經是十分高超的了。這種大型叢書對《五燈會元》的收錄,就某種意義而言,可以說是確立了其文獻和宗教價值的一個標誌,自此以後無論僧俗,對於此書的利用就日漸增多。清末另有一件對於《五燈會元》之研究,起到極大推動作用的事件,就是「寶祐本」的回歸和翻刻。
寶祐本之價值,不僅在於它是到目前為止《五燈會元》最早的一個版本,為文本的校訂提供了早期的文字依據。而且還由於在此本中,保留了早期的序文,更解決了像《五燈會元》的編撰者究竟為何人等,數百年來認識上的誤區,這都對以後此方面的研究,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故而我們可以看到當時佛教史的一些研究者中,有些就對此本的諸多問題都展開過討論。
尤其應該提到的是中國禪宗研究的先驅者胡適之先生,在他的文集裡就有著一系列關於此本的文章。比如〈與周法高論所謂景宋寶祐本《五燈會元》的底本的信〉、〈與黃彰健論劉世珩翻刻《五燈會元》的年代的信〉、〈記中央圖書館藏的宋寶祐本《五燈會元》附:後記四則〉、〈論劉世珩翻刻《五燈會元》的「貞治馬兒年」〉、〈記宋寶祐刻本《五燈會元》的刻工〉、〈記「恭仁山莊善本書影」裡的《五燈會元》書影〉、〈記宋槧本容安書院藏與求古樓藏貞治戊申刊本《五燈會元》〉、〈寶祐本的抄補與配補〉、〈楊守敬「留真譜」初編裡的《五燈會元》書影〉 。這些文章之寫出,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至今依然是學界的最高水平。
現略介紹一下此數篇文章之內容:
一、〈與周法高論所謂景宋寶祐本《五燈會元》的底本的信〉乃適之先生給周氏的信,主要是討論貴池劉氏影印宋寶祐的真偽,由於劉氏此本,將日本貞治年翻刻本的三件題記也照樣附於書首,故導致了胡氏的判斷失誤,這點他在後續的研究中,很快就意識到了。但胡氏此信中也敏銳地意識到,此本書首沈氏序對釐清《五燈會元》編者所具有的價值。
二、〈與黃彰健論劉世珩翻刻《五燈會元》的年代的信〉,此信討論的是和史語所,所購至元本殘頁與劉氏本的字數異同,以及《五燈會元》的傳本系統,除前述對劉氏的年代有誤外,基本是十分精當的。
三、〈記中央圖書館藏的宋寶祐本《五燈會元》附:後記四則〉,此篇討論的是中央圖書館的藏《五燈會元》的版本問題,指出此本中,八、九諸卷為寶祐本原刻,至此篇胡氏已經知悉了劉氏復刻本所附三件貞治題記,並非是寶祐本原配。後面繼前幾篇,繼續討論了此本在日本的流傳情況,以及刻工中的王錫乃淳祐二年所刻《心經》之刻工,關於寶祐本刻工的問題,筆者會在版本問題上做更深入的探討。此篇最重要的部分,是關於元刻本曾有改版的發現,胡氏將寶祐本與元刻本做了對勘,發現在後者中多有妄改的情況。此點非常遺憾,我們現通用的蘇淵雷校勘本中,對此問題卻沒有注意到。僅以〈達摩傳〉為例,胡氏就指出有四處改動,到了蘇本中僅出了一處校記 。
四、附後記四篇:
(一)後記一,特意指出對劉氏本,開始不信其為宋本,但經昌彼得等借原本後,又與周、黃、屈討論,才得以糾正在認證期間之誤判。敬佩胡適之先生,不掠人之美、不掩己之過。
(二)後記二,擬出了一個《五燈會元》的版本系統圖。
(三)後記三,乃討論《續藏經》本《五燈會元》的底本問題,指出此本乃是日本翻印明末福州刻本。又有:「後記的後記」一篇討論的是《嘉興藏》本之《五燈會元》刻本。
(四)後記四,討論日本室町時期兩種翻刻本。〈論劉世珩翻刻《五燈會元》的「貞治馬兒年」〉一文,乃是討論「寶祐本」如何傳到日本的問題,並認為貞治馬兒年實乃日本之年號。下一篇〈記宋寶祐刻本《五燈會元》的刻工〉,此本列出了「寶祐本」的刻工,但只考證了其中的王錫一人。
短文〈記「恭仁山莊善本書影」裡的《五燈會元》書影〉,記錄了所見的內藤湖南博士遺書中,室町時期翻刻本的簡要情況。〈記宋槧本容安書院藏與求古樓藏貞治戊申刊本《五燈會元》〉乃容安書院所藏宋本《五燈會元》殘頁的一個行款簡錄。《寶祐本的抄補與配補》乃記錄了今所傳「寶祐本」,乃經過某一不知名的日僧抄補配補的介紹。《楊守敬留真譜初編裡的五燈會元書影》乃介紹楊氏《留真譜》中,所錄「寶祐本」行款的一些特點。
從上面的介紹可以知道,此一系列文章對於「寶祐本」的底本、年代、刻工和當時刻印的一些細節,以及劉氏翻刻的年代等問題,都做了非常獨到的考證,這其中很多即使是在今日,也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流的成果,顯示了作者精湛的文獻功力。
此後由民國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之間,《五燈會元》之研究大體則甚為寥落,其實此一時期,佛教研究之一個大宗就是禪宗方面的研究 。故而在諸多的禪學以及禪宗史方面的重要著述之中,就難免總會涉及到《五燈會元》,這包括像印順《中國禪宗史》 、楊曾文《唐五代禪宗史》 、顧偉康《禪宗六變》、《禪淨合一流略》 、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通史》 、葛兆光《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9世紀》 、洪修平《禪宗思想的形成與發展》 。
但就專章研究則只有陳垣先生《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四之《五燈會元》部分,此部分所論述之問題包括第一,「《會元》之體制及內容」此部分為《五燈會元》之內容和普濟所出之派系。次為,「《會元》版本及撰人問題」此節討論「寶祐本」對於《五燈會元》編者推定之意義,以及慧明是否為慶元五年,常照寺僧的問題等等。
時至八○年代以後,陳士強的著作《佛典精解》中,對《五燈會元》也有極為精彩的解題。在此部解題中,先論及《五燈會元》各藏經之收藏,次及編者問題,然後各章節的一個詳細解題,最後再以具體例證,討論《五燈會元》與另外五部燈錄之間的聯繫與區別,總之此篇是到目前為止對《五燈會元》最為詳盡的研究。
除此之外,大體上都是一些語言學方面的研究,這主要是因為禪宗語言極具特色,其淳樸、鄙野的原始特徵,對研究唐宋時代的口語極有價值,故而在漢語史研究上,非常流行對於某種燈錄的語言做專題研究,此方面的文章相對而言是比較多的。
此姑舉數例說明如下:
一、沈丹蕾所撰〈《五燈會元》的句尾語氣詞「也」〉 中,以《五燈會元》為例說明句尾語氣詞「也」的用法變化。因為在古代漢語中,主要表示靜態的肯定和判斷,而近代漢語中「也」的使用範圍擴大,增加了表示事態變動的新功能。而《五燈會元》的句尾語氣詞「也」不僅保留著它在古漢語中的用法,而且具備了與語氣詞「了」相同的表示事態變化的功能。此種研究傾向,在中國大陸也呈現同樣的局面。
二、具熙卿所撰〈《五燈會元》、《碧巖集》、《景德傳燈錄》中所見的被字句分析〉 。此文以《五燈會元》等書中的語言材料為佐證,分析宋代佛教的被動句式,在此三本禪宗著作中,被動句式主要有:「為字句」和「被字句」兩種,而以後者更為常見。並以文獻材料為基礎,分析了「被字句」的複雜結構和形式。除了這樣一種以《五燈會元》一書或幾種禪宗典籍中的材料,表態分析其語言學問題之外,另有從多部語錄之變化動態分析的方法。
三、張美蘭所撰〈論宋代禪宗的語言特色:從《祖堂集》與《五燈會元》語言的風格差異入手〉 為例,此文結合禪宗發展史和漢語語言發展史,在對《祖堂集》和《五燈會元》的文獻語言風格對比之後,側重闡述了宋代禪宗語言的語言學特點,探尋其差異出現的原因,並進一步探討其在漢語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此一語言學方面的研究文章非常多,由於與本文所研究的角度相差較大,故不再一一羅列。
除了這些佛教語言學方面的研究之外,對於《五燈會元》文獻學方面的研究則有項楚先生,項楚做為文獻學研究界的重要學者,其治學範圍較廣,餘力所及也兼治禪宗語言,對於《五燈會元》所做的研究主要是版本的校勘。其發表的作品是〈《五燈會元》點校獻疑三百例〉 、〈《五燈會元》點校獻疑續補一百例〉 。
另馮國棟博士對此方面也有研究,馮氏目前研究有兩個重點,一是燈錄史,一是佛教目錄學。關於《五燈會元》的研究則是其第一方面的成就,具體有〈《五燈會元》校點疏失類舉〉 ,此文主要是針對1984年蘇淵雷校本而發,其校正蘇本之誤近百例之多,其中包括「影宋本不誤點校本轉錄致誤例」、「未能以續藏本、龍藏本正影宋本之失例」、「不明名義點斷致誤例」、「專名號使用失誤例」等數種失誤,為一次對蘇本較為全面的清理。另一篇為〈《五燈會元》版本與流傳〉 ,此篇考察了《五燈會元》歷代的刊刻情況,對《五燈會元》的各種版本做了較為全面的描述,並在此基礎上研究了此書在歷代的流布,就總體而言,此篇文章是到目前為止對《五燈會元》版本研究較為重要的成果。
從以上《五燈會元》研究情況的總體分析來看,大體上由於其流傳方面的原因,學者對其研究之發現實為明代,到了清末民初由於新版本的發現,又進一步推動了其後的發展,為《五燈會元》研究中,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提供了可行性的解決線索。而真正具有現在學術規範研究的開拓者是陳援庵先生。此方面到了八○年代以後,則又有陳士強教授的研究。在此之外,除了漢語史方面的研究,對此方面做出貢獻則有項楚和馮國棟等的文獻學研究。這樣一種冷清的局面,是和《五燈會元》其自身價值遠遠不能相稱的,故而筆者希望能通過此文的寫作來對此稍加改變。
第二節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本文主要採取文獻學和歷史研究的方法。首先,本文採取文獻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尤其是側重於版本的校勘與研究。在校勘方面,一方面通過傳統的本校與對校法,利用不同版本之間的校對來盡量考訂《五燈會元》一千多年來,傳抄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錯誤,乃至其他有意或無意的失誤。這實際上是出於一個非常實際的需要,就是筆者希望能以更新的校勘理念、多樣的校勘手法、搜集更多的版本,以及精力的更大投入,以求能整理出一個,比目前學界所最常使用的版本,更加方便並且準確的校訂本。而本文在校勘與版本,乃至於史源學上的研究成果與實際經驗,主要是為了今後《五燈會元》的進一步整理做些材料方面的準備。
另外,本文研究方面的另一個特點,是在校勘四法之中主要利用他校法。此點乃與本文的另一個研究目的有關,即為了廓清《五燈會元》其編輯過程中,具體使用了哪些史源及其材料採擷上的標準。這種史源學上的推考,主要是為了恢復在禪宗史的宏觀背景之下,《五燈會元》編纂之時的禪宗史料存世情況。並由此考察當時禪宗不同派系之間,利用編輯史料之辦法來相互傳播,自己所在特定派系的不同宗教思想。此點在本文中,則主要牽涉到了臨濟宗的一些宗派。
比如著名的「大慧派」,此派乃由大慧宗杲所創立。非常值得研究,而且也饒有趣味的是,大慧本人以「看話禪」為特色而鳴於世。並欲焚其師之書,這本來是在中唐以降,禪宗的禪法漸漸廢弛,而禪僧則多沉迷於法語、公案,以至於多以語句之發明為參悟之道,甚至流連於祖師法語的註釋而忘返。其主張「看話禪」正是對此種繁瑣的經學主義的離棄,但是我們卻應該看到,在另一方面,熱衷於禪宗史籍編撰的又恰恰是「大慧派」傳人 。在這樣一個歷史發展的正反合裡,其中確實透露了很多的宗教和社會信息,而筆者也希望能通過,對於本文的寫作來窺其一斑。
本文的第二個研究方法,是歷史主義的研究方法,首先盡量將《五燈會元》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加以關照。盡最大的可能性,恢復其文本編纂時的原生狀態,期以同情默應的態度,來理解當時編著者們的心境。以此來研究當時禪宗發展,乃至臨濟宗發展的一般以及特殊情境。就實際而言,我們從禪宗歷代記錄中,所看到的史和當時真實的史之間,是存在一個很大的差距。
一方面,客觀上認為人類的任何一種記錄工具,都不可能將我們,哪怕同時代的活生生的歷史,完完整整地記錄下來;另一方面,由於記錄者本身也都是一些有思想傾向的、具有獨特視角的人,那麼在他們的記錄中,我們所看到的史,其實就很大程度而言,只不過是他們想讓我們知道的歷史,而不是那個沒有愛憎偏見的完整的史。這種情況在禪宗史中顯得尤為突出,有時候我們會發現很多的宗教家,都有「編造」歷史的習慣。以前當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我們對此總是嗤之以鼻,其實我們更應該看到即使是偽史,其背後也有真實的宗教關懷在,而後者也正是我們研究所應該關注的。
在具體的思路和研究計畫上,和一般文獻學的基本研究方法非常一致,首先筆者初期的工作重心,主要是放在各種史料的比對校勘之上,這佔據全部研究計畫一半以上的時間。筆者在此文中的絕大多數觀點,都是在這個漫長而充滿艱辛的校勘過程中逐個得來,筆者在文中所要表達的思想,也在此一過程之中慢慢成形。這也是筆者在文獻學學習的過程中,所得來的一點小小的心得,即在研究之前並沒有一個一定要表達的思想,而是讓材料自身去展現其本來就有的觀點,這就不會導致刻意去搜集材料,而產生先入為主地論證某種觀念的弊病。
在校勘學的具體方法上,前面筆者已經提到,限於本文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集中於史源學的範圍,所以採用最多的是他校法。這種方法對於文獻整理而言,最大的好處在於可以以某種經典為中心而觸類旁通,兼及某一橫向歷史切面之上的諸多宗教史料,並由此克服個案研究所最容易產生的「只見樹木,不見樹林」的弊病。
在對《五燈會元》的史源學考察之中,由於其史料最早來源於北宋初年,景德年間之《景德傳燈錄》,而《五燈會元》本身則成書於南宋即將覆滅的末期。這樣在史料的時間跨度之上,就橫亙了幾乎天水一朝的全部,也可以從中相當完整地涵括了宋代禪宗發展的全部過程。實際並不止此,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五燈會元》的史料採集,甚至有兼及北宋立朝之前的早期大德語錄的情況,這就使論文的發展具有了縱向的延展度。
在各種史料的比對校勘完成以後,剩下的工作就是對各種寫作素材,做重新的分類與剪裁,然後在此基礎之上寫作論文。文獻學研究並非是萬靈藥,其工具性的特點實乃其最大的局限。我們一方面不能估計此種文獻研究,在整個學術體系之中的基礎作用,另一方面則絕不能把文獻之研究當作學術的終結。由於筆者自身僅局限於文獻學的這一缺陷,就顯得更加放大,所以對此,筆者一直將之銘感於心。
從《五燈會元》的情況來看,我們必須知道,就實際定位,它並不是被當作一種純客觀的「史」來編纂的,而只是附著於特定宗教情感關懷之下,具有特定宗派意義,並傳達其宗教理念的傳承世系。在《五燈會元》的編者心中「歷史本身是如何?」其重要性是讓位於「歷史應該是如何?」對此點筆者一直都有著較為清醒的認識,否則就會偏離整個研究的基礎方向,這也是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最重要的一個研究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