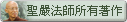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當呼吸化為空氣:一位天才神經外科醫師最後的生命洞察
譯者:唐勤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16年08月02日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84頁 / 15 x 21 cm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50120661
ISBN:9789571367286
定價:NT$320
會員價:NT$272 (85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章節試閱
↑TOP
要是我會寫書,我會編輯一個各類死亡的紀事錄,加上評論:能教死,必能教生。
—〈讀哲學就是學怎麼死),米歇爾.德.蒙田
病床上,我躺在露西身邊,兩人都在哭,CT掃描影像還在電腦螢幕上發光。醫師的身分—我的身分—從此無關緊要。癌細胞已經侵入多個器官系統,診斷十分明確。病房很安靜。露西告訴我她愛我。「我不想死,」我說。告訴她要再婚,我無法忍受想到她一個人過日子。我告訴她,我們應該馬上把房屋貸款拿去重新融資。我們開始打電話給家人。某一刻,維多利亞來到病房,我們討論掃描影像,以及未來可能的治療。當她提起回來當住院醫師的種種現實準備時,我打斷她。
「維多利亞,」我說,「我不會回醫院當醫師了。你不覺得嗎?」
我生命的一章似乎結束了;也許整本書都在收尾。與其成為牧師般的角色,協助另一個生命轉型,我發現自己才是那頭迷失而惶惑的羊。重病不僅改變生命,更是粉碎生命。感覺這不太像天啟(一道刺眼的疾光,照亮「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比較像某個人剛剛丟下燃燒彈,夷平往前的道路。現在,我得繞道而行。
弟弟基凡已經來到床邊。「你完成了這麼多事情,」他說。「你知道的,對不對?」
我嘆氣。他是好意,可是那話好空洞。我這一生一直在累積自己的潛力,如今無用武之地的潛力。我計畫要做的事這麼多,而且已經如此接近實現的邊緣。我身體不再能行動,我想像中的未來、我個人的身分認同一起幻滅,而我面對的是病人同樣面對的存在困境。肺癌的診斷已經證實。我小心翼翼計畫並努力追求到手的未來從此不存。死亡,在我的工作中如此熟悉的因素,現在造訪我本人。我們就在這裡,終於直視彼此,然而它似乎沒有任何我能辨認的特徵。站在交叉路口,我本來應該看見並追隨幾年來我治療過的無數個病人的腳印,然而我只見到一片發亮的白色沙漠,空白,難以逼視,沒有任何東西,就好像一場沙暴泯滅了所有熟悉的痕跡。
太陽正在西下。第二天我就會出院。癌症醫師的約診時間已經訂好,就在這個星期稍晚。不過護士告訴我,我的癌症醫師當晚離開醫院去接小孩以前,會先來一趟。她的名字是艾瑪.海沃,她想在初次正式看診前先來打聲招呼。我跟艾瑪稍有接觸。我曾經治療過她的幾個病人,可是除了工作上的禮貌寒暄外,我們從來沒有其他交談。我父母和兄弟在病房的不同角落,沒說什麼話,而露西坐在床邊,握著我的手。房門開了,艾瑪步入,她的白袍透露了她經歷很長的一天,可是她的微笑清新。跟在她身後的是研究醫師和住院醫師。艾瑪只比我大幾歲,頭髮黑而長,可是一如所有跟死亡頗有接觸的人一樣,髮中夾雜幾綹灰白。她抓過一張椅子。
「嗨,我叫艾瑪,」她說。「很抱歉今天我只能待很短的時間,不過我想先過來自我介紹。」
我們握手。點滴線纏著我的手臂。
「謝謝你過來一趟,」我說。「我知道你要接小孩。這是我的家人。」
她點頭向露西、我的兄弟、我的父母致意。
「很抱歉這事發生在你身上,」她說。「發生在你們所有人身上。過兩天,我們有很多時間可以談。我已經先要檢驗室開始對你的腫瘤樣本做些檢測,這樣可以協助指引治療方向。也許是化療,也許不是,要看檢測結果。」
十八個月前,我曾經因為闌尾炎住院。當時我不像病人,反而被當成同事一樣對待,幾乎就是我自己病例的一個諮詢醫師。我預期現在也是同樣的狀況。「我知道現在不是時候,」我開始說,「不過我會想討論Kaplan-Meier 存活曲線。」
「不行,」她說。「絕對不行。」
短暫的沉默。她憑什麼?我心想。這是醫師(像我這樣的醫師)理解預後的方式。我有權知道。
「我們可以以後再談治療方案,」她說。「我們也可以討論你日後回去工作, 如果你想回去的話。傳統化療使用的複合藥劑, cisplatin、pemetrexed,可能還加上Avastin,產生末梢神經病變的比例頗高,所以我們大概會換下cisplatin,改用carboplatin,對你的神經有較好的保護,因為你是外科醫師。」
回去工作?她在說什麼?她昏頭了嗎?還是我對自己的預後完全搞錯了?對存活率沒有現實的預估之前,我們怎麼能談論這些事情?最近幾天大地已在我腳下搖晃、崩裂,此刻又來一次。
「細節可以以後談,」她繼續說,「我知道這是一大堆要吸收的東西。最主要的是,我想在星期四約診前先見見你們。今天還有任何我可以做,或任何需要我回答的問題嗎?除了存活曲線之外。」
「沒有,」我說,腦袋發暈。「很謝謝你來一趟。我真的很感激。」
「這是我的名片,」她說,「這是看診室的電話。如果這兩天有任何事情,隨時打給我。」
我的親友很快就在醫界同事圈裡送出訊息,尋找全國最好的肺癌專科醫師。休士頓和紐約有主要的癌症中心;我應該去那裡治療嗎?搬家或暫時遷
居等等現實考慮,以後再弄清楚就好,還不急。回覆來得很快,差不多意見一致:艾瑪不但是最好的醫師之一(世界知名癌症專家、全國性主要癌症諮詢委員會成員),而且她以慈悲知名,知道什麼時候推一把,什麼時候讓一步。我有一會兒不禁自問,為什麼這一連串的事件讓我環繞世界一圈,電腦的配對軟體決定送我來此進行住院醫師訓練,然後我莫名其妙得了這個病,結果竟然落入最棒的醫師手中接受治療。
這個星期我多半臥床休息,癌症持續發展,我明顯虛弱不少。我的身體,以及與之緊密連結的身分,發生劇烈變化。下床上廁所不再是不經思考的皮質下運動程式,而是需要努力與策畫的活動。物理治療師給我一張單子,列出的物品可以幫忙我過渡到居家療養:手杖、修改過的馬桶座、休息時用來支撐腿部的乳膠塊。醫師開了一堆新的鎮痛藥。當我一跛一跛地走出醫院,我想知道,六天前我怎麼能在手術室連續待上將近三十六個小時?難道一週之內,我的病就變得這麼嚴重?是的,有一部分是真的。可是,我當初也運用了一些技巧,並且靠外科同僚的協助才捱過那三十六小時。還有,儘管那樣,我一直在承受難熬的痛楚。我所害怕的診斷結果得到肯定(CT掃描、實驗室檢測不只透露了癌症的端倪,而且顯示我的身體已經應付不了,逼近死亡),是否就卸下了我服務眾人的責任?卸下了我對病人、對神經外科、對行善的責任?沒錯,我想,悖論就在這裡:就像跑者衝過終點線之後倒下,一旦照顧病患的責任不再推我前行,我就成了廢人。
通常當我的病人有奇特症狀時,我會諮詢該領域的專家,花時間閱讀相關資料。現在似乎沒有什麼不同。可是,當我開始閱讀化療資訊,裡面包含種種藥劑,以及針對特定突變的現代創新療法,我的問題多到根本無法進行有方向的有用研究。詩人亞歷山大.波普說:「學習一點是件危險的事;/深深汲飲,否則別嚐皮埃里亞之泉。」沒有恰當的醫學經驗,我無法在這個訊息的新世界裡找到定位,也無法為自己在Kaplan-Meier 曲線上找到定點。我等著,以期待的心情,去見醫師。
不過,多半我都在休息。
我坐起,盯著露西和我在醫學院拍的一張相片,我們跳著舞笑著;多麼悲傷,那兩個人計畫共度此生,絲毫不覺,也完全沒有預想到自身的脆弱。
我的朋友羅莉死於交通意外時已經有未婚夫了—這更殘酷嗎?
我的家人忙忙碌碌地進行各種活動,將我的生活從醫師轉變為病人。
我們在一家郵購藥品店開立帳戶,訂購了床護欄,買了一張人體工學床墊以減輕折磨人的背痛。我們的財務計畫現在看來搖搖欲墜。幾天前我們還仰賴著下一年我將增為六倍的收入,接下來似乎需要新的財務工具來保護露西。
我父親宣稱,這些調整是向疾病低頭—我會擊敗它,會有某種方法治癒我的。有多少次我聽到病人家屬做出類似宣言?以前我從來不知道要對他們說什麼,而現在我不知道要對父親說什麼。
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另一個可能故事會如何發展?
兩天後,露西和我在診療室跟艾瑪碰面。我父母在候診室裡走來走去。
醫療助理替我做了例行檢查。艾瑪和專科護理師的準時令人嘉許,艾瑪拉來一張椅子坐到我面前,面對面、兩眼平視地跟我交談。
「又見面了,」她說。「這位是阿列克絲,我的得力臂膀。」她朝專科
護理師做了個手勢,後者坐在電腦前記錄。「我知道有很多事情要討論,不過,第一件事:你覺得怎麼樣?」「還可以,把所有事情考慮在內的話,」我說。「享受我的『放假』,我想。你好嗎?」
「噢,我還行。」她停了下來—病人通常不會問醫師好不好,可是艾瑪也是同事。「這禮拜輪到我管住院, 所以你知道會是什麼樣子。」她微笑。露西和我是知道的。門診專科醫師不時要輪值住院部門工作,在已經擠得滿滿的一天裡外加幾小時的工作。
繼續寒暄一會兒後,我們自然而然地進入肺癌研究現況的討論。有兩個途徑可走,她說。傳統方法是化療,針對目標是所有快速分裂的細胞—主要是癌細胞,不過也包括骨髓、毛囊、腸道之類的細胞。艾瑪覆述了數據和選項,彷彿在對醫師上課,不過再次略過Kaplan-Meier 存活曲線的任何提示。然而,已發展出來的較新治療方法,針對目標則是癌症本身特定的分子缺陷。我聽過這種研究的傳言(這一直是癌症治療的聖杯),很驚異地知道如今進展有多大。這些治療似乎已經讓「某些」病人可以長期存活。
「你大部分檢驗的結果都送來了,」艾瑪說。「你有一個PI3K 突變,不過我們尚未明瞭它的意義。你這類病患最常見的突變,EGFR,檢查結果還沒出來。我打賭你應該會有。如果正確,你可以吃一種藥,叫做Tarceva,而不需要做化療。那項結果應該明天星期五會送來,不過你病得已經夠重,因此我訂星期一開始化療,以免EGFR 檢測是陰性的。」
我立即感到一種血緣般的親近。這正是我在神經外科的行醫方式:手上總是有A、B、C幾個計畫。
「關於化療藥物,我們主要會從carboplatin 跟cisplatin 當中選擇一種。
在若干孤立的研究中,它們兩個相比,身體對c a rbopl a t in 的耐受性較高。
c i spl a t in 可能效果較佳,但是毒性高很多,特別是對於神經的毒性,不過所有數據都很舊,而且沒有跟現代化療療程的直接比較。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對於保護自己的手以繼續開刀,不那麼在意,」我說,「我可以做
很多不同的事情。如果失去雙手,我可以從事另一行,或者不工作,或者幹什麼別的。」
她停了一下。「我這麼問你好了:開刀對你重不重要?是不是你想做的事情?」
「嗯,是重要,我幾乎花了這輩子的三分之一在準備這件事。」
「好的, 那麼我要建議我們採用c a r b opl a t in。我不認為它會改變存活率,不過它會劇烈改變你的生活品質。有沒有其他問題?」
她似乎很清楚這是該走的方向,我樂意追隨。也許,我開始讓自己相信,再度操刀是有可能的。我感覺自己輕鬆了一點。
「我可以開始抽煙了嗎?」我開玩笑。
露西笑出來,艾瑪兩眼打轉。
「不行。有沒有認真的問題?」
「Kaplan-Meier ⋯⋯」
「我們不討論那個,」她說。
我不了解她的抗拒。畢竟,我是熟悉這些統計數字的醫師。我可以自己去查⋯⋯那好,我必須那麼做。
「好吧,」我說。「我想事情都相當清楚了。明天我們會從你這兒得知
EGFR 的結果。如果陽性,就開始服用Tarceva,如果陰性,那麼星期一開始化療。」
「對。另外有件事我希望你知道:我現在是你的醫師了。有任何問題,從一般醫療到不管其他什麼問題,你都先找我們。」
又一次,我被血緣般的親近感扎到了。
「謝謝,」我說。「住院病房那裡,祝你好運了。」
她出了診間,卻在一秒鐘之後探頭進來。「你大可拒絕沒關係,不過有些肺癌基金的募款人很想見你。現在還不用回答。考慮考慮,然後告訴阿列克絲你有沒有興趣。別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
我們離開時,露西說道,「她太棒了。她很適合你。不過⋯⋯」她露出笑容。「我覺得她喜歡你。」
「所以?」
「嗯,有一個研究說,當醫師有個人因素摻雜進來時,對病人的預後判斷會比較差。」
「我們的擔憂清單又多了一項,」我笑了一聲。「我想,它落在重要性最低的那個象限。」
我開始了解,跟自己的大限如此近距離地接觸,既改變了一切,也什麼都沒改變。在癌症確診以前,我知道自己有天會死,可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確診之後,我知道自己有天會死,可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不過現在我很明白,這其實不是科學問題。死亡的事實令人不安。然而,沒有別的方式可活。
逐漸地,醫學的迷霧開始散開—至少現在我有足夠的資訊可以一頭栽入文獻。雖然數字還很模糊,有EGFR 突變似乎會增加一年的平均壽命,還有長期存活的潛力;如果沒有,意味著兩年內死亡機率為百分之八十。弄清楚我的餘生將是一個變化不斷的過程。
第二天,露西和我去一家精子銀行,保存生殖細胞以及未來選項。我們一直計畫當我住院訓練結束時要生孩子,但是現在⋯⋯癌症藥物對我的精子有未知的影響。因此,為了保留生孩子的機會,我們必須在治療開始前冷凍精子。一個年輕女子為我們一一解釋不同的付款計畫、庫存的選擇,以及擁有者的法律表格。她的桌上有許多彩色小冊子,是關於年輕癌症患者的各種社交聚會:即興表演聚會,無伴奏合唱團、自動上台演唱的晚會,等等。我嫉妒他們快樂的臉,心裡明白,在統計上,他們患的大概都是擁有高治癒率的癌症,也有合理的預期壽命。三十六歲的人只有百分之○.○○一二會得到肺癌。是的,患上癌症的所有病人都很不幸,不過有的患了癌症,有的卻患了癌症,得到後者的是真正倒了大楣。當她問我們,如果我倆有一人「萬一死去」,如何指定精子的未來—死後誰合法擁有精子—淚水滾落露西的臉頰。
「希望」這個字大約一千年前首次出現在英文裡,指的是信心和欲求的某種結合。可是我欲求的—生命,並非我有信心會發生的—死亡。那麼,當我談希望的時候,我的意思真的是「留些空間給無根據的欲求」嗎?
不是的。醫學統計不只講出數據,例如平均存活率,還有測量我們對那些數字有多少信心的工具,像是信賴水準、信賴區間、信賴界限之類的。那麼,我的意思是「留些空間給統計上不可能但是仍然有機會發生的結局—恰好高於信賴區間值百分之九十五的存活比」嗎?這就是希望嗎?我們能不能把曲線劃分為若干量化的存在感線段,從「一籌莫展」到「悲觀」到「符合現實」到「抱著希望」到「妄想」?難道數字不只是數字嗎?我們是不是總覺得每一個病人都高於平均值,於是向這種「希望」繳械投降了?
我突然想到,一旦我成了統計之一,我跟統計的關係就改變了。
住院醫師期間,我跟數不清的病人和家屬坐下來討論灰暗的預後;作為醫師,那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當病人是九十四歲,處於失智症末期,事情容易得多。可是像我這樣,三十六歲,被診斷為罹患末期癌症,真的沒有任何言語可用。醫師不給病人明確的預後,原因不只是他們無法辦到。當然,要是病人的預期遠遠超過現實,譬如說,有人期待活到一百三十歲,或者有人認為良性皮膚斑點是瀕臨死亡的跡象,那麼醫師有義務將病人的預期拉回合理的機率範疇。病人想要的並非醫師隱藏起來的科學知識,而是貨真價實的存在感,後者其實必須靠自己去追尋。過分深入數據,就像喝海水止渴。面對人生大限的焦慮,不會在統計機率裡找到療癒。
—〈讀哲學就是學怎麼死),米歇爾.德.蒙田
病床上,我躺在露西身邊,兩人都在哭,CT掃描影像還在電腦螢幕上發光。醫師的身分—我的身分—從此無關緊要。癌細胞已經侵入多個器官系統,診斷十分明確。病房很安靜。露西告訴我她愛我。「我不想死,」我說。告訴她要再婚,我無法忍受想到她一個人過日子。我告訴她,我們應該馬上把房屋貸款拿去重新融資。我們開始打電話給家人。某一刻,維多利亞來到病房,我們討論掃描影像,以及未來可能的治療。當她提起回來當住院醫師的種種現實準備時,我打斷她。
「維多利亞,」我說,「我不會回醫院當醫師了。你不覺得嗎?」
我生命的一章似乎結束了;也許整本書都在收尾。與其成為牧師般的角色,協助另一個生命轉型,我發現自己才是那頭迷失而惶惑的羊。重病不僅改變生命,更是粉碎生命。感覺這不太像天啟(一道刺眼的疾光,照亮「真正重要的事情」),反而比較像某個人剛剛丟下燃燒彈,夷平往前的道路。現在,我得繞道而行。
弟弟基凡已經來到床邊。「你完成了這麼多事情,」他說。「你知道的,對不對?」
我嘆氣。他是好意,可是那話好空洞。我這一生一直在累積自己的潛力,如今無用武之地的潛力。我計畫要做的事這麼多,而且已經如此接近實現的邊緣。我身體不再能行動,我想像中的未來、我個人的身分認同一起幻滅,而我面對的是病人同樣面對的存在困境。肺癌的診斷已經證實。我小心翼翼計畫並努力追求到手的未來從此不存。死亡,在我的工作中如此熟悉的因素,現在造訪我本人。我們就在這裡,終於直視彼此,然而它似乎沒有任何我能辨認的特徵。站在交叉路口,我本來應該看見並追隨幾年來我治療過的無數個病人的腳印,然而我只見到一片發亮的白色沙漠,空白,難以逼視,沒有任何東西,就好像一場沙暴泯滅了所有熟悉的痕跡。
太陽正在西下。第二天我就會出院。癌症醫師的約診時間已經訂好,就在這個星期稍晚。不過護士告訴我,我的癌症醫師當晚離開醫院去接小孩以前,會先來一趟。她的名字是艾瑪.海沃,她想在初次正式看診前先來打聲招呼。我跟艾瑪稍有接觸。我曾經治療過她的幾個病人,可是除了工作上的禮貌寒暄外,我們從來沒有其他交談。我父母和兄弟在病房的不同角落,沒說什麼話,而露西坐在床邊,握著我的手。房門開了,艾瑪步入,她的白袍透露了她經歷很長的一天,可是她的微笑清新。跟在她身後的是研究醫師和住院醫師。艾瑪只比我大幾歲,頭髮黑而長,可是一如所有跟死亡頗有接觸的人一樣,髮中夾雜幾綹灰白。她抓過一張椅子。
「嗨,我叫艾瑪,」她說。「很抱歉今天我只能待很短的時間,不過我想先過來自我介紹。」
我們握手。點滴線纏著我的手臂。
「謝謝你過來一趟,」我說。「我知道你要接小孩。這是我的家人。」
她點頭向露西、我的兄弟、我的父母致意。
「很抱歉這事發生在你身上,」她說。「發生在你們所有人身上。過兩天,我們有很多時間可以談。我已經先要檢驗室開始對你的腫瘤樣本做些檢測,這樣可以協助指引治療方向。也許是化療,也許不是,要看檢測結果。」
十八個月前,我曾經因為闌尾炎住院。當時我不像病人,反而被當成同事一樣對待,幾乎就是我自己病例的一個諮詢醫師。我預期現在也是同樣的狀況。「我知道現在不是時候,」我開始說,「不過我會想討論Kaplan-Meier 存活曲線。」
「不行,」她說。「絕對不行。」
短暫的沉默。她憑什麼?我心想。這是醫師(像我這樣的醫師)理解預後的方式。我有權知道。
「我們可以以後再談治療方案,」她說。「我們也可以討論你日後回去工作, 如果你想回去的話。傳統化療使用的複合藥劑, cisplatin、pemetrexed,可能還加上Avastin,產生末梢神經病變的比例頗高,所以我們大概會換下cisplatin,改用carboplatin,對你的神經有較好的保護,因為你是外科醫師。」
回去工作?她在說什麼?她昏頭了嗎?還是我對自己的預後完全搞錯了?對存活率沒有現實的預估之前,我們怎麼能談論這些事情?最近幾天大地已在我腳下搖晃、崩裂,此刻又來一次。
「細節可以以後談,」她繼續說,「我知道這是一大堆要吸收的東西。最主要的是,我想在星期四約診前先見見你們。今天還有任何我可以做,或任何需要我回答的問題嗎?除了存活曲線之外。」
「沒有,」我說,腦袋發暈。「很謝謝你來一趟。我真的很感激。」
「這是我的名片,」她說,「這是看診室的電話。如果這兩天有任何事情,隨時打給我。」
我的親友很快就在醫界同事圈裡送出訊息,尋找全國最好的肺癌專科醫師。休士頓和紐約有主要的癌症中心;我應該去那裡治療嗎?搬家或暫時遷
居等等現實考慮,以後再弄清楚就好,還不急。回覆來得很快,差不多意見一致:艾瑪不但是最好的醫師之一(世界知名癌症專家、全國性主要癌症諮詢委員會成員),而且她以慈悲知名,知道什麼時候推一把,什麼時候讓一步。我有一會兒不禁自問,為什麼這一連串的事件讓我環繞世界一圈,電腦的配對軟體決定送我來此進行住院醫師訓練,然後我莫名其妙得了這個病,結果竟然落入最棒的醫師手中接受治療。
這個星期我多半臥床休息,癌症持續發展,我明顯虛弱不少。我的身體,以及與之緊密連結的身分,發生劇烈變化。下床上廁所不再是不經思考的皮質下運動程式,而是需要努力與策畫的活動。物理治療師給我一張單子,列出的物品可以幫忙我過渡到居家療養:手杖、修改過的馬桶座、休息時用來支撐腿部的乳膠塊。醫師開了一堆新的鎮痛藥。當我一跛一跛地走出醫院,我想知道,六天前我怎麼能在手術室連續待上將近三十六個小時?難道一週之內,我的病就變得這麼嚴重?是的,有一部分是真的。可是,我當初也運用了一些技巧,並且靠外科同僚的協助才捱過那三十六小時。還有,儘管那樣,我一直在承受難熬的痛楚。我所害怕的診斷結果得到肯定(CT掃描、實驗室檢測不只透露了癌症的端倪,而且顯示我的身體已經應付不了,逼近死亡),是否就卸下了我服務眾人的責任?卸下了我對病人、對神經外科、對行善的責任?沒錯,我想,悖論就在這裡:就像跑者衝過終點線之後倒下,一旦照顧病患的責任不再推我前行,我就成了廢人。
通常當我的病人有奇特症狀時,我會諮詢該領域的專家,花時間閱讀相關資料。現在似乎沒有什麼不同。可是,當我開始閱讀化療資訊,裡面包含種種藥劑,以及針對特定突變的現代創新療法,我的問題多到根本無法進行有方向的有用研究。詩人亞歷山大.波普說:「學習一點是件危險的事;/深深汲飲,否則別嚐皮埃里亞之泉。」沒有恰當的醫學經驗,我無法在這個訊息的新世界裡找到定位,也無法為自己在Kaplan-Meier 曲線上找到定點。我等著,以期待的心情,去見醫師。
不過,多半我都在休息。
我坐起,盯著露西和我在醫學院拍的一張相片,我們跳著舞笑著;多麼悲傷,那兩個人計畫共度此生,絲毫不覺,也完全沒有預想到自身的脆弱。
我的朋友羅莉死於交通意外時已經有未婚夫了—這更殘酷嗎?
我的家人忙忙碌碌地進行各種活動,將我的生活從醫師轉變為病人。
我們在一家郵購藥品店開立帳戶,訂購了床護欄,買了一張人體工學床墊以減輕折磨人的背痛。我們的財務計畫現在看來搖搖欲墜。幾天前我們還仰賴著下一年我將增為六倍的收入,接下來似乎需要新的財務工具來保護露西。
我父親宣稱,這些調整是向疾病低頭—我會擊敗它,會有某種方法治癒我的。有多少次我聽到病人家屬做出類似宣言?以前我從來不知道要對他們說什麼,而現在我不知道要對父親說什麼。
如果不是這樣,那麼另一個可能故事會如何發展?
兩天後,露西和我在診療室跟艾瑪碰面。我父母在候診室裡走來走去。
醫療助理替我做了例行檢查。艾瑪和專科護理師的準時令人嘉許,艾瑪拉來一張椅子坐到我面前,面對面、兩眼平視地跟我交談。
「又見面了,」她說。「這位是阿列克絲,我的得力臂膀。」她朝專科
護理師做了個手勢,後者坐在電腦前記錄。「我知道有很多事情要討論,不過,第一件事:你覺得怎麼樣?」「還可以,把所有事情考慮在內的話,」我說。「享受我的『放假』,我想。你好嗎?」
「噢,我還行。」她停了下來—病人通常不會問醫師好不好,可是艾瑪也是同事。「這禮拜輪到我管住院, 所以你知道會是什麼樣子。」她微笑。露西和我是知道的。門診專科醫師不時要輪值住院部門工作,在已經擠得滿滿的一天裡外加幾小時的工作。
繼續寒暄一會兒後,我們自然而然地進入肺癌研究現況的討論。有兩個途徑可走,她說。傳統方法是化療,針對目標是所有快速分裂的細胞—主要是癌細胞,不過也包括骨髓、毛囊、腸道之類的細胞。艾瑪覆述了數據和選項,彷彿在對醫師上課,不過再次略過Kaplan-Meier 存活曲線的任何提示。然而,已發展出來的較新治療方法,針對目標則是癌症本身特定的分子缺陷。我聽過這種研究的傳言(這一直是癌症治療的聖杯),很驚異地知道如今進展有多大。這些治療似乎已經讓「某些」病人可以長期存活。
「你大部分檢驗的結果都送來了,」艾瑪說。「你有一個PI3K 突變,不過我們尚未明瞭它的意義。你這類病患最常見的突變,EGFR,檢查結果還沒出來。我打賭你應該會有。如果正確,你可以吃一種藥,叫做Tarceva,而不需要做化療。那項結果應該明天星期五會送來,不過你病得已經夠重,因此我訂星期一開始化療,以免EGFR 檢測是陰性的。」
我立即感到一種血緣般的親近。這正是我在神經外科的行醫方式:手上總是有A、B、C幾個計畫。
「關於化療藥物,我們主要會從carboplatin 跟cisplatin 當中選擇一種。
在若干孤立的研究中,它們兩個相比,身體對c a rbopl a t in 的耐受性較高。
c i spl a t in 可能效果較佳,但是毒性高很多,特別是對於神經的毒性,不過所有數據都很舊,而且沒有跟現代化療療程的直接比較。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對於保護自己的手以繼續開刀,不那麼在意,」我說,「我可以做
很多不同的事情。如果失去雙手,我可以從事另一行,或者不工作,或者幹什麼別的。」
她停了一下。「我這麼問你好了:開刀對你重不重要?是不是你想做的事情?」
「嗯,是重要,我幾乎花了這輩子的三分之一在準備這件事。」
「好的, 那麼我要建議我們採用c a r b opl a t in。我不認為它會改變存活率,不過它會劇烈改變你的生活品質。有沒有其他問題?」
她似乎很清楚這是該走的方向,我樂意追隨。也許,我開始讓自己相信,再度操刀是有可能的。我感覺自己輕鬆了一點。
「我可以開始抽煙了嗎?」我開玩笑。
露西笑出來,艾瑪兩眼打轉。
「不行。有沒有認真的問題?」
「Kaplan-Meier ⋯⋯」
「我們不討論那個,」她說。
我不了解她的抗拒。畢竟,我是熟悉這些統計數字的醫師。我可以自己去查⋯⋯那好,我必須那麼做。
「好吧,」我說。「我想事情都相當清楚了。明天我們會從你這兒得知
EGFR 的結果。如果陽性,就開始服用Tarceva,如果陰性,那麼星期一開始化療。」
「對。另外有件事我希望你知道:我現在是你的醫師了。有任何問題,從一般醫療到不管其他什麼問題,你都先找我們。」
又一次,我被血緣般的親近感扎到了。
「謝謝,」我說。「住院病房那裡,祝你好運了。」
她出了診間,卻在一秒鐘之後探頭進來。「你大可拒絕沒關係,不過有些肺癌基金的募款人很想見你。現在還不用回答。考慮考慮,然後告訴阿列克絲你有沒有興趣。別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情。」
我們離開時,露西說道,「她太棒了。她很適合你。不過⋯⋯」她露出笑容。「我覺得她喜歡你。」
「所以?」
「嗯,有一個研究說,當醫師有個人因素摻雜進來時,對病人的預後判斷會比較差。」
「我們的擔憂清單又多了一項,」我笑了一聲。「我想,它落在重要性最低的那個象限。」
我開始了解,跟自己的大限如此近距離地接觸,既改變了一切,也什麼都沒改變。在癌症確診以前,我知道自己有天會死,可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確診之後,我知道自己有天會死,可是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不過現在我很明白,這其實不是科學問題。死亡的事實令人不安。然而,沒有別的方式可活。
逐漸地,醫學的迷霧開始散開—至少現在我有足夠的資訊可以一頭栽入文獻。雖然數字還很模糊,有EGFR 突變似乎會增加一年的平均壽命,還有長期存活的潛力;如果沒有,意味著兩年內死亡機率為百分之八十。弄清楚我的餘生將是一個變化不斷的過程。
第二天,露西和我去一家精子銀行,保存生殖細胞以及未來選項。我們一直計畫當我住院訓練結束時要生孩子,但是現在⋯⋯癌症藥物對我的精子有未知的影響。因此,為了保留生孩子的機會,我們必須在治療開始前冷凍精子。一個年輕女子為我們一一解釋不同的付款計畫、庫存的選擇,以及擁有者的法律表格。她的桌上有許多彩色小冊子,是關於年輕癌症患者的各種社交聚會:即興表演聚會,無伴奏合唱團、自動上台演唱的晚會,等等。我嫉妒他們快樂的臉,心裡明白,在統計上,他們患的大概都是擁有高治癒率的癌症,也有合理的預期壽命。三十六歲的人只有百分之○.○○一二會得到肺癌。是的,患上癌症的所有病人都很不幸,不過有的患了癌症,有的卻患了癌症,得到後者的是真正倒了大楣。當她問我們,如果我倆有一人「萬一死去」,如何指定精子的未來—死後誰合法擁有精子—淚水滾落露西的臉頰。
「希望」這個字大約一千年前首次出現在英文裡,指的是信心和欲求的某種結合。可是我欲求的—生命,並非我有信心會發生的—死亡。那麼,當我談希望的時候,我的意思真的是「留些空間給無根據的欲求」嗎?
不是的。醫學統計不只講出數據,例如平均存活率,還有測量我們對那些數字有多少信心的工具,像是信賴水準、信賴區間、信賴界限之類的。那麼,我的意思是「留些空間給統計上不可能但是仍然有機會發生的結局—恰好高於信賴區間值百分之九十五的存活比」嗎?這就是希望嗎?我們能不能把曲線劃分為若干量化的存在感線段,從「一籌莫展」到「悲觀」到「符合現實」到「抱著希望」到「妄想」?難道數字不只是數字嗎?我們是不是總覺得每一個病人都高於平均值,於是向這種「希望」繳械投降了?
我突然想到,一旦我成了統計之一,我跟統計的關係就改變了。
住院醫師期間,我跟數不清的病人和家屬坐下來討論灰暗的預後;作為醫師,那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當病人是九十四歲,處於失智症末期,事情容易得多。可是像我這樣,三十六歲,被診斷為罹患末期癌症,真的沒有任何言語可用。醫師不給病人明確的預後,原因不只是他們無法辦到。當然,要是病人的預期遠遠超過現實,譬如說,有人期待活到一百三十歲,或者有人認為良性皮膚斑點是瀕臨死亡的跡象,那麼醫師有義務將病人的預期拉回合理的機率範疇。病人想要的並非醫師隱藏起來的科學知識,而是貨真價實的存在感,後者其實必須靠自己去追尋。過分深入數據,就像喝海水止渴。面對人生大限的焦慮,不會在統計機率裡找到療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