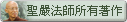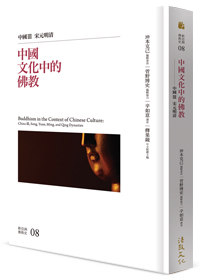商品圖片
中國文化中的佛教:中國III 宋元明清
Buddhism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China III,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作者:編輯委員:沖本克己 / 編輯協力:菅野博史 / 中文版總主編:釋果鏡
譯者:辛如意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05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新亞洲佛教史
規格:平裝 / 15x21 cm / 456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210081
ISBN:9789575986698
定價:NT$520
會員價:NT$442 (85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第五章 第三節 佛教雕刻與佛教繪畫
↑TOP
一、中國式佛像誕生
中國佛教美術不斷擺盪於「華」、「戎」之間,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如來像的衣著形式。之所以稱為「中國式佛像」或「中國化佛像形式」,原因就在於印度佛像並沒有這種衣著形式,而是中國獨自創成的式樣。其實無論佛像衣裝是何種形式皆與佛的本質無關,探討此類課題,未免略嫌細瑣,但若欲探討究竟該將佛視為何種型態樣貌,或該如何讓佛呈現某種樣貌,那麼這些問題不僅與造像者的信仰型態有關,亦關乎著社會認同問題。只要將佛塑造為穿衣裝的人像,肉體造型或衣著式樣將成為決定佛像樣貌的首要因素。
如來像的衣著形式之中,最容易引發問題的就是袈裟(大衣)穿著方式,以及袈裟中的內衣形式或穿法。袈裟穿著方式中,自印度傳來的西方式衣著有兩種,就是披覆雙肩的通肩式和露出右肩的右袒形式,兩種方式的袈裟末端皆搭於左肩。相對而言,中國式佛像在初創時期,袈裟末端是搭於左手前腕。雖然只是些微差異,卻讓衣服自前胸敞至上腹的設計成為一大特徵。此外,更廣泛採用讓袈裟中所穿的內衣自敞開胸口顯露於外的設計。內衣因種類、組合呈現多元化,但多以附屬結帶垂於胸前做為一大特徵。學者試圖將這些衣著和文獻中的僧祇支或偏衫、覆肩衣互相對照,至今眾說紛紜。總之為了避諱裸袒才以內衣方式表現,同時採取敞襟形式,這正是為了強調佛像穿著左右對領的一般漢式俗服的刻意設計。必須附帶一提,這看似衣領的部分往往不是出自同一件袈裟,右側多為其他衣著,這兩種服制在中國皆通稱為「雙領下垂式」。
若從目前僅存的作品來判斷,這種中國式佛像是在五世紀後期突然出現,前節提到的雲岡石窟第十六窟、第六窟即是先例。六世紀以後,不僅是龍門石窟等石窟造像,單尊石佛或金銅佛亦清一色採用此式,就此蔚為風潮。過程中,雲岡石窟佛像已從量感豐沛的軀體逐漸轉為垂肩纖瘦型,衣著分量卻呈反比似的愈顯厚重,恰如多層衣裾、左右對稱外擴的造形所示般,顯現抽象而具結構性的表現。坐像式佛像的衣裾尤其誇張化,繁複層疊的襞褶寬展懸垂於須彌座前,構成華麗的裳懸座。藉由充滿緊張感的概念化造形,表現佛之神祕、超然。巨大舉身光彷如包融佛身,炎炎昇騰,以蓮瓣式呈現,這種形式在印度或犍陀羅皆未曾出現;光背上填滿雲氣紋、蓮華唐草紋。這些漢化的佛像形式,最初是從改變衣著形式開始,漸從軀體表現擴展為莊嚴具設計,概括而言,就是明確朝著捨棄肉體生動實感而進行的變革。
這種變革究竟始於何時或何處、何種情況?學者對此見解不一,例如有人認為服制改革是北魏皇朝推行漢化政策中的重要環節,因此成為契機。或有認為此乃南朝佛像在民族化過程中自然發展的結果,甚至以為是涼州或隴西、長安附近一帶出現創新樣式後,流傳至其他地區發展等諸項因素。尤其在日本學界曾關注飛鳥佛式樣的起源,在此背景下引發北魏起源說、南朝起源說相爭不下的情況。前者關注的北魏服制改革,是第六代君主孝文帝(四七一—九九在位)於太和十年(四八六)正式制定以漢式衣冠做為朝服。北魏造像的特色在於皇帝結合如來形象,佛像衣裝與皇帝袞冕服近似,開領、長雙袖,胸前垂懸結帶。暫且將時間回溯至服制改革之前,一尊鐫銘為南齊年號永明元年(四八三)的中國式佛像,發現地點卻在遙遠的四川省茂縣,此佛是現存可確定年代最早的漢式服制佛像。根據銘文記載,發願者是僧侶玄嵩,出身可能是五胡十六國的西涼。位於茂縣的茂汶地區是南朝出西關的要衝,亦是南齊立國當時建造齊興寺的地點(《高僧傳》〈玄暢傳〉)。這尊石像的建造年代和發現地點皆無其他任何線索可循,必須特別審慎處理,但對中國式佛像創自北魏中央一帶之外的見解,提供引發議論之空間。
至於南朝起源說,就如南京西善橋出土的南朝墓磚畫一般,佛像似是竹林七賢的裝束,嶙峋瘦骨,受到南朝初期貴族社會流行的高士脫俗形象所影響,或許是根據漢族士大夫的官服制所創成。然而,從國都建康(南京)等南朝中心要地來看,目前尚未發現中國式佛像,仍欠缺南朝建立佛像形式的佐證。
其實將袈裟穿法精心改造成漢式俗服已是違反佛教戒律,但為何偏要如此?曾有學者關注此課題,試從三教交涉觀點來詮釋中國式佛像在五世紀後期出現的原委(岩井共二,二○○七)。隨著格義佛教時代結束,世間對佛教理解愈深,加上教團擴大、整頓戒律,導致佛教與儒、道衝突漸增,終於釀成五世紀中葉發生廢佛及夷夏論爭,固有的佛教右袒服制遭到儒家抨擊違反禮制,道家則攻訐佛教為夷狄之教,佛家服制成為夷服,飽受批判。學者認為佛教在此情況下,必須採取與儒、道價值觀的相融或妥協方式,兼具佛家最低限度的威儀,繼守穿袈裟儀規,並可配合漢地衣式習俗。然而,這必須是以佛像衣著形式來反映僧服制為前提,若能如此,所謂漢式佛像的產生,就是與西方傳來的佛教在歷經與儒、道交涉後演變成中國特有佛教的狀況,恰能維持步調一致發展。
二、崇尚「印度式」造像與靈驗像
自西元一九七○年代起,中國山東省陸續發現石佛,年代大約始於北朝晚期的東魏(五三四—五○年)至北齊(五五○—七七年)之間。佛像多成碎片,數量高達幾百件,與北宋銅錢等文物一併出土,可知北宋時期有人發心助施,將損毀佛像蒐集後奉埋於地窖。陸續發現的文物中,最受矚目的是西元一九九六年於青州龍興寺遺址窖藏出土的四百多尊石佛,佛身尚存豔彩,刻工精雕細琢。遍觀這些文物,首先發現佛像中既有以漢式衣裝、背置大型舉身光為特徵的漢式佛像,亦有薄衣貼身的西方式佛像,形形色色混雜其中。尤其後者雖屬西方式樣,卻有異於北朝前期造像,特徵為充滿寫實感的柔和面貌、量感適中的柔滑體軀,這些造像源自於印度鹿野苑的笈多式樣和南印式樣,較為接近東南亞風格,屬於新型的「印度式」佛像。
中國式佛像素有「秀骨清像」之稱,這種形式於六世紀前期形成典範,享有獨尊之位。此後卻出現風格迥異、動感洋溢的印度式佛像,這種造形孕育成形後,在北齊時代廣為流行,北齊皇權主導下營造的北響堂山石窟即是代表。新印度式佛像流行的原因,在其背景因素中,不僅包括深受中國和印度、中亞、東南亞活絡交流的影響,亦包含北齊對北魏推行激進漢化政策所造成的反動現象。造像者在此情況下,將非「漢」即「胡」的意識型態寄託於印度式佛像中,這與前文所述的後趙石虎表明反漢俗的立場或構造不謀而合。如此現象同樣發生於南朝統治下的四川地區,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的同一批石佛,亦出現兩種截然不同形式並存、競相演出豐富的創作風格。
這種造像稱為印度式佛像,但未必就是以梵土佛像為模本製成,實際上,應說更類似於中國人想像的印度佛像,在造像中大量融入印度的創作要素。在此試舉一件風格獨具的佛像為例—梁朝太清五年(五五一)的「育王像」銘石像。此像的出土地點是四川成都,從佛容蓄有濃髭、通肩式大衣的定型化衣襞、軀體構造等特徵來觀察,乍看之下是印度式造像。同款作品還發現數件,其中一件果真附有「阿育王像」銘刻。毋庸置疑的,阿育王(無憂王)正是西元前三世紀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被尊為護法聖王,其像在中土廣受崇奉。正如下節將提出說明的,阿育王像對中國的舍利信仰影響十分深遠。所謂的阿育王像是指阿育王敕命立造的佛像,當時眾人所見之像,應是兼具聖王與佛的雙重形象。這些阿育王像融合了犍陀羅後期和笈多式要素,自中國獨特的文脈中創生,實際上,在印度從未有過此類像容。
入唐後,佛像透過纖柔衣裝,栩栩如生表現了豐腴感和裊娜動態。唐代佛像堂堂示現出富於生命力的理想人體之美,成為統一新羅時期、日本奈良時期的古典美術典範。如此讓印度式佛像自六世紀後期以來形成的潮流,與帶有強烈國際風格的開放時代息脈相通,一股作氣絢爛發展,加上玄奘、義淨等求法僧,以及王玄策等人陸續自印度傳回佛教美術新知,更造成顯著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玄奘於貞觀十九年(六四五)歸朝,返抵長安之際除了攜回經典、佛舍利,亦迎回七尊佛像。請來品的詳細物件可見於《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著作,婆羅痆斯國鹿野苑的初轉法輪像、劫比他國的三道寶階降下像等作品,皆是根據與印度佛蹟有淵源的釋迦像為模本刻造而成。這與中國佛教界向天竺求取真經、希求引入中土佛教界的精神相通,不難想像,這些佛像具備了佛教發源地釋迦像應有的權威,充滿魅惑之感的印度式像容蘊涵著深遠的影響力。
然而,玄奘並非只選擇當地極受重視的知名佛像而已,在請來品目錄中,有七尊造像是以釋尊後半生事蹟為主題,分別根據時序配列而成。前段所述的請來佛像中,僅有兩尊與印度慣有的八相釋迦像相同而已,其他如摩揭陀國靈鷲山說法像、憍賞彌國優填王思慕像、那揭羅曷龍窟影像等題材,在印度皆屬罕見題材,在中國才格外備受重視。靈鷲山或那揭羅曷的佛影窟,因有《法華經》和《觀佛三昧海經》描述當地為如來常住說法之處,故而廣為人知。優填王思慕像是摹寫釋尊在世真容的最早釋迦像,釋尊曾親囑滅度後可做為度化眾生之用,堪稱是集結特殊信仰的產物。這些佛像超越了釋迦在佛傳中的定位,具有更普遍性、屬於永久常住的釋迦如來性格。自南北朝初期以來,這些尊像之所以在中國漸受重視的原因,必然是出於與釋尊時空相隔遙遠所產生的渴切之念。中國信眾對這些如同禮敬釋迦如來真身的造像,必然期待是能摹擬釋尊形貌的印度式佛容,玄奘正是為此才特意選擇此類造像。
此外,靈驗像可示現各種奇瑞之兆,故而格外深受崇信,其中又以大肆宣傳源自印度的緣起傳說型佛像數量居冠,例如荊州(湖北省江陵)長沙寺的阿育王像就是代表之一。根據《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的靈驗傳說記載,此像出現於東晉時期的荊州,一名來自罽賓(喀什米爾)的僧侶解讀這尊佛像的光背梵文後,認定出自阿育王所造,證言此像在天竺已佚失,如今遠降生於華夏。此後這尊佛像會出現放光、流汗、流淚等異象,甚至繞龕行道,某次步出寺門,還被起疑的巡邏揮刀砍擊。佛像遇到火災會自行變輕,任人抬走倖免於難,遇到乾旱向其求雨,必能應驗。每逢佛像放光,便會出現佛教大興或帝王行幸來寺禮佛等祥瑞之事,佛像若流汗或垂淚,則發生廢佛或戰亂等危及佛教、佛身之禍,或是不幸遭遇皇帝賓天、暴政者崛起、皇朝將亡等厄兆。誠如此像之例,中國佛教靈驗記中出現不少描述與俗權有關的題材,對為政者而言,靈驗像亦是定奪是非的天意代言者。藉由讖緯之說(以陰陽五行為基礎判斷吉凶)的取決方式,為政者在宣揚俗權護持佛教之餘,更透過聲稱佛像來自佛教發源地印度的方式,宣示佛像及其所屬寺院、教團的正統性,同時賦予一種權威。
這類佛像在靈驗傳說烘托之下,被稱為瑞像或靈像,隨著信仰者愈多,逐漸被仿製成摹刻像,或將其獨具特質的像容繪圖流傳於世。這是基於信眾深信摹刻像與原像具有同樣靈力,安奉威信十足的靈驗像,祈求保全或擴張寺院、宗派之勢。最能以充分資料說明這種情況的例子,就是北宋時期的木雕像,亦即日本京都清涼寺的本尊釋迦如來像。此像為優填王思慕像,素有栴檀瑞像之稱,被視為佛之真身,安奉於北宋太宗宮內。日本東大寺僧奝然(九三八—一○一六)在台州(浙江省)委人摹刻後,於西元九八六年迎請新像渡日,此佛具備與真身佛相應的構造,胎內納置絹製的五臟六腑。鎌倉時期以後,摹刻像的製作數量愈顯增加。如前所述,此像既是釋尊在世的釋迦本尊,亦是受如來託囑,傳歷於印、中、日三國,其權威之高,恐無任何佛像可與之比擬。奝然身為南都僧侶,迎請此像歸國的意圖,應是對延曆寺大舉擴張勢力懷有對抗意識。另有一項原因,就是鎌倉時期盛行的佛像摹刻,被視為南都律宗振興行動的重要環節。
此外,有些造像在今日雖屬來歷不明,被視為尋常佛像,但相信其中必有一些曾是身分殊異、擁有各自獨特信仰的靈驗像。
三、寺院壁畫與變相圖
就形式及功能來看,佛教繪畫美術分為兩種,就是做為禮敬、儀禮之用的本尊畫像,以及在寺堂或石窟壁畫中可見的、做為裝飾或賦予宗教空間某種意義、透過嚴飾後的作品。繪畫比雕刻更為脆弱易失,除了敦煌石窟壁畫和藏經洞內發現的紙本或絹本畫之外,回溯至北宋以前的作品已是寥寥無幾。然而從畫史或畫論、寺誌等史料來看,仍可一窺中國佛教衍生出豐富的繪畫藝術世界。張彥遠在九世紀前期撰述的《歷代名畫記》卷三之中,記載當時長安、洛陽寺觀內的壁畫作品,留下繪畫主題和畫家姓名等珍貴紀錄。例如長安光宅寺之項:「東菩薩院內,北壁東西偏,尉遲畫降魔等變。殿內吳生、楊廷光畫,又尹琳畫西方變。」尉遲是出身於西域和闐的尉遲乙僧,吳生是吳道玄,楊廷光、尹琳皆是活躍於七世紀後期至八世紀前期的畫家。所謂的畫題〈西方變〉,例如敦煌莫高窟第二百二十窟南壁的作品中,根據《觀無量壽經》或《阿彌陀經》等經典講述的西方極樂淨土境相,施以絢彩描繪,藉由大幅畫面展現,以諸聖眾簇擁的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菩薩為主題,另有化生童子嬉遊、奏樂天等列席而坐的蓮池露台、金碧輝煌的寶樓寶樹、旋舞虛空的樂器彩雲等。〈降魔等變〉則是描繪魔眾攻來、釋尊手結降魔觸地印,以佛傳中降魔成道的情景為代表的各種神變故事繪畫。
所謂的「變」,亦稱變相(圖)、經變(圖),是指根據經文敘事或敘景內容為基礎的造形表現。例如第二節已介紹的大足寶頂山石刻般的雕刻形式,或是卷子、掛軸皆屬此類,主要型態仍是寺院或石窟的大幅壁畫。《歷代名畫記》提到的繪畫主題,尚有維摩變、涅槃變、彌勒下生變、華嚴變、十輪變、金剛變、金光明經變、本行經變、地獄變等,從敦煌石窟可發現許多唐代壁畫的作例,就此來看,可知中央都市寺院盛行描繪的變相圖,亦廣泛流傳至邊域。
原本「變」的字義即有幾種說法,根據江戶初期的真言僧運敞(一六一四—九三)所述,其義為:「變動也。圖畫不動,而畫極樂或地獄種種動相,故云變相也」(《寂照堂谷響續集》卷一)。佛教的視覺印象中,最具動勢、動感的主題就是來迎或示現、放光這種藉由佛菩薩行為引發的諸多奇象,對一般信徒而言,這才是深具臨場感、亟欲親睹為快的。構圖複雜、主題千變萬化、色彩富麗揮灑,變相圖描繪出佛國淨土與超俗的奇蹟場面,正為了滿足此需求。就此意味來說,這些大幅畫面的變相圖,不僅為了嚴飾寺院空間,有時更配合解說神變故事繪畫的說唱曲藝,教化民眾之餘,亦提供一種慰藉、娛樂。
比較耐人尋味的是敦煌變相圖的描繪內容,與其說是經典,倒不如說更接近稱為變文或說經話本所採用的文辭方式。這些話本在敦煌藏經洞所發現的敦煌文書中大量出現,是一種藉由韻文、散文夾雜的平易用語講說艱澀經文要旨的劇本,推定摹寫年代應比變相圖遺存年代更晚,約在晚唐至五代時期。換言之,變相圖與變文是在互為影響中,漸朝佛教大眾化而蓬勃發展。
說起寺院壁畫的繪畫名家,自古有東晉顧愷之在建康瓦官寺繪作維摩詰像。南北朝梁武帝(五○二—四九在位)時期的御用畫家張僧繇,亦是箇中翹楚。梁武帝以虔心奉佛而知名,實為歷代帝王所僅見,張僧繇就在武帝陸續興建的大伽藍中積極創作壁畫。張僧繇曾以畫龍點睛的故事而名噪一時,據說作品素以描線簡潔、精準掌握人物樣態為特色,但在南朝覆滅的動盪中,其作品面臨與寺院共存亡的命運,早已湮沒於世間。相傳唐代首屈一指、享有畫聖之譽的吳道玄,正是張僧繇再世。唐玄宗(七一二—五六在位)時期,吳道玄在長安、洛陽各寺觀中繪壁畫,長達三百餘壁。《太平廣記》卷二十二中有一則著名軼聞,描述吳道玄在當地景公寺完成地獄變相圖後,長安百姓望見這幅作品之時,紛紛被那血淋淋慘象嚇得魂不附體,深怕造業而改過向善,市集中從此漸無人敢賣魚販肉,可知當時的寺院壁畫已開放供人觀賞,廣泛享受其趣。
現存的寺院壁畫幾乎是十世紀以後的作品,其中尤其以山西省遺跡最為豐富。五台山佛光寺現存一座木造大殿,重建於九世紀中期,至於建造時間遠溯至唐代的毘沙門天像、佛說法壁畫則殘存無幾。此外,以應縣木塔而馳名於世的佛宮寺釋迦塔,創建於遼朝清寧二年(一○五六),塔內仍保存跨越遼、金二朝的四天王像。位於山西省南部高平縣開化寺的大雄寶殿壁畫,是北宋郭發於紹聖三年(一○九六—九七)費時兩年完成,堂內三面壁上有西方淨土變、釋迦說法圖、本生說話圖,從細膩描繪的本生故事中,可知宋代世俗生活百態。位於五台山麓的繁峙巖山寺是金代所建的敕願寺,現存有宮廷畫家王逵於西元一一六七年繪作的壁畫。這幅大壁畫以端整精緻的北宋筆法,繪出鬼子母變相與本行經變相,氣勢雄渾,充滿緊張感,足以讓觀者為之屏息。
四、日本迎請的佛像與佛畫
若說起中國佛教美術的現存地區,不可輕忘的就是日本。自奈良時期以來,日本外交使節或求法僧、來朝僧、貿易商人等在迎歸經典之際,大量攜回了圖像、佛像、佛畫、佛具等佛教美術品項,流傳於寺院或顯貴之家。在佛像雕刻方面的代表作品中,包括:前述的清涼寺釋迦如來像,以及初唐製作的法隆寺所藏九面觀音像、據傳由空海請歸的金剛峰寺諸尊佛龕(枕本尊)、中唐製作的東寺所藏兜跋毘沙門天像、晚唐製作的東寺所藏五大虛空藏菩薩像、南宋製作的泉涌寺所藏觀音菩薩像(通稱楊貴妃觀音)等。佛像或繪像方面,則如:唐貞元二十一年(永貞元年,八○五)製作的東寺〈真言五祖像〉、圓珍於西元八五五年獲授的〈五部心觀〉、奝然迎請栴檀瑞像之際一同攜回北宋製作的清涼寺〈十六羅漢圖〉、南宋製作的仁和寺孔雀明王像、知恩院〈阿彌陀淨土圖〉、奈良博物館所藏的陸信忠筆本〈佛涅槃圖〉和〈十王圖〉等,其數浩繁不勝枚舉。
試想中國傳世之作在當地已碩果僅存,若說幸而當時能將這些作品迎請渡日才得以傳存至今,如此說法一點也不為過。迎請者除了篤信佛教、通達教理且具備審美觀之外,更重要的是請歸的意志堅決,經由篩選、摹製之後,將這些藝品載航歸國,其中恐怕有許多在中國當時亦屬於一流之作。光憑中國現有的僅存作品來看,難免出現遺缺或過小評價,但東傳日本的作品恰可彌補其憾,就此意味來看,這些作品極具價值,尤其在密教繪畫或唐、宋木雕像方面更為明顯,姑且試舉兩、三件作品為例。
白描圖像〈五部心觀〉是由日僧圓珍(八一四—九一)迎請歸國,此後為園城寺所藏。根據圓珍自撰的題跋,可知此圖是圓珍居留長安之際,由其師青龍寺法全親自授贈。所謂五部,是指構成金剛界曼荼羅的如來部、金剛部、寶部、蓮花部、羯磨部,以圖示法表現修行者依五部諸尊入三摩地的觀修法,故而取名為心觀。題跋之前,大幅描繪一名僧人以跪坐之姿,雙手捧持柄香爐,可知卷末所繪是善無畏之像,更顯示此圖是出自善無畏(六三七—七三五)法系。換言之,空海(七七四—八三五)繼承的金剛界圖像是金剛智(六七一—七四一)法系,相對來看,圓珍則繼承正統善無畏系的金剛界圖像。〈五部心觀〉以纖細、蒼勁的線條精細描繪諸尊和印契,作品饒富生趣及高尚之感,唐代中央畫壇之作在今日已逸,卻可從〈五部心觀〉充分窺知精髓。
東寺觀智院的五大虛空藏菩薩像,是入唐僧惠運(七九八—八六九)或其弟子三修(八二九—九○○)於九世紀前期迎歸日本,這五尊木雕佛像傳達了晚唐密教信仰的意象,堪稱是現存唯一例證。據學者推測,佛像的製作地點應在歸返日本的出航地明州(浙江省寧波),像材選用中國櫻木,採一木造雕法,就是從頭軀至蓮座皆以同材一體雕成,不施內刳處理,頭髮或眼瞳、胸飾等以捏塑方式另行製作,由上述技法可知有別於日式木雕像的手法。明州是江南國際貿易港,海運發展繁盛,亦是佛教文化發信地。這五尊虛空藏菩薩的造像,在對於了解唐代明州造像發展趨勢上,提供極為寶貴的訊息。此後至宋、元時期,日本與明州之間的人文、物資往來愈發活絡,其中,以陸信忠為代表的寧波佛畫師之作在日本廣為傳世,如此盛況正反映了當時趨勢。
中國佛教美術不斷擺盪於「華」、「戎」之間,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如來像的衣著形式。之所以稱為「中國式佛像」或「中國化佛像形式」,原因就在於印度佛像並沒有這種衣著形式,而是中國獨自創成的式樣。其實無論佛像衣裝是何種形式皆與佛的本質無關,探討此類課題,未免略嫌細瑣,但若欲探討究竟該將佛視為何種型態樣貌,或該如何讓佛呈現某種樣貌,那麼這些問題不僅與造像者的信仰型態有關,亦關乎著社會認同問題。只要將佛塑造為穿衣裝的人像,肉體造型或衣著式樣將成為決定佛像樣貌的首要因素。
如來像的衣著形式之中,最容易引發問題的就是袈裟(大衣)穿著方式,以及袈裟中的內衣形式或穿法。袈裟穿著方式中,自印度傳來的西方式衣著有兩種,就是披覆雙肩的通肩式和露出右肩的右袒形式,兩種方式的袈裟末端皆搭於左肩。相對而言,中國式佛像在初創時期,袈裟末端是搭於左手前腕。雖然只是些微差異,卻讓衣服自前胸敞至上腹的設計成為一大特徵。此外,更廣泛採用讓袈裟中所穿的內衣自敞開胸口顯露於外的設計。內衣因種類、組合呈現多元化,但多以附屬結帶垂於胸前做為一大特徵。學者試圖將這些衣著和文獻中的僧祇支或偏衫、覆肩衣互相對照,至今眾說紛紜。總之為了避諱裸袒才以內衣方式表現,同時採取敞襟形式,這正是為了強調佛像穿著左右對領的一般漢式俗服的刻意設計。必須附帶一提,這看似衣領的部分往往不是出自同一件袈裟,右側多為其他衣著,這兩種服制在中國皆通稱為「雙領下垂式」。
若從目前僅存的作品來判斷,這種中國式佛像是在五世紀後期突然出現,前節提到的雲岡石窟第十六窟、第六窟即是先例。六世紀以後,不僅是龍門石窟等石窟造像,單尊石佛或金銅佛亦清一色採用此式,就此蔚為風潮。過程中,雲岡石窟佛像已從量感豐沛的軀體逐漸轉為垂肩纖瘦型,衣著分量卻呈反比似的愈顯厚重,恰如多層衣裾、左右對稱外擴的造形所示般,顯現抽象而具結構性的表現。坐像式佛像的衣裾尤其誇張化,繁複層疊的襞褶寬展懸垂於須彌座前,構成華麗的裳懸座。藉由充滿緊張感的概念化造形,表現佛之神祕、超然。巨大舉身光彷如包融佛身,炎炎昇騰,以蓮瓣式呈現,這種形式在印度或犍陀羅皆未曾出現;光背上填滿雲氣紋、蓮華唐草紋。這些漢化的佛像形式,最初是從改變衣著形式開始,漸從軀體表現擴展為莊嚴具設計,概括而言,就是明確朝著捨棄肉體生動實感而進行的變革。
這種變革究竟始於何時或何處、何種情況?學者對此見解不一,例如有人認為服制改革是北魏皇朝推行漢化政策中的重要環節,因此成為契機。或有認為此乃南朝佛像在民族化過程中自然發展的結果,甚至以為是涼州或隴西、長安附近一帶出現創新樣式後,流傳至其他地區發展等諸項因素。尤其在日本學界曾關注飛鳥佛式樣的起源,在此背景下引發北魏起源說、南朝起源說相爭不下的情況。前者關注的北魏服制改革,是第六代君主孝文帝(四七一—九九在位)於太和十年(四八六)正式制定以漢式衣冠做為朝服。北魏造像的特色在於皇帝結合如來形象,佛像衣裝與皇帝袞冕服近似,開領、長雙袖,胸前垂懸結帶。暫且將時間回溯至服制改革之前,一尊鐫銘為南齊年號永明元年(四八三)的中國式佛像,發現地點卻在遙遠的四川省茂縣,此佛是現存可確定年代最早的漢式服制佛像。根據銘文記載,發願者是僧侶玄嵩,出身可能是五胡十六國的西涼。位於茂縣的茂汶地區是南朝出西關的要衝,亦是南齊立國當時建造齊興寺的地點(《高僧傳》〈玄暢傳〉)。這尊石像的建造年代和發現地點皆無其他任何線索可循,必須特別審慎處理,但對中國式佛像創自北魏中央一帶之外的見解,提供引發議論之空間。
至於南朝起源說,就如南京西善橋出土的南朝墓磚畫一般,佛像似是竹林七賢的裝束,嶙峋瘦骨,受到南朝初期貴族社會流行的高士脫俗形象所影響,或許是根據漢族士大夫的官服制所創成。然而,從國都建康(南京)等南朝中心要地來看,目前尚未發現中國式佛像,仍欠缺南朝建立佛像形式的佐證。
其實將袈裟穿法精心改造成漢式俗服已是違反佛教戒律,但為何偏要如此?曾有學者關注此課題,試從三教交涉觀點來詮釋中國式佛像在五世紀後期出現的原委(岩井共二,二○○七)。隨著格義佛教時代結束,世間對佛教理解愈深,加上教團擴大、整頓戒律,導致佛教與儒、道衝突漸增,終於釀成五世紀中葉發生廢佛及夷夏論爭,固有的佛教右袒服制遭到儒家抨擊違反禮制,道家則攻訐佛教為夷狄之教,佛家服制成為夷服,飽受批判。學者認為佛教在此情況下,必須採取與儒、道價值觀的相融或妥協方式,兼具佛家最低限度的威儀,繼守穿袈裟儀規,並可配合漢地衣式習俗。然而,這必須是以佛像衣著形式來反映僧服制為前提,若能如此,所謂漢式佛像的產生,就是與西方傳來的佛教在歷經與儒、道交涉後演變成中國特有佛教的狀況,恰能維持步調一致發展。
二、崇尚「印度式」造像與靈驗像
自西元一九七○年代起,中國山東省陸續發現石佛,年代大約始於北朝晚期的東魏(五三四—五○年)至北齊(五五○—七七年)之間。佛像多成碎片,數量高達幾百件,與北宋銅錢等文物一併出土,可知北宋時期有人發心助施,將損毀佛像蒐集後奉埋於地窖。陸續發現的文物中,最受矚目的是西元一九九六年於青州龍興寺遺址窖藏出土的四百多尊石佛,佛身尚存豔彩,刻工精雕細琢。遍觀這些文物,首先發現佛像中既有以漢式衣裝、背置大型舉身光為特徵的漢式佛像,亦有薄衣貼身的西方式佛像,形形色色混雜其中。尤其後者雖屬西方式樣,卻有異於北朝前期造像,特徵為充滿寫實感的柔和面貌、量感適中的柔滑體軀,這些造像源自於印度鹿野苑的笈多式樣和南印式樣,較為接近東南亞風格,屬於新型的「印度式」佛像。
中國式佛像素有「秀骨清像」之稱,這種形式於六世紀前期形成典範,享有獨尊之位。此後卻出現風格迥異、動感洋溢的印度式佛像,這種造形孕育成形後,在北齊時代廣為流行,北齊皇權主導下營造的北響堂山石窟即是代表。新印度式佛像流行的原因,在其背景因素中,不僅包括深受中國和印度、中亞、東南亞活絡交流的影響,亦包含北齊對北魏推行激進漢化政策所造成的反動現象。造像者在此情況下,將非「漢」即「胡」的意識型態寄託於印度式佛像中,這與前文所述的後趙石虎表明反漢俗的立場或構造不謀而合。如此現象同樣發生於南朝統治下的四川地區,成都萬佛寺遺址出土的同一批石佛,亦出現兩種截然不同形式並存、競相演出豐富的創作風格。
這種造像稱為印度式佛像,但未必就是以梵土佛像為模本製成,實際上,應說更類似於中國人想像的印度佛像,在造像中大量融入印度的創作要素。在此試舉一件風格獨具的佛像為例—梁朝太清五年(五五一)的「育王像」銘石像。此像的出土地點是四川成都,從佛容蓄有濃髭、通肩式大衣的定型化衣襞、軀體構造等特徵來觀察,乍看之下是印度式造像。同款作品還發現數件,其中一件果真附有「阿育王像」銘刻。毋庸置疑的,阿育王(無憂王)正是西元前三世紀度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被尊為護法聖王,其像在中土廣受崇奉。正如下節將提出說明的,阿育王像對中國的舍利信仰影響十分深遠。所謂的阿育王像是指阿育王敕命立造的佛像,當時眾人所見之像,應是兼具聖王與佛的雙重形象。這些阿育王像融合了犍陀羅後期和笈多式要素,自中國獨特的文脈中創生,實際上,在印度從未有過此類像容。
入唐後,佛像透過纖柔衣裝,栩栩如生表現了豐腴感和裊娜動態。唐代佛像堂堂示現出富於生命力的理想人體之美,成為統一新羅時期、日本奈良時期的古典美術典範。如此讓印度式佛像自六世紀後期以來形成的潮流,與帶有強烈國際風格的開放時代息脈相通,一股作氣絢爛發展,加上玄奘、義淨等求法僧,以及王玄策等人陸續自印度傳回佛教美術新知,更造成顯著影響。其中最重要的是玄奘於貞觀十九年(六四五)歸朝,返抵長安之際除了攜回經典、佛舍利,亦迎回七尊佛像。請來品的詳細物件可見於《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等著作,婆羅痆斯國鹿野苑的初轉法輪像、劫比他國的三道寶階降下像等作品,皆是根據與印度佛蹟有淵源的釋迦像為模本刻造而成。這與中國佛教界向天竺求取真經、希求引入中土佛教界的精神相通,不難想像,這些佛像具備了佛教發源地釋迦像應有的權威,充滿魅惑之感的印度式像容蘊涵著深遠的影響力。
然而,玄奘並非只選擇當地極受重視的知名佛像而已,在請來品目錄中,有七尊造像是以釋尊後半生事蹟為主題,分別根據時序配列而成。前段所述的請來佛像中,僅有兩尊與印度慣有的八相釋迦像相同而已,其他如摩揭陀國靈鷲山說法像、憍賞彌國優填王思慕像、那揭羅曷龍窟影像等題材,在印度皆屬罕見題材,在中國才格外備受重視。靈鷲山或那揭羅曷的佛影窟,因有《法華經》和《觀佛三昧海經》描述當地為如來常住說法之處,故而廣為人知。優填王思慕像是摹寫釋尊在世真容的最早釋迦像,釋尊曾親囑滅度後可做為度化眾生之用,堪稱是集結特殊信仰的產物。這些佛像超越了釋迦在佛傳中的定位,具有更普遍性、屬於永久常住的釋迦如來性格。自南北朝初期以來,這些尊像之所以在中國漸受重視的原因,必然是出於與釋尊時空相隔遙遠所產生的渴切之念。中國信眾對這些如同禮敬釋迦如來真身的造像,必然期待是能摹擬釋尊形貌的印度式佛容,玄奘正是為此才特意選擇此類造像。
此外,靈驗像可示現各種奇瑞之兆,故而格外深受崇信,其中又以大肆宣傳源自印度的緣起傳說型佛像數量居冠,例如荊州(湖北省江陵)長沙寺的阿育王像就是代表之一。根據《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中的靈驗傳說記載,此像出現於東晉時期的荊州,一名來自罽賓(喀什米爾)的僧侶解讀這尊佛像的光背梵文後,認定出自阿育王所造,證言此像在天竺已佚失,如今遠降生於華夏。此後這尊佛像會出現放光、流汗、流淚等異象,甚至繞龕行道,某次步出寺門,還被起疑的巡邏揮刀砍擊。佛像遇到火災會自行變輕,任人抬走倖免於難,遇到乾旱向其求雨,必能應驗。每逢佛像放光,便會出現佛教大興或帝王行幸來寺禮佛等祥瑞之事,佛像若流汗或垂淚,則發生廢佛或戰亂等危及佛教、佛身之禍,或是不幸遭遇皇帝賓天、暴政者崛起、皇朝將亡等厄兆。誠如此像之例,中國佛教靈驗記中出現不少描述與俗權有關的題材,對為政者而言,靈驗像亦是定奪是非的天意代言者。藉由讖緯之說(以陰陽五行為基礎判斷吉凶)的取決方式,為政者在宣揚俗權護持佛教之餘,更透過聲稱佛像來自佛教發源地印度的方式,宣示佛像及其所屬寺院、教團的正統性,同時賦予一種權威。
這類佛像在靈驗傳說烘托之下,被稱為瑞像或靈像,隨著信仰者愈多,逐漸被仿製成摹刻像,或將其獨具特質的像容繪圖流傳於世。這是基於信眾深信摹刻像與原像具有同樣靈力,安奉威信十足的靈驗像,祈求保全或擴張寺院、宗派之勢。最能以充分資料說明這種情況的例子,就是北宋時期的木雕像,亦即日本京都清涼寺的本尊釋迦如來像。此像為優填王思慕像,素有栴檀瑞像之稱,被視為佛之真身,安奉於北宋太宗宮內。日本東大寺僧奝然(九三八—一○一六)在台州(浙江省)委人摹刻後,於西元九八六年迎請新像渡日,此佛具備與真身佛相應的構造,胎內納置絹製的五臟六腑。鎌倉時期以後,摹刻像的製作數量愈顯增加。如前所述,此像既是釋尊在世的釋迦本尊,亦是受如來託囑,傳歷於印、中、日三國,其權威之高,恐無任何佛像可與之比擬。奝然身為南都僧侶,迎請此像歸國的意圖,應是對延曆寺大舉擴張勢力懷有對抗意識。另有一項原因,就是鎌倉時期盛行的佛像摹刻,被視為南都律宗振興行動的重要環節。
此外,有些造像在今日雖屬來歷不明,被視為尋常佛像,但相信其中必有一些曾是身分殊異、擁有各自獨特信仰的靈驗像。
三、寺院壁畫與變相圖
就形式及功能來看,佛教繪畫美術分為兩種,就是做為禮敬、儀禮之用的本尊畫像,以及在寺堂或石窟壁畫中可見的、做為裝飾或賦予宗教空間某種意義、透過嚴飾後的作品。繪畫比雕刻更為脆弱易失,除了敦煌石窟壁畫和藏經洞內發現的紙本或絹本畫之外,回溯至北宋以前的作品已是寥寥無幾。然而從畫史或畫論、寺誌等史料來看,仍可一窺中國佛教衍生出豐富的繪畫藝術世界。張彥遠在九世紀前期撰述的《歷代名畫記》卷三之中,記載當時長安、洛陽寺觀內的壁畫作品,留下繪畫主題和畫家姓名等珍貴紀錄。例如長安光宅寺之項:「東菩薩院內,北壁東西偏,尉遲畫降魔等變。殿內吳生、楊廷光畫,又尹琳畫西方變。」尉遲是出身於西域和闐的尉遲乙僧,吳生是吳道玄,楊廷光、尹琳皆是活躍於七世紀後期至八世紀前期的畫家。所謂的畫題〈西方變〉,例如敦煌莫高窟第二百二十窟南壁的作品中,根據《觀無量壽經》或《阿彌陀經》等經典講述的西方極樂淨土境相,施以絢彩描繪,藉由大幅畫面展現,以諸聖眾簇擁的阿彌陀佛、觀音、勢至菩薩為主題,另有化生童子嬉遊、奏樂天等列席而坐的蓮池露台、金碧輝煌的寶樓寶樹、旋舞虛空的樂器彩雲等。〈降魔等變〉則是描繪魔眾攻來、釋尊手結降魔觸地印,以佛傳中降魔成道的情景為代表的各種神變故事繪畫。
所謂的「變」,亦稱變相(圖)、經變(圖),是指根據經文敘事或敘景內容為基礎的造形表現。例如第二節已介紹的大足寶頂山石刻般的雕刻形式,或是卷子、掛軸皆屬此類,主要型態仍是寺院或石窟的大幅壁畫。《歷代名畫記》提到的繪畫主題,尚有維摩變、涅槃變、彌勒下生變、華嚴變、十輪變、金剛變、金光明經變、本行經變、地獄變等,從敦煌石窟可發現許多唐代壁畫的作例,就此來看,可知中央都市寺院盛行描繪的變相圖,亦廣泛流傳至邊域。
原本「變」的字義即有幾種說法,根據江戶初期的真言僧運敞(一六一四—九三)所述,其義為:「變動也。圖畫不動,而畫極樂或地獄種種動相,故云變相也」(《寂照堂谷響續集》卷一)。佛教的視覺印象中,最具動勢、動感的主題就是來迎或示現、放光這種藉由佛菩薩行為引發的諸多奇象,對一般信徒而言,這才是深具臨場感、亟欲親睹為快的。構圖複雜、主題千變萬化、色彩富麗揮灑,變相圖描繪出佛國淨土與超俗的奇蹟場面,正為了滿足此需求。就此意味來說,這些大幅畫面的變相圖,不僅為了嚴飾寺院空間,有時更配合解說神變故事繪畫的說唱曲藝,教化民眾之餘,亦提供一種慰藉、娛樂。
比較耐人尋味的是敦煌變相圖的描繪內容,與其說是經典,倒不如說更接近稱為變文或說經話本所採用的文辭方式。這些話本在敦煌藏經洞所發現的敦煌文書中大量出現,是一種藉由韻文、散文夾雜的平易用語講說艱澀經文要旨的劇本,推定摹寫年代應比變相圖遺存年代更晚,約在晚唐至五代時期。換言之,變相圖與變文是在互為影響中,漸朝佛教大眾化而蓬勃發展。
說起寺院壁畫的繪畫名家,自古有東晉顧愷之在建康瓦官寺繪作維摩詰像。南北朝梁武帝(五○二—四九在位)時期的御用畫家張僧繇,亦是箇中翹楚。梁武帝以虔心奉佛而知名,實為歷代帝王所僅見,張僧繇就在武帝陸續興建的大伽藍中積極創作壁畫。張僧繇曾以畫龍點睛的故事而名噪一時,據說作品素以描線簡潔、精準掌握人物樣態為特色,但在南朝覆滅的動盪中,其作品面臨與寺院共存亡的命運,早已湮沒於世間。相傳唐代首屈一指、享有畫聖之譽的吳道玄,正是張僧繇再世。唐玄宗(七一二—五六在位)時期,吳道玄在長安、洛陽各寺觀中繪壁畫,長達三百餘壁。《太平廣記》卷二十二中有一則著名軼聞,描述吳道玄在當地景公寺完成地獄變相圖後,長安百姓望見這幅作品之時,紛紛被那血淋淋慘象嚇得魂不附體,深怕造業而改過向善,市集中從此漸無人敢賣魚販肉,可知當時的寺院壁畫已開放供人觀賞,廣泛享受其趣。
現存的寺院壁畫幾乎是十世紀以後的作品,其中尤其以山西省遺跡最為豐富。五台山佛光寺現存一座木造大殿,重建於九世紀中期,至於建造時間遠溯至唐代的毘沙門天像、佛說法壁畫則殘存無幾。此外,以應縣木塔而馳名於世的佛宮寺釋迦塔,創建於遼朝清寧二年(一○五六),塔內仍保存跨越遼、金二朝的四天王像。位於山西省南部高平縣開化寺的大雄寶殿壁畫,是北宋郭發於紹聖三年(一○九六—九七)費時兩年完成,堂內三面壁上有西方淨土變、釋迦說法圖、本生說話圖,從細膩描繪的本生故事中,可知宋代世俗生活百態。位於五台山麓的繁峙巖山寺是金代所建的敕願寺,現存有宮廷畫家王逵於西元一一六七年繪作的壁畫。這幅大壁畫以端整精緻的北宋筆法,繪出鬼子母變相與本行經變相,氣勢雄渾,充滿緊張感,足以讓觀者為之屏息。
四、日本迎請的佛像與佛畫
若說起中國佛教美術的現存地區,不可輕忘的就是日本。自奈良時期以來,日本外交使節或求法僧、來朝僧、貿易商人等在迎歸經典之際,大量攜回了圖像、佛像、佛畫、佛具等佛教美術品項,流傳於寺院或顯貴之家。在佛像雕刻方面的代表作品中,包括:前述的清涼寺釋迦如來像,以及初唐製作的法隆寺所藏九面觀音像、據傳由空海請歸的金剛峰寺諸尊佛龕(枕本尊)、中唐製作的東寺所藏兜跋毘沙門天像、晚唐製作的東寺所藏五大虛空藏菩薩像、南宋製作的泉涌寺所藏觀音菩薩像(通稱楊貴妃觀音)等。佛像或繪像方面,則如:唐貞元二十一年(永貞元年,八○五)製作的東寺〈真言五祖像〉、圓珍於西元八五五年獲授的〈五部心觀〉、奝然迎請栴檀瑞像之際一同攜回北宋製作的清涼寺〈十六羅漢圖〉、南宋製作的仁和寺孔雀明王像、知恩院〈阿彌陀淨土圖〉、奈良博物館所藏的陸信忠筆本〈佛涅槃圖〉和〈十王圖〉等,其數浩繁不勝枚舉。
試想中國傳世之作在當地已碩果僅存,若說幸而當時能將這些作品迎請渡日才得以傳存至今,如此說法一點也不為過。迎請者除了篤信佛教、通達教理且具備審美觀之外,更重要的是請歸的意志堅決,經由篩選、摹製之後,將這些藝品載航歸國,其中恐怕有許多在中國當時亦屬於一流之作。光憑中國現有的僅存作品來看,難免出現遺缺或過小評價,但東傳日本的作品恰可彌補其憾,就此意味來看,這些作品極具價值,尤其在密教繪畫或唐、宋木雕像方面更為明顯,姑且試舉兩、三件作品為例。
白描圖像〈五部心觀〉是由日僧圓珍(八一四—九一)迎請歸國,此後為園城寺所藏。根據圓珍自撰的題跋,可知此圖是圓珍居留長安之際,由其師青龍寺法全親自授贈。所謂五部,是指構成金剛界曼荼羅的如來部、金剛部、寶部、蓮花部、羯磨部,以圖示法表現修行者依五部諸尊入三摩地的觀修法,故而取名為心觀。題跋之前,大幅描繪一名僧人以跪坐之姿,雙手捧持柄香爐,可知卷末所繪是善無畏之像,更顯示此圖是出自善無畏(六三七—七三五)法系。換言之,空海(七七四—八三五)繼承的金剛界圖像是金剛智(六七一—七四一)法系,相對來看,圓珍則繼承正統善無畏系的金剛界圖像。〈五部心觀〉以纖細、蒼勁的線條精細描繪諸尊和印契,作品饒富生趣及高尚之感,唐代中央畫壇之作在今日已逸,卻可從〈五部心觀〉充分窺知精髓。
東寺觀智院的五大虛空藏菩薩像,是入唐僧惠運(七九八—八六九)或其弟子三修(八二九—九○○)於九世紀前期迎歸日本,這五尊木雕佛像傳達了晚唐密教信仰的意象,堪稱是現存唯一例證。據學者推測,佛像的製作地點應在歸返日本的出航地明州(浙江省寧波),像材選用中國櫻木,採一木造雕法,就是從頭軀至蓮座皆以同材一體雕成,不施內刳處理,頭髮或眼瞳、胸飾等以捏塑方式另行製作,由上述技法可知有別於日式木雕像的手法。明州是江南國際貿易港,海運發展繁盛,亦是佛教文化發信地。這五尊虛空藏菩薩的造像,在對於了解唐代明州造像發展趨勢上,提供極為寶貴的訊息。此後至宋、元時期,日本與明州之間的人文、物資往來愈發活絡,其中,以陸信忠為代表的寧波佛畫師之作在日本廣為傳世,如此盛況正反映了當時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