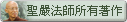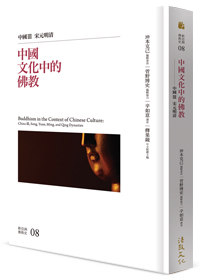商品圖片
中國文化中的佛教:中國III 宋元明清
Buddhism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Culture:China III,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作者:編輯委員:沖本克己 / 編輯協力:菅野博史 / 中文版總主編:釋果鏡
譯者:辛如意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05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新亞洲佛教史
規格:平裝 / 15x21 cm / 456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210081
ISBN:9789575986698
定價:NT$520
會員價:NT$442 (85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第一章 第二節、道學與佛教
↑TOP
(一)佛教對道學形成的貢獻
道學深受佛教影響已是常論,但在另一方面,有些主張認為此乃中國傳統思想的發展型態之一。筆者除了再次檢視這個問題,亦將探討一個基本問題—佛教以何種形式與儒家思想發展產生關聯。
以朱子學為代表的宋學(道學),以及以陽明學為代表的明學,兩者共通點在於將焦點集中於內心與外界的關係論。
無論宋學或明學,皆將成聖視為最大目的。所謂聖人,就是「不思而得」(《中庸》)、「心之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篇〉),換言之,就是無論外界給予任何影響,我心依然維持適切的反應。聖人因具有高潔純粹的心靈而為聖人,與本文後述的身分、地位尊卑等要件無關。朱子學提倡的理氣論發展宏大,亦是為成聖而存在。缺乏問題意識者所目睹的世界,充其量不過是充斥各種事物外象而已。一旦立志為聖者,就能強烈意識到世界的現實樣貌與本來樣貌之間的相互關係,這種關係可彙整為檢討對象,導入的概念就是「理」與「氣」。
陽明學亦主張聖人像是以心靈崇高而成為聖者,以及聖人是可藉由心來精確因應外界,這兩點與朱子學主張一致。
宋學(道學)、明學兩者的共通點在於:1.強調眾人皆可能達到最高存在之境界;2.最高存在與純粹心理狀態有關;3.心的本質可見於內心與外界之間的反應關係。筆者認為,這些共通點,正反映出佛教對宋學、明學影響最深。
(二)達到最高存在之可能性—佛與聖人
眾人皆可成聖的思想,讓人立即產生聯想的就是佛教的「悉皆成佛」,問題是中國古代性善說與「悉皆成佛」的關係為何。
湯用彤曾發表一篇簡短卻富啟發性的論文—〈謝靈運《辨宗論》書後〉(天津《大公報》十月二十三日《文史週刊》第二期,一九四六,收於《魏晉玄學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其中提到漢、魏以來針對聖人提出的問題是:1.聖是否可成;2.聖如何至。中國傳統思想認為既不可學聖亦不可至聖,印度傳統思想則相信既可學聖亦可至聖。聖人不可至不可學的思想在漢代已廣為流傳,玄學繼承了此思想脈絡。這兩大異說看似難以調和,東晉和南朝劉宋時期的謝靈運(三八五—四三三)卻在《辨宗論》中援引道生(竺道生,?—四三四)之論,將此二說折衷並提出新義。湯用彤根據此說彙整如下:1.聖人不可學不可至,此乃中國傳統;2.聖人可學可至,此乃印度傳統;3.聖人可學不可至,此說無理不能成立;4.聖人不可學但能至,此乃《辨宗論》述生公之新說。道生提倡的新說雖倡導萬人成佛,卻非經由累積學養的過程,而是頓時達到「頓悟」境界,故而主張「聖人不可學」。換言之,道生自印度思想中擷取聖人可至的理念,同時自中國吸取聖人不可學的理念,進而調和兩大異說。湯用彤認為,道生提出的概念與初期道學家程頤主張的眾人皆可成聖的思想有關,只是程頤認為有學方可成聖,此思想端倪可見於前文所述的〈顏子所好何學論〉。就湯用彤的說法,當時一般認為聖人可至卻不可學,程頤卻主張聖人可學,這也是為何胡瑗見程頤之文大感驚異的緣故。換言之,自道生以後,認為可成聖、成佛、成仙的思想逐漸普及化,這僅是成聖的必要手段的分歧而已。
戰國時期,《孟子》云:「舜人也,我亦人也。」(《孟子》〈離婁下〉)《荀子》則對於「學惡乎始?惡乎終?」之問的答覆為:「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荀子》〈勸學篇〉)乍看此文,人人似乎可達聖人境界,但這些議論主張僅是為了強調人之本性蘊涵有可能接受儒家道德的能力,卻還不足以對心靈的完整性立下判斷。
所謂聖,原是指聰慧者,自春秋末期至戰國時期,聖亦包含聖王之意(吉川忠夫,《岩波講座 東洋思想十四 中國宗教思想二 真人と聖人》,岩波書店,一九九○)。古代儒家文獻中可見聖人等同於聖王之例,但眾人無法皆成王者,只要採取這種聖人概念,眾人皆可成聖的思想應不存在。換言之,古代儒家雖將聖人視為修學實踐的最終目標,但有關人可至聖的議論課題此時仍未成為主流。若欲催化人可至聖的思想發酵,畢竟仍需要佛教思想刺激。
在此且多做一點說明。中國可說是接受佛教義理的精神土壤,其思想大致可分為「自然」與「作為」二派,以孟子為代表的思想家屬於前者,以荀子為代表的思想家則屬後者。前者主張人處於自然狀態方為理想,相對的,後者主張順其自然與禽獸無異,必須有所作為,以全人道。如此的區別,導致儒家在學派性格上與道家產生了根本的差異。老、莊等道家思想和孟子皆屬於前者,只不過,自然狀態究竟是讓道德價值無用化或極端明顯化,老、莊等道家思想和孟子等儒家思想之間也產生了分歧。換言之,自然派當中包含了有為自然派與無為自然派,儒家屬於前者,道家屬於後者。另一方面,荀子提出「性惡」的用語僅出現在〈性惡篇〉,對前引〈勸學篇〉中提示人可提昇道德的說法,荀子亦表認同。在此所謂的「作為派」,並非否定人天生具有道德能力,而是更強調人性的潛在危害,故而重視學習或環境的影響效果,亦即後天作為的意義。這點在本質上有別於基督教的原罪概念。嚴謹來說,其在構造上與自然派具有共同要素,但在觀點強調上卻產生極大的分歧。
這兩者之間,自然派逐漸居於主流。道學與此系譜連結;至於魏、晉玄學,則成為邁向道學發展的媒介思想,並因而形成問題。
探討玄學與道學關係的論述甚多,其中,島田虔次採取不應過於誇大佛教對道學影響的觀點,舉出郭象(?—三一二)、韓伯的言論,主張在其思想中已具有宋學(道學)的雛形(《朱子學と陽明學》,岩波新書,一九六七)。玄學式的思考方法確實極有可能對道學造成影響。
然而,筆者認為,玄學與道學並非直線式的影響關係。玄學中最接近道學的思想家是郭象,如前所述,湯用彤關注的課題是郭象在《莊子注》中雖主張以「名教」為末、以「自然」為本,卻顯現兩者不可分離的思想(〈魏晉思想的發展〉,收於《魏晉玄學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郭象將有為自然的狀態視為理,在此範疇之內,堪稱是與道學思想同型。然而,北宋初期的道學家並未論及郭象;筆者認為,初期道學家關注的玄學家是王弼、韓伯。儘管這些道學家抨擊王弼、韓伯對《易經》的闡釋,卻仍認定道家無為自然的立場是「無」思想,並將自我主張視為「有」思想。換言之,面對無為自然之際,是將本身設為有為自然,將自我思想立場更鮮明化。這意味著不斷充分吸收重視自然的思想,成功彰顯有為意涵,程頤所撰的《易傳》即是代表著作之一。唐代編纂的《正義》(註疏),至北宋時期仍具權威。誠如前文所述,「新義」為此陸續出現不少富於思想性的註釋,程頤的著作《易傳》亦是其中之一。他們意識到的著作,在《易經》方面是《周易正義》,而《正義》正是採玄學家王弼、韓伯的註解。由於以上種種背景,道學是以批判角度攝取玄學思想的。
對人而言,完成理想自然狀態者為聖人,眾人內在皆蘊涵自然狀態,人人皆可至聖。尊重自然的立場,必然容易與悉皆成佛的思想結合。在佛教中,禪宗特別強調捨棄一切作為、成為自然狀態,就此意味來說,佛教亦屬於無為自然的類型。當藉由徹底成為無為自然而至佛境界的思想,逐漸傾向於有為自然,這種思想就會轉化為只要徹底遵循社會秩序就可成為聖人。所謂的最高存在,佛教中稱為佛,道教中稱為神仙,儒家則稱為聖人。道教受到佛教「悉皆成佛」的啟迪,提出眾人皆可藉修行成仙的「神仙可學論」,儒家則主張通達學問修養可至聖的「聖人可學論」。道學綜合三種學說,將王弼、韓伯對玄學批判式的攝取思想,加上佛教提倡佛性論的影響,其聖人觀在這兩個因素相輔之下於焉形成。
禪宗講求眾人皆具佛性,宋學(道學)或明學則著眼於人心皆可成聖,最重要的,這裡所謂的聖人,是指心靈完備者。換言之,就是將前述具有古代聖人概念的「王者」性格拂拭殆盡,僅保留純粹內在的完整度,這意味著無論處於何種地位,皆有可能成為聖人。如此一來,當科舉階層變動比前朝更激烈時,士大夫無論是身為中央官僚、政治家,抑或在野文化人,皆可實現成聖理想,此說因而極具吸引力,亦是禪宗能滲透士大夫階層之故。不分社會階層,人人皆可成佛,在家亦有成佛機會,甚至身處高度壓力的官僚核心社會,同樣可獲得精神安定,這對士大夫而言,亦是禪宗之魅力所在。道學產生後,儒家同樣被期待具有如此功能。
在宋代,孔子的門生顏回逐漸受到重視。顏回是孔子最欣賞的弟子,亦是最接近至聖先師的境界,況且還能拒不出仕,安貧樂道,因此成為繼承聖賢的代表人物,備受矚目,一般人也將他視為達成人生境界的目標,程頤的著名論述〈顏子所好何學論〉即是其中的代表。程頤認為,將澹泊名利的顏回視為理想目標,重點不在於社會地位,而是純粹的高尚心境;他同時也導入「理」的概念,將周敦頤牽強運用「無」的思想殘渣拂拭殆盡,確立始終一貫的「有」次元思想。
此外,顏回有「三月不違仁」之稱,以三個月為限全力以赴,故而臻至聖人境界。還有,聖人維持永恆完美的心靈狀態,就是成全自然之存在。那麼具體而言,完美之心究竟為何?
(三)內心與外界
原本道學所稱的聖人,是指內心能對外界適度反應者,從先前引述的「不思而得」(《中庸》)、「心之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篇〉)等說法便可略窺端倪。當人獲此心境時,除了具有意識,尚能對外界產生條件反射式的反應,故可消除一切壓力。為求實現這項理想,就必須消除內心與外界的分別意識。例如,道學開祖之一的程頤曾主張:「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定性書〉)與其否定外界、肯定內心,倒不如不去意識內、外之念。
原本禪宗就有許多諸如此類的議論,包括朱熹在內的道學家,往往將心亂如麻、「思慮紛擾」視為問題所在,禪宗文獻亦主張追求滅絕思慮「紛亂」。若僅除「境」念,即無法除「境」,只徒增「紛亂」而已,必須「心」、「境」俱忘(黃檗希運《傳心法要》)。禪宗文獻以心與境來表現(除《傳心法要》外,尚有牛頭法融《心銘》、荷澤神會《顯宗記》,以及僧璨《信心銘》的「能」與「境」),「心」即是程頤所言的「內」,「境」則是「外」。這種心境才能被賦予「自然」概念,換言之,重視「自然」的思想收攝於內心與外界的反應關係。
這種內心與外界的自然反應關係,以消除自他界限感、達成萬物一體境界的方式來呈現。無論禪宗或道學,兩者共通的萬物一體觀,就是以此方式產生的。筆者想再次說明的,就是應注意心的本質為內心與外界的反應關係。禪宗對道學的最大貢獻,是集中關心心性,將心的本質凝聚於內心與外界的反應關係之中。
那麼,道學與佛教的分歧點為何?答案就在於在人倫方面將內心與外界的反應關係發揮至極致,或者藉此否定或排除人倫。
因此,當內心對外界反應明確時,道學讓人倫得以完美發揮,故而先徹底意識人倫,達到心隨人倫而動的境界,最後連追求人倫的意識也盡除。以道學用語來說,人倫是「理」,首先不斷累積「格物(「推究其物」,意即徹底理解事物之理,亦稱為「窮理」)」,最後獲得「豁然貫通」的感悟,達到「不思而得」的境界。對於道學的思惟方式,禪宗主張若意識到人倫,將阻礙自由曠達的心性發展。首先應拋捨對人倫的意念,最後實現外界和內心原本具有的自然的反應關係。在此情況下,即使是在禪宗接近士大夫的過程中,結果並未強烈傾向於實現不違背人倫的心靈作用,有時甚至比儒者更高唱愛國主義。即使是禪宗,最終仍暗示應如何實踐士大夫的價值觀。總之,在出發點上,究竟該徹底意識人倫,或否定及排除人倫,道學與禪宗出現了決定性的分歧。佛教在心性問題方面雖對儒家影響甚深,卻也出現接近儒家價值觀的層面,堪稱是互為影響。
(四)修養論的發展
除上述課題外,道學受佛教思想啟發的領域尚有「修養論」。在此同時,儒家雖受坐禪影響,卻亟欲構思與坐禪截然不同的修養法,例如司馬光提倡「中」修養法。「中」是以儒家經書《中庸》為基礎概念,司馬光有意在儒學中探尋可與禪宗抗衡的修養方式。
程顥、程頤則提出前述的「敬」修養法,就是以心為專一對象,不僅在靜室內澄澈心靈,並在日常事物的應對場域中實踐。「敬」是以《易經》為代表的經書為依據,二程從儒家經書中求取與坐禪抗衡的修養法。誠然,古代並無此類修養法,這畢竟是受禪宗啟迪的一種嘗試。
「敬」修養法堪稱是劃時代的構想。冥想法當中,一般分為對某特定對象集中意識型,以及無念無想型。前者多以神或公案等無形對象為主流,「敬」則不同於這些類型,其集中意識的對象是眼前之物,而非集中意識的行為,並且從中測定對此對象的感覺有多鮮明、能實踐多少「敬」。若將意識集中於此對象,便能開啟心的原有功能,經由不斷實踐,有助於日後發展的長久性。
此外,朱熹主張當心靈動向對某對象感到不協調時,剎那間就會發動本善之心。這項邏輯之所以成立,在於正因為發動本善之心,才讓歪曲之心顯現不協調。如此將心投注於某對象,一切日常情境將成為修養場域,就可避免直接以心為對象。此即為「敬」的意義。
在此提到避免將心視為對象,朱熹在邏輯或實踐方面,皆將以心見心視為問題。這項論述可見於「觀心說」等主張。朱熹縱然正面攻擊佛教,同時卻將屬於道學流派的湖南學、甚至陸九淵學派一併納入攻擊範圍。
朱熹對佛教式「觀心」的批判論點,在於若是以心觀心,將導致所觀之心與被觀之心同時並存。朱熹在其他場合提出疑問,認為縱然是以心觀心,最初生起惡心,繼而起反省善心,再起自覺反省之心,這些心念同時並存本非合理,萬一每個心念在霎時發生作用,則又顯得過於慌亂(〈答吳晦叔〉六)。在此所謂的慌亂,是指無法期待修養效果的實踐問題亦糾結其中,而朱熹在議論中不時出現邏輯上的整合與實踐上的要求相混的情形,或許也在此顯現。
(五)因應死亡
在儒家思想中,道學受佛教影響最深,但亦是與佛教最徹底頑抗的學說。道學受儒家思想的觸發,對佛教提出的一切議論進行爭逐,其中最大的難題就是死亡問題。
原本儒家就不倡說來世或輪迴轉生,但再如何探討死亡結構,亦無法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北宋末年,劉安世(一一○○—六七)援用司馬光之說,指出五經無法讓人理解生死,佛教面臨此課題卻能處於優勢(馬永卿輯《元城語錄》上)。即使連朱熹本身,也聲稱經書雖充分述說聖賢行蹟,但對生死交關之事卻隻字未提(〈跋鄭景元簡〉),道學家張載、程頤則勇於挑戰此問題。
首先張載以自我之氣與太虛思想來說明死亡,人猶如水面浮冰,死則如冰融釋於水。冰無法以同樣形狀重生,水整體永恆不變,故應捨棄自我框限,與全宇宙同一化,如此便能感悟永恆。
其次,程頤主張人人必經成長及衰老的歷程,此為自然現象,故應徹底成為自然,與天地合一。換言之,就是經常維持與天地合一的恆常性,即可感悟永恆。
張載、程頤皆未提及來世或輪迴轉生,只藉由心靈作用克服對死亡的恐懼。然而,這種心境無法輕易獲得,畢竟佛教在死亡問題上所居的優勢地位屹立不搖。
原本在儒家思想中,死後魂魄分離,亡魂將轉移至神主牌,在祠堂接受祭祀。只要有血脈相傳的子孫持續祭祀,血族既能同心,亡魂將繼續顯應。然而隨著歲月增長,亡魂反應漸弱,卻仍被認為有跡象可循,在古代僅有上層階級方能設置神主。
程頤主張身為士大夫應祭祀神主,目的是促進士大夫從佛教信仰回歸儒家祭祀。佛教本無神主牌,至宋代方才採用,此習俗亦傳至日本。程頤的祭祀思想為朱熹所繼承,撰有《文公家禮》(亦有說法指出此書並非由朱熹完成)。程頤、朱熹試圖貫徹實行儒家祭祀,讓死亡問題成為儒家獨占的思想領域。附帶一提,二程兄弟向來以家室中不採佛教祀法為傲。
然而,靈魂移入神主牌的亡魂,既然處於凡是子孫缺乏祭祀就無法顯應的被動立場,加上顯應日漸衰微的情況下,無法徹底解決眾人被暴露在永恆之無的死亡恐怖下所造成的根本問題,人們縱然舉行儒家祭祀,依舊前往寺廟祈拜。佛教在諸多領域中遭致道學壓迫,但在死亡問題方面,卻能維持不變之重要性。
(六)三教並存之道
道學是提供士大夫生存原理的思想,如前所述,佛教人士亦親近士大夫,逐漸散播思想魅力。儒、佛皆嘗試因應士大夫的精神需求,中心課題就是心的問題。
佛教中的禪宗與淨土宗發展隆盛,淨土宗並非僅著重西方,而是傾向於發現心中淨土的唯心淨土思想。這種逐漸關注心性的傾向,與禪宗甚至道學皆有相通之處。至於道教方面,藉由冥想或呼吸法求取成仙的內丹十分發達,服用不死藥的外丹雖漸趨式微,卻同樣將重點置於身心層面,以順應時代潮流發展。
如此看來,更可感受佛教影響深遠,對集中關注心性的課題遍布各教派,紛紛引發各種思想交流或融合、駁斥之舉。
集中關注於心性課題,亦可發現探討心靈場域將導致議論分歧,另一方面,亦有思想流派試圖超越教派藩籬,加速議論同一化。換言之,儒、釋、道三教皆以達到本心至高境界為目標,只要提高心靈境界,無論何種方式皆具意義。三教儘管注重各自權威,更將心性權威視為其上,如此便可摒除三教藩籬,漸而形成「三教合一」形式。明代王守仁(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倡導的陽明學強調心性權威,多數儒學家出自此流派,皆具三教合一傾向,正是受此風潮影響所致。有關此項問題,筆者已發表拙論〈三教圖への道—中國近世における心の思想〉(《シリーズ東アジア佛教五,東アジア社會と佛教文化》,春秋社,一九九六),在此暫容省略,但孔子(儒)、釋迦(釋)、老子(道)三聖暢談的三教圖(三聖圖),就是由此衍生而來。
以上屬於思想傳遞訊息方面,至於接受思想訊息者,則採取更柔軟的姿態。士大夫具有儒家涵養,在親屬或個人面臨死亡之際往詣佛寺,為求精神安定,參詣禪剎不曾間斷。儒、釋、道並列之中,士大夫與百姓多以因應狀況而選擇適於己身的思想。
道學深受佛教影響已是常論,但在另一方面,有些主張認為此乃中國傳統思想的發展型態之一。筆者除了再次檢視這個問題,亦將探討一個基本問題—佛教以何種形式與儒家思想發展產生關聯。
以朱子學為代表的宋學(道學),以及以陽明學為代表的明學,兩者共通點在於將焦點集中於內心與外界的關係論。
無論宋學或明學,皆將成聖視為最大目的。所謂聖人,就是「不思而得」(《中庸》)、「心之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篇〉),換言之,就是無論外界給予任何影響,我心依然維持適切的反應。聖人因具有高潔純粹的心靈而為聖人,與本文後述的身分、地位尊卑等要件無關。朱子學提倡的理氣論發展宏大,亦是為成聖而存在。缺乏問題意識者所目睹的世界,充其量不過是充斥各種事物外象而已。一旦立志為聖者,就能強烈意識到世界的現實樣貌與本來樣貌之間的相互關係,這種關係可彙整為檢討對象,導入的概念就是「理」與「氣」。
陽明學亦主張聖人像是以心靈崇高而成為聖者,以及聖人是可藉由心來精確因應外界,這兩點與朱子學主張一致。
宋學(道學)、明學兩者的共通點在於:1.強調眾人皆可能達到最高存在之境界;2.最高存在與純粹心理狀態有關;3.心的本質可見於內心與外界之間的反應關係。筆者認為,這些共通點,正反映出佛教對宋學、明學影響最深。
(二)達到最高存在之可能性—佛與聖人
眾人皆可成聖的思想,讓人立即產生聯想的就是佛教的「悉皆成佛」,問題是中國古代性善說與「悉皆成佛」的關係為何。
湯用彤曾發表一篇簡短卻富啟發性的論文—〈謝靈運《辨宗論》書後〉(天津《大公報》十月二十三日《文史週刊》第二期,一九四六,收於《魏晉玄學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其中提到漢、魏以來針對聖人提出的問題是:1.聖是否可成;2.聖如何至。中國傳統思想認為既不可學聖亦不可至聖,印度傳統思想則相信既可學聖亦可至聖。聖人不可至不可學的思想在漢代已廣為流傳,玄學繼承了此思想脈絡。這兩大異說看似難以調和,東晉和南朝劉宋時期的謝靈運(三八五—四三三)卻在《辨宗論》中援引道生(竺道生,?—四三四)之論,將此二說折衷並提出新義。湯用彤根據此說彙整如下:1.聖人不可學不可至,此乃中國傳統;2.聖人可學可至,此乃印度傳統;3.聖人可學不可至,此說無理不能成立;4.聖人不可學但能至,此乃《辨宗論》述生公之新說。道生提倡的新說雖倡導萬人成佛,卻非經由累積學養的過程,而是頓時達到「頓悟」境界,故而主張「聖人不可學」。換言之,道生自印度思想中擷取聖人可至的理念,同時自中國吸取聖人不可學的理念,進而調和兩大異說。湯用彤認為,道生提出的概念與初期道學家程頤主張的眾人皆可成聖的思想有關,只是程頤認為有學方可成聖,此思想端倪可見於前文所述的〈顏子所好何學論〉。就湯用彤的說法,當時一般認為聖人可至卻不可學,程頤卻主張聖人可學,這也是為何胡瑗見程頤之文大感驚異的緣故。換言之,自道生以後,認為可成聖、成佛、成仙的思想逐漸普及化,這僅是成聖的必要手段的分歧而已。
戰國時期,《孟子》云:「舜人也,我亦人也。」(《孟子》〈離婁下〉)《荀子》則對於「學惡乎始?惡乎終?」之問的答覆為:「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荀子》〈勸學篇〉)乍看此文,人人似乎可達聖人境界,但這些議論主張僅是為了強調人之本性蘊涵有可能接受儒家道德的能力,卻還不足以對心靈的完整性立下判斷。
所謂聖,原是指聰慧者,自春秋末期至戰國時期,聖亦包含聖王之意(吉川忠夫,《岩波講座 東洋思想十四 中國宗教思想二 真人と聖人》,岩波書店,一九九○)。古代儒家文獻中可見聖人等同於聖王之例,但眾人無法皆成王者,只要採取這種聖人概念,眾人皆可成聖的思想應不存在。換言之,古代儒家雖將聖人視為修學實踐的最終目標,但有關人可至聖的議論課題此時仍未成為主流。若欲催化人可至聖的思想發酵,畢竟仍需要佛教思想刺激。
在此且多做一點說明。中國可說是接受佛教義理的精神土壤,其思想大致可分為「自然」與「作為」二派,以孟子為代表的思想家屬於前者,以荀子為代表的思想家則屬後者。前者主張人處於自然狀態方為理想,相對的,後者主張順其自然與禽獸無異,必須有所作為,以全人道。如此的區別,導致儒家在學派性格上與道家產生了根本的差異。老、莊等道家思想和孟子皆屬於前者,只不過,自然狀態究竟是讓道德價值無用化或極端明顯化,老、莊等道家思想和孟子等儒家思想之間也產生了分歧。換言之,自然派當中包含了有為自然派與無為自然派,儒家屬於前者,道家屬於後者。另一方面,荀子提出「性惡」的用語僅出現在〈性惡篇〉,對前引〈勸學篇〉中提示人可提昇道德的說法,荀子亦表認同。在此所謂的「作為派」,並非否定人天生具有道德能力,而是更強調人性的潛在危害,故而重視學習或環境的影響效果,亦即後天作為的意義。這點在本質上有別於基督教的原罪概念。嚴謹來說,其在構造上與自然派具有共同要素,但在觀點強調上卻產生極大的分歧。
這兩者之間,自然派逐漸居於主流。道學與此系譜連結;至於魏、晉玄學,則成為邁向道學發展的媒介思想,並因而形成問題。
探討玄學與道學關係的論述甚多,其中,島田虔次採取不應過於誇大佛教對道學影響的觀點,舉出郭象(?—三一二)、韓伯的言論,主張在其思想中已具有宋學(道學)的雛形(《朱子學と陽明學》,岩波新書,一九六七)。玄學式的思考方法確實極有可能對道學造成影響。
然而,筆者認為,玄學與道學並非直線式的影響關係。玄學中最接近道學的思想家是郭象,如前所述,湯用彤關注的課題是郭象在《莊子注》中雖主張以「名教」為末、以「自然」為本,卻顯現兩者不可分離的思想(〈魏晉思想的發展〉,收於《魏晉玄學論稿》,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郭象將有為自然的狀態視為理,在此範疇之內,堪稱是與道學思想同型。然而,北宋初期的道學家並未論及郭象;筆者認為,初期道學家關注的玄學家是王弼、韓伯。儘管這些道學家抨擊王弼、韓伯對《易經》的闡釋,卻仍認定道家無為自然的立場是「無」思想,並將自我主張視為「有」思想。換言之,面對無為自然之際,是將本身設為有為自然,將自我思想立場更鮮明化。這意味著不斷充分吸收重視自然的思想,成功彰顯有為意涵,程頤所撰的《易傳》即是代表著作之一。唐代編纂的《正義》(註疏),至北宋時期仍具權威。誠如前文所述,「新義」為此陸續出現不少富於思想性的註釋,程頤的著作《易傳》亦是其中之一。他們意識到的著作,在《易經》方面是《周易正義》,而《正義》正是採玄學家王弼、韓伯的註解。由於以上種種背景,道學是以批判角度攝取玄學思想的。
對人而言,完成理想自然狀態者為聖人,眾人內在皆蘊涵自然狀態,人人皆可至聖。尊重自然的立場,必然容易與悉皆成佛的思想結合。在佛教中,禪宗特別強調捨棄一切作為、成為自然狀態,就此意味來說,佛教亦屬於無為自然的類型。當藉由徹底成為無為自然而至佛境界的思想,逐漸傾向於有為自然,這種思想就會轉化為只要徹底遵循社會秩序就可成為聖人。所謂的最高存在,佛教中稱為佛,道教中稱為神仙,儒家則稱為聖人。道教受到佛教「悉皆成佛」的啟迪,提出眾人皆可藉修行成仙的「神仙可學論」,儒家則主張通達學問修養可至聖的「聖人可學論」。道學綜合三種學說,將王弼、韓伯對玄學批判式的攝取思想,加上佛教提倡佛性論的影響,其聖人觀在這兩個因素相輔之下於焉形成。
禪宗講求眾人皆具佛性,宋學(道學)或明學則著眼於人心皆可成聖,最重要的,這裡所謂的聖人,是指心靈完備者。換言之,就是將前述具有古代聖人概念的「王者」性格拂拭殆盡,僅保留純粹內在的完整度,這意味著無論處於何種地位,皆有可能成為聖人。如此一來,當科舉階層變動比前朝更激烈時,士大夫無論是身為中央官僚、政治家,抑或在野文化人,皆可實現成聖理想,此說因而極具吸引力,亦是禪宗能滲透士大夫階層之故。不分社會階層,人人皆可成佛,在家亦有成佛機會,甚至身處高度壓力的官僚核心社會,同樣可獲得精神安定,這對士大夫而言,亦是禪宗之魅力所在。道學產生後,儒家同樣被期待具有如此功能。
在宋代,孔子的門生顏回逐漸受到重視。顏回是孔子最欣賞的弟子,亦是最接近至聖先師的境界,況且還能拒不出仕,安貧樂道,因此成為繼承聖賢的代表人物,備受矚目,一般人也將他視為達成人生境界的目標,程頤的著名論述〈顏子所好何學論〉即是其中的代表。程頤認為,將澹泊名利的顏回視為理想目標,重點不在於社會地位,而是純粹的高尚心境;他同時也導入「理」的概念,將周敦頤牽強運用「無」的思想殘渣拂拭殆盡,確立始終一貫的「有」次元思想。
此外,顏回有「三月不違仁」之稱,以三個月為限全力以赴,故而臻至聖人境界。還有,聖人維持永恆完美的心靈狀態,就是成全自然之存在。那麼具體而言,完美之心究竟為何?
(三)內心與外界
原本道學所稱的聖人,是指內心能對外界適度反應者,從先前引述的「不思而得」(《中庸》)、「心之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篇〉)等說法便可略窺端倪。當人獲此心境時,除了具有意識,尚能對外界產生條件反射式的反應,故可消除一切壓力。為求實現這項理想,就必須消除內心與外界的分別意識。例如,道學開祖之一的程頤曾主張:「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定性書〉)與其否定外界、肯定內心,倒不如不去意識內、外之念。
原本禪宗就有許多諸如此類的議論,包括朱熹在內的道學家,往往將心亂如麻、「思慮紛擾」視為問題所在,禪宗文獻亦主張追求滅絕思慮「紛亂」。若僅除「境」念,即無法除「境」,只徒增「紛亂」而已,必須「心」、「境」俱忘(黃檗希運《傳心法要》)。禪宗文獻以心與境來表現(除《傳心法要》外,尚有牛頭法融《心銘》、荷澤神會《顯宗記》,以及僧璨《信心銘》的「能」與「境」),「心」即是程頤所言的「內」,「境」則是「外」。這種心境才能被賦予「自然」概念,換言之,重視「自然」的思想收攝於內心與外界的反應關係。
這種內心與外界的自然反應關係,以消除自他界限感、達成萬物一體境界的方式來呈現。無論禪宗或道學,兩者共通的萬物一體觀,就是以此方式產生的。筆者想再次說明的,就是應注意心的本質為內心與外界的反應關係。禪宗對道學的最大貢獻,是集中關心心性,將心的本質凝聚於內心與外界的反應關係之中。
那麼,道學與佛教的分歧點為何?答案就在於在人倫方面將內心與外界的反應關係發揮至極致,或者藉此否定或排除人倫。
因此,當內心對外界反應明確時,道學讓人倫得以完美發揮,故而先徹底意識人倫,達到心隨人倫而動的境界,最後連追求人倫的意識也盡除。以道學用語來說,人倫是「理」,首先不斷累積「格物(「推究其物」,意即徹底理解事物之理,亦稱為「窮理」)」,最後獲得「豁然貫通」的感悟,達到「不思而得」的境界。對於道學的思惟方式,禪宗主張若意識到人倫,將阻礙自由曠達的心性發展。首先應拋捨對人倫的意念,最後實現外界和內心原本具有的自然的反應關係。在此情況下,即使是在禪宗接近士大夫的過程中,結果並未強烈傾向於實現不違背人倫的心靈作用,有時甚至比儒者更高唱愛國主義。即使是禪宗,最終仍暗示應如何實踐士大夫的價值觀。總之,在出發點上,究竟該徹底意識人倫,或否定及排除人倫,道學與禪宗出現了決定性的分歧。佛教在心性問題方面雖對儒家影響甚深,卻也出現接近儒家價值觀的層面,堪稱是互為影響。
(四)修養論的發展
除上述課題外,道學受佛教思想啟發的領域尚有「修養論」。在此同時,儒家雖受坐禪影響,卻亟欲構思與坐禪截然不同的修養法,例如司馬光提倡「中」修養法。「中」是以儒家經書《中庸》為基礎概念,司馬光有意在儒學中探尋可與禪宗抗衡的修養方式。
程顥、程頤則提出前述的「敬」修養法,就是以心為專一對象,不僅在靜室內澄澈心靈,並在日常事物的應對場域中實踐。「敬」是以《易經》為代表的經書為依據,二程從儒家經書中求取與坐禪抗衡的修養法。誠然,古代並無此類修養法,這畢竟是受禪宗啟迪的一種嘗試。
「敬」修養法堪稱是劃時代的構想。冥想法當中,一般分為對某特定對象集中意識型,以及無念無想型。前者多以神或公案等無形對象為主流,「敬」則不同於這些類型,其集中意識的對象是眼前之物,而非集中意識的行為,並且從中測定對此對象的感覺有多鮮明、能實踐多少「敬」。若將意識集中於此對象,便能開啟心的原有功能,經由不斷實踐,有助於日後發展的長久性。
此外,朱熹主張當心靈動向對某對象感到不協調時,剎那間就會發動本善之心。這項邏輯之所以成立,在於正因為發動本善之心,才讓歪曲之心顯現不協調。如此將心投注於某對象,一切日常情境將成為修養場域,就可避免直接以心為對象。此即為「敬」的意義。
在此提到避免將心視為對象,朱熹在邏輯或實踐方面,皆將以心見心視為問題。這項論述可見於「觀心說」等主張。朱熹縱然正面攻擊佛教,同時卻將屬於道學流派的湖南學、甚至陸九淵學派一併納入攻擊範圍。
朱熹對佛教式「觀心」的批判論點,在於若是以心觀心,將導致所觀之心與被觀之心同時並存。朱熹在其他場合提出疑問,認為縱然是以心觀心,最初生起惡心,繼而起反省善心,再起自覺反省之心,這些心念同時並存本非合理,萬一每個心念在霎時發生作用,則又顯得過於慌亂(〈答吳晦叔〉六)。在此所謂的慌亂,是指無法期待修養效果的實踐問題亦糾結其中,而朱熹在議論中不時出現邏輯上的整合與實踐上的要求相混的情形,或許也在此顯現。
(五)因應死亡
在儒家思想中,道學受佛教影響最深,但亦是與佛教最徹底頑抗的學說。道學受儒家思想的觸發,對佛教提出的一切議論進行爭逐,其中最大的難題就是死亡問題。
原本儒家就不倡說來世或輪迴轉生,但再如何探討死亡結構,亦無法克服對死亡的恐懼。北宋末年,劉安世(一一○○—六七)援用司馬光之說,指出五經無法讓人理解生死,佛教面臨此課題卻能處於優勢(馬永卿輯《元城語錄》上)。即使連朱熹本身,也聲稱經書雖充分述說聖賢行蹟,但對生死交關之事卻隻字未提(〈跋鄭景元簡〉),道學家張載、程頤則勇於挑戰此問題。
首先張載以自我之氣與太虛思想來說明死亡,人猶如水面浮冰,死則如冰融釋於水。冰無法以同樣形狀重生,水整體永恆不變,故應捨棄自我框限,與全宇宙同一化,如此便能感悟永恆。
其次,程頤主張人人必經成長及衰老的歷程,此為自然現象,故應徹底成為自然,與天地合一。換言之,就是經常維持與天地合一的恆常性,即可感悟永恆。
張載、程頤皆未提及來世或輪迴轉生,只藉由心靈作用克服對死亡的恐懼。然而,這種心境無法輕易獲得,畢竟佛教在死亡問題上所居的優勢地位屹立不搖。
原本在儒家思想中,死後魂魄分離,亡魂將轉移至神主牌,在祠堂接受祭祀。只要有血脈相傳的子孫持續祭祀,血族既能同心,亡魂將繼續顯應。然而隨著歲月增長,亡魂反應漸弱,卻仍被認為有跡象可循,在古代僅有上層階級方能設置神主。
程頤主張身為士大夫應祭祀神主,目的是促進士大夫從佛教信仰回歸儒家祭祀。佛教本無神主牌,至宋代方才採用,此習俗亦傳至日本。程頤的祭祀思想為朱熹所繼承,撰有《文公家禮》(亦有說法指出此書並非由朱熹完成)。程頤、朱熹試圖貫徹實行儒家祭祀,讓死亡問題成為儒家獨占的思想領域。附帶一提,二程兄弟向來以家室中不採佛教祀法為傲。
然而,靈魂移入神主牌的亡魂,既然處於凡是子孫缺乏祭祀就無法顯應的被動立場,加上顯應日漸衰微的情況下,無法徹底解決眾人被暴露在永恆之無的死亡恐怖下所造成的根本問題,人們縱然舉行儒家祭祀,依舊前往寺廟祈拜。佛教在諸多領域中遭致道學壓迫,但在死亡問題方面,卻能維持不變之重要性。
(六)三教並存之道
道學是提供士大夫生存原理的思想,如前所述,佛教人士亦親近士大夫,逐漸散播思想魅力。儒、佛皆嘗試因應士大夫的精神需求,中心課題就是心的問題。
佛教中的禪宗與淨土宗發展隆盛,淨土宗並非僅著重西方,而是傾向於發現心中淨土的唯心淨土思想。這種逐漸關注心性的傾向,與禪宗甚至道學皆有相通之處。至於道教方面,藉由冥想或呼吸法求取成仙的內丹十分發達,服用不死藥的外丹雖漸趨式微,卻同樣將重點置於身心層面,以順應時代潮流發展。
如此看來,更可感受佛教影響深遠,對集中關注心性的課題遍布各教派,紛紛引發各種思想交流或融合、駁斥之舉。
集中關注於心性課題,亦可發現探討心靈場域將導致議論分歧,另一方面,亦有思想流派試圖超越教派藩籬,加速議論同一化。換言之,儒、釋、道三教皆以達到本心至高境界為目標,只要提高心靈境界,無論何種方式皆具意義。三教儘管注重各自權威,更將心性權威視為其上,如此便可摒除三教藩籬,漸而形成「三教合一」形式。明代王守仁(陽明,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倡導的陽明學強調心性權威,多數儒學家出自此流派,皆具三教合一傾向,正是受此風潮影響所致。有關此項問題,筆者已發表拙論〈三教圖への道—中國近世における心の思想〉(《シリーズ東アジア佛教五,東アジア社會と佛教文化》,春秋社,一九九六),在此暫容省略,但孔子(儒)、釋迦(釋)、老子(道)三聖暢談的三教圖(三聖圖),就是由此衍生而來。
以上屬於思想傳遞訊息方面,至於接受思想訊息者,則採取更柔軟的姿態。士大夫具有儒家涵養,在親屬或個人面臨死亡之際往詣佛寺,為求精神安定,參詣禪剎不曾間斷。儒、釋、道並列之中,士大夫與百姓多以因應狀況而選擇適於己身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