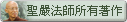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道與空性:老子與龍樹的哲學對話
作者:林建德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3年09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漢傳佛教論叢
規格:14.8x21 cm / 平裝 / 410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260031
ISBN:9789575986230
定價:NT$480
會員價:NT$408 (85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第三節 《老子》與《中論》語言策略之共通處探討
↑TOP
第三節 《老子》與《中論》語言策略之共通處探討
如「緒論」所說, B. K. Matilal曾指出中觀學派和道家使用了非常相近的語言,來表達他們想要說的話,150並認為此二者乃因而成為西方觀點下的東方神祕主義。151Matilal指出,在中觀學裡諸多語句的表達未必合於一般常理思路,甚至含有反邏輯、反理性的傾向,152而這樣的表達方式,在道家思想論述中也時而可見,例如《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即表達了相近的意趣。由此觀點延伸而出,道家與中觀學派對於語言有著什麼樣共通的見解,便成了一個可以探討的課題。
以上諸節已分別討論《老子》與《中論》語言策略的思想概要;其中就《老子》部分,我們可依下列三個重點來理解:
一、「道」不可言說,可說即不是「道」。
二、以兩兩、正反對演的方式而說。
三、「正言若反」為其言說技藝之一。
可知《老子》首章揭示「道」之無限性以及語言表達「道」的有限性,因此如何運用有限的語言來展示無所限制的「道」,成了老學關心之重點。而為顯示「道」為何物,《老子》善於以兩兩對演的方式進行論述,似告訴我們「道」可以從世間的正反關係去理解。153就《中論》的部分,亦有下列三個重點:
一、佛所悟之法甚深難知而不欲說。
二、凡有所言說皆不是(破)。
三、但以二諦與假名方便教說之(立)。
因為佛法甚深而眾生計執太重,所以《中論》似採取「破」、「立」的兩手策略,既以「不說」、「不可說」、「無所說」破諸戲論計執,又以「二諦說」、「假名說」之方便開演來教化眾生。因此就《老子》和《中論》的語言策略或語言運用而言,前者善於以兩兩對演、正反思辨的方式來顯示「道」的深意,後者則以破、立兼施的兩面手法,輾轉交互運用,指引出佛法的歸趣。因此,關於《老子》與《中論》的語言策略,我們可以分別歸納出「正反」與「立破」之策略運用模式;而且,兩者所提出的語言策略,以及其本身所運用的語言策略,乃是一致的。154
根據以上之對比,初步可以同意Matilal所言,即《老子》和《中論》在某個面向上,用了相近的語言表達方式;尤其從《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等,以及《中論》以「不說」、「不可說」、「無所說」等,來標示任何的言說皆不是;就這點上,兩者在外在形式上,實有其一定的相似性。也因此,後代禪門「說似一物即不中」的名句,155究竟是繼承於佛教內部的思想、還是承接自道家的觀點,就難以確切分辨;可以說其既與《中論》的見解有關,卻也不離《老子》的看法。
但是,《老子》與《中論》語言策略背後的思想仍是明顯不同的。例如,《老子》的「正言若反」與《中論》的假名及二諦說,可以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範疇,實際所談的內容及運用之模式也互有差異。兩者共同的交集,主要在於面對不可說的道理,所提出的策略性回應,如善用正反遮照的方式,以試著貼近其欲宣說的理論。簡言之,為了不可說之道,兩者有所謂正反、立破等語言策略之使用,並藉由這些策略、方法,去說那不可說之說(saying the unsayable)。
《老子》與《中論》兩者,在說不可說的同時,其所運用的語言策略有哪些共通點,以及不可說及語言策略的背後,可能表示著什麼樣的意義,也成了值得探討的問題。兩者同樣做為某種哲學或宗教,皆以智慧型態為其主軸,給予世人深刻的啟示;在宣說各自的智慧教示時,確有既說、又不說的共通之處,156從而顯示出外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暫且不論其智慧內容為何,157僅就語言表達的形式而言,對於展現智慧過程中,其間正反、立破語言策略運用的相似或共通處,及其所透顯出的意義,以下即列舉出五個小節做探討。
首先,兩者語言策略之運用,皆為了回應不可說。其次,在語言策略視域下,皆顯示說與不說的微妙與弔詭;即說不可說可視為說之準備,而之所以要說,又是為了不說,顯示出說與不說間之不即不離。第三,兩者之語言策略皆具有動態、靈巧之特質,使能不執著而善用語言、駕馭語言不被語言所誤。第四,關於策略之運用所引起的誤解,在此也做一討論與澄清。最後,小結以上之討論。以下即分別做說明。
一、以語言策略因應不可說
從語言策略入手,探討《老子》與《中論》的語言觀,乃是本研究的特點之一。語言策略的概念,乃與不可說相對,而道、佛哲學中不可說命題的強調,又是其中的特色,因此從語言策略掌握道、佛的語言觀或語言哲學,應是可嘗試的新進路。進言之,佛、道語言哲學的特色之一,乃是在實際運用、教化的層面上,展示出其獨特性。而此語用面向具體的展示之一,即是語言策略或技藝的運用。而且《老子》與《中論》不僅僅提出其語言策略的觀點,事實上也善用此語言策略來做表述,此點實不容二諦」之「破立」的語言策略,其本身也分別力行「正反」與「立破」的語言策略。換言之,兩者皆運用所提出來的語言策略,去表達哲學見解(包括語言策略),而且從《老子》「正反」與《中論》「立破」的語言策略,可知其本身已善於運用語言。
就《老子》與《中論》而言,兩者同樣面對不可說的道理;為了說此不可說,兩者皆開展出其語言策略及對語言的反思。對老子和龍樹來說,語言不能窮究對道與空性、涅槃的認識,但又不能不依靠語言;換言之,語言有一定的工具性價值,使能指向道或諸法實相的認識。因此,兩者所指出的未必全在於語言的限制,也包含了如何善用語言以宣說道理、教化世人。所以,不管是《老子》「正言若反」的正反對演,還是《中論》或說或不說、既立且破的兩面策略,兩者皆強調善用語言技藝,目的之一是為了避免執文害義,而能靈活以待。可知兩者在展示其智慧型態時,有著相近的論述手法。對於兩者在不說與說、不言與言(或不名與名)之間,我們可以就道、佛各自的語言特色,做下列的整理:
不可言說:
道家:
道不可言、不可名、無名
佛教:
空不可說、不欲說、無所說
權巧地說(語言策略):
道家:
正言若反、始制有名(強為之名)、善
言、貴言、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等
佛教:
假名說、二諦說、中道說(說於中
道)、方便說、依義不依語等
可知,道與空性不可說其中所隱含的意涵之一,可在於善用技藝而靈敏地說;即在不可說之餘,如何發揮語言策略以做因應,也是兩者哲學所關心的。因此,相對於西方學界慣以「神祕主義」(mysticism),或者超驗性(transcendental)的觀點,158以及「語言的限制」等,來理解東方哲學所謂的不可說,實際上「權巧地說」也是要傳達的訊息之一。或者,換個方式說,做為宗教實踐面向的老學和中觀學,所謂的不可說強調的主要是修證經驗上語言的非認知性;而做為哲學思辨面向的老學和中觀學,具有十足理智思辨的特質,所指的不可言說,背後應蘊含語言策略運用之必要。
二、語言策略視域下說與不可說間的微妙所在
「不可說」本身即存在一定的弔詭,此點除了古代哲學曾探討過外,在現今也有不少的討論。159若將此一課題的探討,引到語言策略的視域、脈絡下來檢視,或許能有新的啟發。例如,在語言策略的視域下,「說」固然是種語言策略,在此同時,說「不可說」彷彿也可以視為語言策略的運用。此外,在語言策略的觀點下,已使不可說在某個意義下成為可說,而這樣的說終極而言又是為了不(可)說,如此的輾轉交錯,也顯示出一種微妙與弔詭。以下即分三部分來談這些微妙處,即:一、說「不可說」可視為說之預備;二、說是為了不說;三、說與不說間不即不離。
(一)說「不可說」可視為說之預備
說「不可說」此不說之說,可視為一否定之說,即通過否定性的言說指出道、法的超越性與非概念性,此意味著別的言說方式行不通,而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除此之外,說「不可說」亦158 以超驗(transcendence)來理解佛教的宗教經驗,Asanga Tilakaratne也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原始佛教(Early Buddhism)的語言觀及實相觀,皆不是超驗式的,這點與其他的宗教截然有別。見Nirvana and Ineffability: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Theory of Reality and Language, Sri Lanka: University of Kelaniya,
1993, p. 9.
可視為說之準備,或者進而言之:當說一切法不可說時,可能是為說一切法,所做之準備;相近地,當說道不可說時,可能也是為表達道時,所做之準備。160
本文談《老子》和《中論》的語言策略,乃在於《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道常無名」以及佛陀「默然不欲說法」的理路脈絡下,所進行的探討。或者說,《老子》之所以會發展出
正言若反的言說方式,而《中論》會有無所說、假名說以及二諦等既立又破的語言策略,其間主要的理由,乃是在因應道不可道或空不可說的難處。如果道可輕易地被認識,或者涅槃與空性可以淺顯地被理解,則所謂的不可名、不欲說的宣稱即是多餘的。甚至,所謂的不可名、不欲說,也是其語言策略運用的手法之一,其用意似是為說做準備。如《老子》首章第一句話即說:「道可道非常道」,背後所蘊涵的巧思乃是耐人尋味。
既然有語言策略的運用,此時不可說的背後,可隱含其他可能的意義,而其中的意義之一,可以是為說做準備;因此在宣稱不可說時,本身似已是某種語言策略的使用。此外,所謂的不可說、不欲說,除了是為傳達深奧道理所做之宣示外,可能也是要說道者巧妙地說、聞道者靈敏地聽。關於這點,以下做進一步分析:
1.「不可說」本身也是語言策略
不論是道家思想或佛教哲學,兩者的哲理常為世人所重,而且在表達思想時,皆不約而同地宣稱其深邃難解。如《老子》首章從「道可道非常道」,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使得《老
子》的「道」,自古以來即如「謎」一樣般玄深難測。此外,佛法思想中心雖在於苦與苦的止息,但從不欲說、不可說、不可思議等的強調,也說明了佛教緣起、空與涅槃等法義的甚深。而正因為所要傳達的道理過於深奧,所以「不可言說」的觀點,便成了道家典籍及佛教經論兩家思想共同的特色。但說此不可說可能具有哪些意義?
如此的不可言說,若從不同的角度做分析,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所謂的玄深,或反覆強調甚深微妙,其中有五種可能的用意如下:
一、指義理上的深邃難解。161
二、語言的局限性。162
三、宗教經驗上的不可傳達(如涅槃體驗)。163
四、信仰面向情感上的歸敬、讚仰。164
五、聞道者的資質、根機不足。165
但不可說的可能意義,除了以上五點外,還有一個可能的理
解向度,意即說「不可說」可能是為「說」所做之宣示,使得在
宣達深奧道理時,說者與聞者皆在心理上做好準備。尤其在擱置
宗教經驗或信仰層面的考量,純粹從哲學及理性的觀點,來思考
《老子》和《中論》的「不可說」時,其意義更可以是如此。直
言之,在語言策略的觀點下,不可言說本身也可以是種策略的運
用,此時不可說與權巧地說,皆可視為所運用的語言策略,如下
表所示:
語言策略
不可言說權巧地說
道家道不可言、不可名、
無名
正言若反、始制有名(強為之名)、
善言、貴言、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等
佛教空不可說、不欲說、
無所說
假名說、二諦說、中道說(說於中
道)、方便說、依義不依語等
就般若經教及中觀學而言,一切皆是假名施設而無有真實,166就連不可言說本身也是假名施設。《中觀論疏》所謂「凡一切言說皆是方便」167,或者所謂「一切言說皆是假」168的語言觀點,意也在此。而當不可說、不欲說也成為語言策略時,此時任何與不可說相關的敘述,如《老子》不可名、無名等,乃至相近的描繪,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以及「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惟恍惟惚」等,與《中論》之以「甚深微妙相」、「真實微妙法」來描
述佛法的深邃等,169就某個面向而言,亦可視為語言策略的運用。可知,無論是《老子》「惟恍惟惚」或者《中論》「甚深微妙」等語句的出現,皆可視為在表達深湛思想時,在語言策略上的巧妙安排。此似是要人有所警覺,莫停留在文字表面上的理解,也勿以僵化滯著的方式來認識,而要從中領會語言背後的深意。
2.說道者巧妙地說而聞道者靈敏地聽
如果不可言說本身也是種策略的運用,則目的應是要說道者巧妙地說、而聞道者靈敏地聽。細部分析,所謂之「不可說」,仍是因人而異的;因為一個理論(或一件事情)之所以很難理
解,除了理論本身極為深刻、一般人無法領悟外,也和講解此理論的人所使用的方式或技藝有關。換言之,說法、傳道的過程主要有三個條件:
一、傳道或說法的內容(即「道」或「法」)。
二、傳道或說法所憑藉的方式(如語言)。
三、傳道或說法的對象(即聽聞者)。
如果說道者能巧妙地說、而聞道者能靈敏地聽,即第二點與第三點能得到充分之改善,則第一點的可能限制即可減少。170如同好的解說者,能由淺入深、由簡入繁,甚至善用故事比喻來做引導。或者,換個方式說,正因為理論太過深奧,所以更需要以方便善巧的方式做宣說(skillful in expression)。而在佛、道二家思想中,似乎皆體會到這點,從而在甚深義理的背後,各自發展出一套獨特的言說策略,以此建構出各自的語言觀。因此,《老子》在「道可道非常道」之後,即以兩兩對演的方式,呈現其想說的,提出「正言若反」的言說方式,而此也成了理解其哲學的切入點之一。就《中論》思想而言,雖然佛陀悟道之初,默然不欲說法,而且以遮遣的方式遍破一切,既不言此、也不說彼,但在「善滅諸戲論」的同時,也注重方便權巧之施設,因此以二諦說、假名說等為其核心教導。
職是之故,雖然道家說「道不當名」、佛教言「空不可說」,但道家與佛教所留下的典籍卻也是汗牛充棟;其所謂的不可名、不可說背後的深意,仍值得再做思索。例如此處即點出一個可能的理解向度,即佛道間的不可言說本身已是一種表達方式,而可被視為某種言說策略的運用,其中所隱含的深意之一,似在於說與聽間的巧妙互動。即不只是要說道者巧妙地說,也要聽道者靈敏地聽,雙方皆能透過語言得其利卻不受其害。
(二)說是為了不說
如上所提,說「不可說」是為說做準備;但之所以說,卻又是以不說為終極目的,說乃是為了不說。此也意味著語言策略使用的最終目的,在於不用任何的策略。換言之,就《老子》和《中論》而言,道與涅槃的境界皆是無法言說的,《中論》的「無所說」、「離諸見」,以及《老子》的「不言之教」,皆是如此;但為了教化人達到此一境地,語言的運用乃是不可避免的手段。而一旦達到目的,一切皆離棄、止息,最終未嘗有言;171如果有所說,就還不是最高的境界。172
所以,《老子》標示出語言認識「道」的限制時,提出「不言」和「善言」兩種因應之道,其中「不言」可說是較高的境界。同樣地,《中論》之「佛亦無所說」,也表達出絕諸戲論的的高超境界。因此對《老子》和《中論》來說,甚至對整體道家和佛教思想而言,語言乃做為表達的方法或手段;而這樣的方法、手段,其本身並不等於目的,只是有助於達成目的而已。最終的目的在於傳遞訊息,使人有所領悟,如同標月之指、渡江之筏,一旦目的完成,這些工具即應拋棄,由是顯示出一定的教化意義。因此,兩者可說是在實用的脈絡(pragmatic context)底下,所發展出的言說策略,而未必僅是單純語言議題的探討(solely linguistic issue)。173
眾生所知,強調第一和三個條件。其中,兩者共同認為,所宣說之「道」或「法」是深奧難知的,只不過面對玄深的道理,《老子》指出了語言的限制,而《中論》提到的是眾生根機的不足,卻未必是語言的限制,由此可知兩者強調之重點略有不同。儘管如此,如何使用有限之語言,傳達玄之又玄的道,或者使鈍根眾生,領悟甚深法義,使得深妙的道理得以傳遞出去,成了《老子》和《中論》所共同關心的。
可知,宗教上的實踐面向也是兩者關心之所在,其中《中論》思想亦是如此。如同《中論》所說,佛陀說空的目的是破一切見,而破一切見後,並不是要復生空見為見,而是「空」之自身亦為「空」。174換言之,語言所展示的空義,是為勘除一切顛倒見,如此的語言並不為實,語言也是因緣所生、空無自性;而且正因為是性空如幻,才會有語言之作用,其才能有所遮破和顯立。關於此觀點,龍樹在《迴諍論》也做了清楚的表示。175龍樹指出,一切法皆緣起無自性空,語言亦是因緣所生(「我語亦因緣生」及「我語因緣和合而生」),故因緣生的語言,也是空無自性的;正因為語言空無自性,所以才能產生語言之作用(「空語世間受用」)。176此意味著語言間的運用,以及人世間一切的言行造作,如同幻化人之間的活動。語言的功用不過是以一個幻化不實,來指出另一個幻化不實,藉幻化來遮止幻化,其中的一切皆是幻化。177而後代禪門的「以楔出楔,將聲止聲」178、「黃葉止小兒啼」179,也說明相近之意境;即因為是以音聲佛事來將聲止聲,所以說本身也不能執著,或者其自身也是空的。180
總之,不管是《中論》的空、涅槃不可說,還是《老子》的「道常無名」,皆說明「道」或「空」是不可說的。雖然不可言說,但此時仍需藉由名言做為溝通的方便,因此《老子》說:「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而《中論》云:「但以假名說」,此皆是藉由一定的施設,來說此不可說的道理。而此藉名言而說的目的,仍在於不可說、無所說,以達到「無所說」或「大音希聲」、「行不言之教」之境地。181
(三)說與不說間不即不離
由於說是以不說為目的,終究是為了無所說,因此在說與無所說、語言策略與不可說之間,存在著不即不離的關係。如此之不即不離,也代表了《中論》與《老子》對於語言和道、空性間的看法。
在《老子》和《中論》裡,語言僅被視為體道的手段或工具,僅是一種策略性的運用以助於體道。而在語言策略和其目的之間,可能具有什麼樣的關係?在《老子》中,其既說「名可名非常名」、「道隱無名」,但也說「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同樣地,《中論》既提到「不說」、「不欲說」、「不可說」、「無所說」,但也提到諸佛依二諦說法及「但以假名說」。所以,在說與不說間,兩者都有其深思之處,也顯示了其間一定的關係。
首先,在《老子》部分,《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常道」,其中「道」一詞所含的兩個意涵,恰可說是相對的;如道用來指涉其哲學之核心要旨時,此「道」是不可知、不可言說的,如「道常無名」即說明此一道理。但「道」此一字詞的另一層意涵,即有「說」或「言」的意思,因此「道不可說」與「道就是說」兩者間形成某種張力,即「道」既不可說,但其本身卻又是說,多少顯示出《老子》思想的巧思所在。而在面對說與不說的弔詭所在時,《老子》似也提供線索,使助於「道」的理解。如先前曾分析過的,「道可道非常道」後緊接著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其中「有名萬物之母」,說明《老子》雖以「無名」來描繪道,但並沒有否定「有名」做為道的另一側面,名言之約定俗成的設立,在《老子》看來仍舊是必要的,因而強調有、無兩個面向並重來認識「道」。所以,就《老子》思想而言,一方面語言無法傳達「道」的境界,另一方面不透過語言,也無法領會「道」為何,因此「不可說之道」和「道之言說」間有著不即不離的關係。182
其次,在《中論》裡,一方面語言的虛構、擴張而形成戲論,從而成為須摧破止滅的對象;但另一方面,語言的方便施設、假名安立,藉由言說活動進行說法,又是不可避免的。如此
語言既可被掃蕩,亦可被安立,也顯示出對語言不即不離的觀點。此外,《中論》二諦的道理,說明不依俗諦則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可知涅槃、第一義是目的,相對於涅
槃、第一義之目的,世俗諦如同某種方便的手段,可有助於達成勝義的涅槃彼岸,因此勝義與世俗二諦間也可說是不即不離的。此時語言所示的教法乃是工具,當到達彼岸後「筏」是要放下的,顯示語言文字為悟道的方便法門。同樣地,道家「得意忘言」亦是把語言視為工具,且不能對此工具產生執著。如此,就佛教與道家而言,語言既是要被捨棄、被超越,同時也要被依靠、被仰賴,如此既依靠、又捨棄的關係,皆說明道與語言、勝義與世俗二諦間不即不離的關係。183
總之,綜合上述三點,即說不可說可視為是說之準備、說是為了不說,以及說與不說間不即不離,顯示出語言策略視域下,說與不可說間的微妙處。可知,語言策略雖在因應不可說,但就如同不可說本身存在著弔詭,語言策略的運用也隱含相似的特性。其中的第一點,所謂的不可說,可視為策略運用的一部分,其可能的意涵,即在於策略使用下敏捷地說,此時不可說並非全然不可說,而是要有技巧地說。就第二點而言,運用語言策略而說,雖使不可說在有限範圍內成為可說,但此可說仍是為了不可說(的道與空性),最後也須回到不(可)說做為終極目的。就第三點而言,從視說不可說為說之準備、及說是為了不說,可知說與不說、語言與道或空性間的不即不離、亦即亦離。但無論如何,有技巧、技藝地說,乃是語言策略所關注的重點。如同前面所分析的,兩者運用語言策略之技藝,就《老子》而言是正反對
演,就《中論》來說是既破且立;無論是正反對演或既破且立,其共通點皆是動態、靈活之特質,以下即說明之。
如「緒論」所說, B. K. Matilal曾指出中觀學派和道家使用了非常相近的語言,來表達他們想要說的話,150並認為此二者乃因而成為西方觀點下的東方神祕主義。151Matilal指出,在中觀學裡諸多語句的表達未必合於一般常理思路,甚至含有反邏輯、反理性的傾向,152而這樣的表達方式,在道家思想論述中也時而可見,例如《老子》首章「道可道非常道」,即表達了相近的意趣。由此觀點延伸而出,道家與中觀學派對於語言有著什麼樣共通的見解,便成了一個可以探討的課題。
以上諸節已分別討論《老子》與《中論》語言策略的思想概要;其中就《老子》部分,我們可依下列三個重點來理解:
一、「道」不可言說,可說即不是「道」。
二、以兩兩、正反對演的方式而說。
三、「正言若反」為其言說技藝之一。
可知《老子》首章揭示「道」之無限性以及語言表達「道」的有限性,因此如何運用有限的語言來展示無所限制的「道」,成了老學關心之重點。而為顯示「道」為何物,《老子》善於以兩兩對演的方式進行論述,似告訴我們「道」可以從世間的正反關係去理解。153就《中論》的部分,亦有下列三個重點:
一、佛所悟之法甚深難知而不欲說。
二、凡有所言說皆不是(破)。
三、但以二諦與假名方便教說之(立)。
因為佛法甚深而眾生計執太重,所以《中論》似採取「破」、「立」的兩手策略,既以「不說」、「不可說」、「無所說」破諸戲論計執,又以「二諦說」、「假名說」之方便開演來教化眾生。因此就《老子》和《中論》的語言策略或語言運用而言,前者善於以兩兩對演、正反思辨的方式來顯示「道」的深意,後者則以破、立兼施的兩面手法,輾轉交互運用,指引出佛法的歸趣。因此,關於《老子》與《中論》的語言策略,我們可以分別歸納出「正反」與「立破」之策略運用模式;而且,兩者所提出的語言策略,以及其本身所運用的語言策略,乃是一致的。154
根據以上之對比,初步可以同意Matilal所言,即《老子》和《中論》在某個面向上,用了相近的語言表達方式;尤其從《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等,以及《中論》以「不說」、「不可說」、「無所說」等,來標示任何的言說皆不是;就這點上,兩者在外在形式上,實有其一定的相似性。也因此,後代禪門「說似一物即不中」的名句,155究竟是繼承於佛教內部的思想、還是承接自道家的觀點,就難以確切分辨;可以說其既與《中論》的見解有關,卻也不離《老子》的看法。
但是,《老子》與《中論》語言策略背後的思想仍是明顯不同的。例如,《老子》的「正言若反」與《中論》的假名及二諦說,可以說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範疇,實際所談的內容及運用之模式也互有差異。兩者共同的交集,主要在於面對不可說的道理,所提出的策略性回應,如善用正反遮照的方式,以試著貼近其欲宣說的理論。簡言之,為了不可說之道,兩者有所謂正反、立破等語言策略之使用,並藉由這些策略、方法,去說那不可說之說(saying the unsayable)。
《老子》與《中論》兩者,在說不可說的同時,其所運用的語言策略有哪些共通點,以及不可說及語言策略的背後,可能表示著什麼樣的意義,也成了值得探討的問題。兩者同樣做為某種哲學或宗教,皆以智慧型態為其主軸,給予世人深刻的啟示;在宣說各自的智慧教示時,確有既說、又不說的共通之處,156從而顯示出外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暫且不論其智慧內容為何,157僅就語言表達的形式而言,對於展現智慧過程中,其間正反、立破語言策略運用的相似或共通處,及其所透顯出的意義,以下即列舉出五個小節做探討。
首先,兩者語言策略之運用,皆為了回應不可說。其次,在語言策略視域下,皆顯示說與不說的微妙與弔詭;即說不可說可視為說之準備,而之所以要說,又是為了不說,顯示出說與不說間之不即不離。第三,兩者之語言策略皆具有動態、靈巧之特質,使能不執著而善用語言、駕馭語言不被語言所誤。第四,關於策略之運用所引起的誤解,在此也做一討論與澄清。最後,小結以上之討論。以下即分別做說明。
一、以語言策略因應不可說
從語言策略入手,探討《老子》與《中論》的語言觀,乃是本研究的特點之一。語言策略的概念,乃與不可說相對,而道、佛哲學中不可說命題的強調,又是其中的特色,因此從語言策略掌握道、佛的語言觀或語言哲學,應是可嘗試的新進路。進言之,佛、道語言哲學的特色之一,乃是在實際運用、教化的層面上,展示出其獨特性。而此語用面向具體的展示之一,即是語言策略或技藝的運用。而且《老子》與《中論》不僅僅提出其語言策略的觀點,事實上也善用此語言策略來做表述,此點實不容二諦」之「破立」的語言策略,其本身也分別力行「正反」與「立破」的語言策略。換言之,兩者皆運用所提出來的語言策略,去表達哲學見解(包括語言策略),而且從《老子》「正反」與《中論》「立破」的語言策略,可知其本身已善於運用語言。
就《老子》與《中論》而言,兩者同樣面對不可說的道理;為了說此不可說,兩者皆開展出其語言策略及對語言的反思。對老子和龍樹來說,語言不能窮究對道與空性、涅槃的認識,但又不能不依靠語言;換言之,語言有一定的工具性價值,使能指向道或諸法實相的認識。因此,兩者所指出的未必全在於語言的限制,也包含了如何善用語言以宣說道理、教化世人。所以,不管是《老子》「正言若反」的正反對演,還是《中論》或說或不說、既立且破的兩面策略,兩者皆強調善用語言技藝,目的之一是為了避免執文害義,而能靈活以待。可知兩者在展示其智慧型態時,有著相近的論述手法。對於兩者在不說與說、不言與言(或不名與名)之間,我們可以就道、佛各自的語言特色,做下列的整理:
不可言說:
道家:
道不可言、不可名、無名
佛教:
空不可說、不欲說、無所說
權巧地說(語言策略):
道家:
正言若反、始制有名(強為之名)、善
言、貴言、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等
佛教:
假名說、二諦說、中道說(說於中
道)、方便說、依義不依語等
可知,道與空性不可說其中所隱含的意涵之一,可在於善用技藝而靈敏地說;即在不可說之餘,如何發揮語言策略以做因應,也是兩者哲學所關心的。因此,相對於西方學界慣以「神祕主義」(mysticism),或者超驗性(transcendental)的觀點,158以及「語言的限制」等,來理解東方哲學所謂的不可說,實際上「權巧地說」也是要傳達的訊息之一。或者,換個方式說,做為宗教實踐面向的老學和中觀學,所謂的不可說強調的主要是修證經驗上語言的非認知性;而做為哲學思辨面向的老學和中觀學,具有十足理智思辨的特質,所指的不可言說,背後應蘊含語言策略運用之必要。
二、語言策略視域下說與不可說間的微妙所在
「不可說」本身即存在一定的弔詭,此點除了古代哲學曾探討過外,在現今也有不少的討論。159若將此一課題的探討,引到語言策略的視域、脈絡下來檢視,或許能有新的啟發。例如,在語言策略的視域下,「說」固然是種語言策略,在此同時,說「不可說」彷彿也可以視為語言策略的運用。此外,在語言策略的觀點下,已使不可說在某個意義下成為可說,而這樣的說終極而言又是為了不(可)說,如此的輾轉交錯,也顯示出一種微妙與弔詭。以下即分三部分來談這些微妙處,即:一、說「不可說」可視為說之預備;二、說是為了不說;三、說與不說間不即不離。
(一)說「不可說」可視為說之預備
說「不可說」此不說之說,可視為一否定之說,即通過否定性的言說指出道、法的超越性與非概念性,此意味著別的言說方式行不通,而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除此之外,說「不可說」亦158 以超驗(transcendence)來理解佛教的宗教經驗,Asanga Tilakaratne也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原始佛教(Early Buddhism)的語言觀及實相觀,皆不是超驗式的,這點與其他的宗教截然有別。見Nirvana and Ineffability: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Theory of Reality and Language, Sri Lanka: University of Kelaniya,
1993, p. 9.
可視為說之準備,或者進而言之:當說一切法不可說時,可能是為說一切法,所做之準備;相近地,當說道不可說時,可能也是為表達道時,所做之準備。160
本文談《老子》和《中論》的語言策略,乃在於《老子》「道可道非常道」、「道常無名」以及佛陀「默然不欲說法」的理路脈絡下,所進行的探討。或者說,《老子》之所以會發展出
正言若反的言說方式,而《中論》會有無所說、假名說以及二諦等既立又破的語言策略,其間主要的理由,乃是在因應道不可道或空不可說的難處。如果道可輕易地被認識,或者涅槃與空性可以淺顯地被理解,則所謂的不可名、不欲說的宣稱即是多餘的。甚至,所謂的不可名、不欲說,也是其語言策略運用的手法之一,其用意似是為說做準備。如《老子》首章第一句話即說:「道可道非常道」,背後所蘊涵的巧思乃是耐人尋味。
既然有語言策略的運用,此時不可說的背後,可隱含其他可能的意義,而其中的意義之一,可以是為說做準備;因此在宣稱不可說時,本身似已是某種語言策略的使用。此外,所謂的不可說、不欲說,除了是為傳達深奧道理所做之宣示外,可能也是要說道者巧妙地說、聞道者靈敏地聽。關於這點,以下做進一步分析:
1.「不可說」本身也是語言策略
不論是道家思想或佛教哲學,兩者的哲理常為世人所重,而且在表達思想時,皆不約而同地宣稱其深邃難解。如《老子》首章從「道可道非常道」,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使得《老
子》的「道」,自古以來即如「謎」一樣般玄深難測。此外,佛法思想中心雖在於苦與苦的止息,但從不欲說、不可說、不可思議等的強調,也說明了佛教緣起、空與涅槃等法義的甚深。而正因為所要傳達的道理過於深奧,所以「不可言說」的觀點,便成了道家典籍及佛教經論兩家思想共同的特色。但說此不可說可能具有哪些意義?
如此的不可言說,若從不同的角度做分析,可能就有不同的看法。所謂的玄深,或反覆強調甚深微妙,其中有五種可能的用意如下:
一、指義理上的深邃難解。161
二、語言的局限性。162
三、宗教經驗上的不可傳達(如涅槃體驗)。163
四、信仰面向情感上的歸敬、讚仰。164
五、聞道者的資質、根機不足。165
但不可說的可能意義,除了以上五點外,還有一個可能的理
解向度,意即說「不可說」可能是為「說」所做之宣示,使得在
宣達深奧道理時,說者與聞者皆在心理上做好準備。尤其在擱置
宗教經驗或信仰層面的考量,純粹從哲學及理性的觀點,來思考
《老子》和《中論》的「不可說」時,其意義更可以是如此。直
言之,在語言策略的觀點下,不可言說本身也可以是種策略的運
用,此時不可說與權巧地說,皆可視為所運用的語言策略,如下
表所示:
語言策略
不可言說權巧地說
道家道不可言、不可名、
無名
正言若反、始制有名(強為之名)、
善言、貴言、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等
佛教空不可說、不欲說、
無所說
假名說、二諦說、中道說(說於中
道)、方便說、依義不依語等
就般若經教及中觀學而言,一切皆是假名施設而無有真實,166就連不可言說本身也是假名施設。《中觀論疏》所謂「凡一切言說皆是方便」167,或者所謂「一切言說皆是假」168的語言觀點,意也在此。而當不可說、不欲說也成為語言策略時,此時任何與不可說相關的敘述,如《老子》不可名、無名等,乃至相近的描繪,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以及「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惟恍惟惚」等,與《中論》之以「甚深微妙相」、「真實微妙法」來描
述佛法的深邃等,169就某個面向而言,亦可視為語言策略的運用。可知,無論是《老子》「惟恍惟惚」或者《中論》「甚深微妙」等語句的出現,皆可視為在表達深湛思想時,在語言策略上的巧妙安排。此似是要人有所警覺,莫停留在文字表面上的理解,也勿以僵化滯著的方式來認識,而要從中領會語言背後的深意。
2.說道者巧妙地說而聞道者靈敏地聽
如果不可言說本身也是種策略的運用,則目的應是要說道者巧妙地說、而聞道者靈敏地聽。細部分析,所謂之「不可說」,仍是因人而異的;因為一個理論(或一件事情)之所以很難理
解,除了理論本身極為深刻、一般人無法領悟外,也和講解此理論的人所使用的方式或技藝有關。換言之,說法、傳道的過程主要有三個條件:
一、傳道或說法的內容(即「道」或「法」)。
二、傳道或說法所憑藉的方式(如語言)。
三、傳道或說法的對象(即聽聞者)。
如果說道者能巧妙地說、而聞道者能靈敏地聽,即第二點與第三點能得到充分之改善,則第一點的可能限制即可減少。170如同好的解說者,能由淺入深、由簡入繁,甚至善用故事比喻來做引導。或者,換個方式說,正因為理論太過深奧,所以更需要以方便善巧的方式做宣說(skillful in expression)。而在佛、道二家思想中,似乎皆體會到這點,從而在甚深義理的背後,各自發展出一套獨特的言說策略,以此建構出各自的語言觀。因此,《老子》在「道可道非常道」之後,即以兩兩對演的方式,呈現其想說的,提出「正言若反」的言說方式,而此也成了理解其哲學的切入點之一。就《中論》思想而言,雖然佛陀悟道之初,默然不欲說法,而且以遮遣的方式遍破一切,既不言此、也不說彼,但在「善滅諸戲論」的同時,也注重方便權巧之施設,因此以二諦說、假名說等為其核心教導。
職是之故,雖然道家說「道不當名」、佛教言「空不可說」,但道家與佛教所留下的典籍卻也是汗牛充棟;其所謂的不可名、不可說背後的深意,仍值得再做思索。例如此處即點出一個可能的理解向度,即佛道間的不可言說本身已是一種表達方式,而可被視為某種言說策略的運用,其中所隱含的深意之一,似在於說與聽間的巧妙互動。即不只是要說道者巧妙地說,也要聽道者靈敏地聽,雙方皆能透過語言得其利卻不受其害。
(二)說是為了不說
如上所提,說「不可說」是為說做準備;但之所以說,卻又是以不說為終極目的,說乃是為了不說。此也意味著語言策略使用的最終目的,在於不用任何的策略。換言之,就《老子》和《中論》而言,道與涅槃的境界皆是無法言說的,《中論》的「無所說」、「離諸見」,以及《老子》的「不言之教」,皆是如此;但為了教化人達到此一境地,語言的運用乃是不可避免的手段。而一旦達到目的,一切皆離棄、止息,最終未嘗有言;171如果有所說,就還不是最高的境界。172
所以,《老子》標示出語言認識「道」的限制時,提出「不言」和「善言」兩種因應之道,其中「不言」可說是較高的境界。同樣地,《中論》之「佛亦無所說」,也表達出絕諸戲論的的高超境界。因此對《老子》和《中論》來說,甚至對整體道家和佛教思想而言,語言乃做為表達的方法或手段;而這樣的方法、手段,其本身並不等於目的,只是有助於達成目的而已。最終的目的在於傳遞訊息,使人有所領悟,如同標月之指、渡江之筏,一旦目的完成,這些工具即應拋棄,由是顯示出一定的教化意義。因此,兩者可說是在實用的脈絡(pragmatic context)底下,所發展出的言說策略,而未必僅是單純語言議題的探討(solely linguistic issue)。173
眾生所知,強調第一和三個條件。其中,兩者共同認為,所宣說之「道」或「法」是深奧難知的,只不過面對玄深的道理,《老子》指出了語言的限制,而《中論》提到的是眾生根機的不足,卻未必是語言的限制,由此可知兩者強調之重點略有不同。儘管如此,如何使用有限之語言,傳達玄之又玄的道,或者使鈍根眾生,領悟甚深法義,使得深妙的道理得以傳遞出去,成了《老子》和《中論》所共同關心的。
可知,宗教上的實踐面向也是兩者關心之所在,其中《中論》思想亦是如此。如同《中論》所說,佛陀說空的目的是破一切見,而破一切見後,並不是要復生空見為見,而是「空」之自身亦為「空」。174換言之,語言所展示的空義,是為勘除一切顛倒見,如此的語言並不為實,語言也是因緣所生、空無自性;而且正因為是性空如幻,才會有語言之作用,其才能有所遮破和顯立。關於此觀點,龍樹在《迴諍論》也做了清楚的表示。175龍樹指出,一切法皆緣起無自性空,語言亦是因緣所生(「我語亦因緣生」及「我語因緣和合而生」),故因緣生的語言,也是空無自性的;正因為語言空無自性,所以才能產生語言之作用(「空語世間受用」)。176此意味著語言間的運用,以及人世間一切的言行造作,如同幻化人之間的活動。語言的功用不過是以一個幻化不實,來指出另一個幻化不實,藉幻化來遮止幻化,其中的一切皆是幻化。177而後代禪門的「以楔出楔,將聲止聲」178、「黃葉止小兒啼」179,也說明相近之意境;即因為是以音聲佛事來將聲止聲,所以說本身也不能執著,或者其自身也是空的。180
總之,不管是《中論》的空、涅槃不可說,還是《老子》的「道常無名」,皆說明「道」或「空」是不可說的。雖然不可言說,但此時仍需藉由名言做為溝通的方便,因此《老子》說:「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而《中論》云:「但以假名說」,此皆是藉由一定的施設,來說此不可說的道理。而此藉名言而說的目的,仍在於不可說、無所說,以達到「無所說」或「大音希聲」、「行不言之教」之境地。181
(三)說與不說間不即不離
由於說是以不說為目的,終究是為了無所說,因此在說與無所說、語言策略與不可說之間,存在著不即不離的關係。如此之不即不離,也代表了《中論》與《老子》對於語言和道、空性間的看法。
在《老子》和《中論》裡,語言僅被視為體道的手段或工具,僅是一種策略性的運用以助於體道。而在語言策略和其目的之間,可能具有什麼樣的關係?在《老子》中,其既說「名可名非常名」、「道隱無名」,但也說「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同樣地,《中論》既提到「不說」、「不欲說」、「不可說」、「無所說」,但也提到諸佛依二諦說法及「但以假名說」。所以,在說與不說間,兩者都有其深思之處,也顯示了其間一定的關係。
首先,在《老子》部分,《老子》首章說「道可道非常道」,其中「道」一詞所含的兩個意涵,恰可說是相對的;如道用來指涉其哲學之核心要旨時,此「道」是不可知、不可言說的,如「道常無名」即說明此一道理。但「道」此一字詞的另一層意涵,即有「說」或「言」的意思,因此「道不可說」與「道就是說」兩者間形成某種張力,即「道」既不可說,但其本身卻又是說,多少顯示出《老子》思想的巧思所在。而在面對說與不說的弔詭所在時,《老子》似也提供線索,使助於「道」的理解。如先前曾分析過的,「道可道非常道」後緊接著說:「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其中「有名萬物之母」,說明《老子》雖以「無名」來描繪道,但並沒有否定「有名」做為道的另一側面,名言之約定俗成的設立,在《老子》看來仍舊是必要的,因而強調有、無兩個面向並重來認識「道」。所以,就《老子》思想而言,一方面語言無法傳達「道」的境界,另一方面不透過語言,也無法領會「道」為何,因此「不可說之道」和「道之言說」間有著不即不離的關係。182
其次,在《中論》裡,一方面語言的虛構、擴張而形成戲論,從而成為須摧破止滅的對象;但另一方面,語言的方便施設、假名安立,藉由言說活動進行說法,又是不可避免的。如此
語言既可被掃蕩,亦可被安立,也顯示出對語言不即不離的觀點。此外,《中論》二諦的道理,說明不依俗諦則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可知涅槃、第一義是目的,相對於涅
槃、第一義之目的,世俗諦如同某種方便的手段,可有助於達成勝義的涅槃彼岸,因此勝義與世俗二諦間也可說是不即不離的。此時語言所示的教法乃是工具,當到達彼岸後「筏」是要放下的,顯示語言文字為悟道的方便法門。同樣地,道家「得意忘言」亦是把語言視為工具,且不能對此工具產生執著。如此,就佛教與道家而言,語言既是要被捨棄、被超越,同時也要被依靠、被仰賴,如此既依靠、又捨棄的關係,皆說明道與語言、勝義與世俗二諦間不即不離的關係。183
總之,綜合上述三點,即說不可說可視為是說之準備、說是為了不說,以及說與不說間不即不離,顯示出語言策略視域下,說與不可說間的微妙處。可知,語言策略雖在因應不可說,但就如同不可說本身存在著弔詭,語言策略的運用也隱含相似的特性。其中的第一點,所謂的不可說,可視為策略運用的一部分,其可能的意涵,即在於策略使用下敏捷地說,此時不可說並非全然不可說,而是要有技巧地說。就第二點而言,運用語言策略而說,雖使不可說在有限範圍內成為可說,但此可說仍是為了不可說(的道與空性),最後也須回到不(可)說做為終極目的。就第三點而言,從視說不可說為說之準備、及說是為了不說,可知說與不說、語言與道或空性間的不即不離、亦即亦離。但無論如何,有技巧、技藝地說,乃是語言策略所關注的重點。如同前面所分析的,兩者運用語言策略之技藝,就《老子》而言是正反對
演,就《中論》來說是既破且立;無論是正反對演或既破且立,其共通點皆是動態、靈活之特質,以下即說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