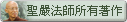商品圖片
知識與解脫:促成宗教轉化之體驗的藏傳佛教知識論
KNOWLEDGE AND LIBERATION: Tibetan Buddhist Epistemology in Support of Transformative Religious Experience
作者:安妮‧克萊因
出版社:法鼓文化
出版日期:2012年08月01日
語言:繁體中文
系列別:法鼓佛教學院譯叢
規格:25K / 平裝 / 383頁 / 單色印刷
商品編號:1111250011
ISBN:9789575985936
定價:NT$450
會員價:NT$383 (85折)
精采書摘
< 回商品頁第二章 達倉的「二諦」說
↑TOP
貫穿於格魯派所系統化的隨理行經量部二諦說內的主軸線是:徹底地肯定自相法、勝義諦、現量的所現境及無常法是同義詞。共相法、世俗諦、思維的所現境及常住法四項也是徹底的同義詞,上述兩個系列是截然二分的。
我們剛看過,「勝義諦」一範疇包括如桌、椅、樹等一般對象,以及組成這些蘊聚法的極微塵。格魯派此說是依法稱而立:「凡勝義地堪任力用者皆自相法,餘者乃共相法」。與達倉的看法相反的是章嘉,他認為法稱的論斷所提供的不是二諦的「性相」(梵:lakṣaṇa,藏:mtshan nyid),而是二諦的「名相」(梵:lakṣya,藏:mtshan gzhi)。章嘉認為,「勝義諦」的「性相」是:
依自住態,不依思維或名言的施設,而堪受正理抉擇。
這表示如桌、屋等一類對象,能夠憑藉它們作為一具有其自己「所住態」(藏:gnas lugs)的事物之體性與能耐,而顯現予現量;它們能夠在未經名言指涉或反映等之施設下而顯現。準此,格魯派主張,凡缺其本身的「所住態」者,就可說它是常住法、世俗諦及共相法。我們已經注意到:在格魯派經量部當中,自相法及常住法兩個範疇之間,是徹底互斥的;故凡存在,必定是二者居其一,而不能夠兩者皆是。
十五世紀早期的薩迦派學者達倉在宗喀巴身後數十年間寫下對法稱的不同詮釋,他對經量部二諦說有頗為不同的理解。依照達倉的看法,世親《俱舍論》的二諦說與法稱在《釋量論》內對自相、共相二法的解釋,提供了對真、俗二諦的平衡定義。世親說:
若一個對象(如瓶或水)被毀壞,或在思想上被分解後,就不會再被視作原先的對象,這就是世俗諦。
依照達倉的觀點,世親在此所謂的「世俗地存在的事物」,是指法稱所說的,除「勝義地堪任力用」以外的那些事物。同樣地,在世親的系統內,「勝義法」是指勝義諦及勝義地堪任力用者。反之,在應成派,勝義諦(即空性)既非勝義地,亦非真實地存在;空性在其「非實有性」這一點上,與所有其他事物無異。當然,「勝義法」之範疇所指的是:儘管在事物被物理地或概念地分解之際,「與義相應心」(梵:anvartha-buddhi,藏:blo don mthun)仍可繼續以原物(譯按:分解之前)作為所緣取的對象,而進行認知。
達倉與格魯派不同的是,他聲稱世親與法稱二諦說之間只是用詞不同,而不是定義不同,所以他沒有劃分隨理行經量部及隨教行經量部。達倉在其主要著作《宗義》(譯者按:書名全稱是《解一切宗義離邊之善說海》)內並沒有提過這種劃分,故前述的主張或許是格魯派的獨門理論。再者,達倉肯定經量部與毘婆沙師一樣,都認為只有物質中的無方分極微塵及不可分剎那識才是勝義諦。達倉依此認定:由於如桌等事物是世俗地作用,所以它們是由自相法所組成。同時,他指出藉著把它們稱為共相法,使它們成為蘊聚。根據達倉,蘊聚永遠不是自相法或勝義諦。這種看法衍生自達倉對法稱頌文的詮釋:唯「勝義地堪任力用」者才是自相法或勝義諦。於是達倉便在格魯派的詮釋上挑毛病,與格魯派針鋒相對,達倉主張,桌、椅及其他粗分的無常事物既不是勝義諦,也不是自相法。桌、椅等是「無常的共相法」(藏:dngos por gyur pa’i spyi mtshan),因為它們是「不堪任於勝義地起力用」。當然,桌、椅等是「世俗地堪任原因的角色與力用,進而還能生起能緣取(譯按:無常的共相法)的識」。
第一節 無常的共相法
達倉為了將「蘊聚所成無常法」納入他的二諦說,他發明出「具力用的共相法」之範疇。故此,達倉不接受格魯派隨理行經量部的假定,即:沒有一法既是共相法,又是有力用的事物,因為這二者是徹底互斥的。達倉提出這範疇就表示他不接受一切無常法都是自相的,例如「瓶」等項目可被視為「具力用的共相法」(藏:dngos por gyur pa’i spyi mtshan,譯按:本來依照藏文,理應譯作「成為實有(dngos po)的共相」,但作者在此及上一段卻分别用上兩個不同的英譯,分别是impermanent及functioning,今依英譯。譯者感謝陳又新博士指出這一點)。
為確立他自己詮釋的正確性,達倉必須解釋為什麽法稱似乎接受無常法(堪任力用者)及自相法二者是同義的。
事實上,格魯派學者嘉木樣就是引述該頌文以支持他的立論;對法稱來說,自相法及無常法是徹底互相涵攝的,即:舉凡是此也就是彼,因此桌、椅等既是自相法,故亦是勝義諦:
凡堪任力用者,皆具其自相。
在達倉身後兩百餘年,嘉木樣在其著作一步推論:達倉引用法稱這頌文作為證明(似乎是一個精確的意譯,但不是一真正的引述),乃是他「自暴其短」之舉。也就是說這位薩迦派學者或他的支持者並沒有提出一個在詮釋上能自圓其說、言之成理的滿意答案。當然,達倉確有談到這一點。他引述了法稱用「勝義地」一詞來規定「堪任力用」:
凡於此能勝義地堪任力用者,是勝義地存在;其餘是世俗地存在。此謂之自相(法)及共相(法)。
達倉堅稱,對法稱來說,只有那些勝義地堪任力用的事物才是自相法或勝義諦。一切具力用法或無常法等皆不屬於這個範疇。達倉寫道:
(法稱謂):「凡是堪任力用……」的段落加上「勝義地」之簡別,很明顯是用來統合出現在前、後不同處頌文的意義。
達倉把這必要性擴大,並聲稱透過義理上的綜合,把同一部文本內的不同文句變得合情合理乃是刻不容緩:
……提出的闡釋必定要兼顧任何文本中前後全體的安排,若只斷章地依文解義,會招惹出很多內在矛盾。
包括格魯派在內的所有釋義家都同意,必須依上文下理為脈絡來解讀特定文句。故達倉宣布了一條每人都同意的詮釋學(hermeneutical)原則;然而,這不表示所有人都會得出相同甚或相近的結論。
達倉運用文本綜合的方式把法稱對「自相法」的解釋規定為專指「勝義地堪任力用者」,並建立這一解釋的適切性。縱使「勝義地」一語未見之於上述所引的第一個句子,但卻見於他處,而達倉連結這兩個句子的方法,是把副詞「勝義地」用於兩者身上。
為著進一步確立他的詮釋,達倉擴大「勝義地」一語的意義重要性。他論證道,法稱利用這詞區分「勝義地具力用的事物」(如極微塵等)與「世俗地具力用的事物」(例如可被直接認知的桌、椅及所有其他蘊聚所成的無常事物)。色法極微塵所起的「勝義力用」是進行積聚,以形成無常法,即「具力用的共相法」。這些蘊聚物世俗地起力用,如盛水、托書等。
達倉及格魯派都同意,「自相法」對於勝義識來說,是起著「所緣緣」的力用。也許可想像對達倉來說,儘管聚成粗分境的那些個別微塵,既不是在視覺上可相分離,亦在時、地或體性上不相混,但這些微塵所組成的粗分境確實是以一種混合的方式顯現出來。例如,一張椅子代表了位置的混合,因為儘管左邊不是右邊,但椅子是由兩邊並成。同樣地,椅子世俗地存在於一段時間內,從昨日伸延到明日,並且椅子的體性遍布於從頂到底。椅子依此落實了時、空及體性的混和。故此,根據達倉,椅子及蘊聚所成的所有其他無常法,皆是具力用的共相法。這些蘊聚所成的無常法沒有勝義地起力用(若它們是這樣,則它們必定是自相法),它們只是世俗地起力用。
格魯派學者們如昂旺班丹、丹達拉讓巴、章嘉及貢覺晉美旺波皆不會把「堪任力用」劃分為世俗及勝義兩類。他們都主張法稱是在與中觀師對諍的脈絡下使用「勝義地」一詞,以求遮破中觀師的立論,即:事物只是世俗地,而非勝義地堪任力用。格魯派認為,經量部在這課題上是透過強調自相法勝義地起力用,指出經部與中觀見地之間的分歧。例如在昂旺班丹的《四宗義世俗及勝義解》(Grub mtha’ bzhi’i lugs gyi kun rdzob dang don dam pa’i don rnam par bshad pa),引述賈曹傑《善顯解脫道》(THar lam gsal byed)的頌文:
(法稱)說,(在第三品第三頌)加「勝義」簡別的目的是破斥那些(如中觀師)持只能世俗地堪任力用之錯誤見地。
昂旺班丹則注意到達倉的「具力用的共相法」之範疇與法稱的另一句說話相違:
因為它只是所詮境,它不是具力用的事物。
昂旺班丹視此為法稱「共相法不具力用」論點之證據。故他作如下結論呼應賈曹傑:
於「勝義地堪任力用」一句加「勝義地」之簡別的目的,乃是用以破斥無體論(中觀師)之論斷:(事物)只是世俗地堪任力用;然而它不是用作促成勝義及世俗二者俱堪任力用。
簡而言之,格魯派學者們及達倉雙方對法稱使用「勝義地」一詞的說明都各有法度。對達倉來說,「勝義地」一語指那些世俗地具力用的事物,以此來證成他對「具力用的共相法」(藏:dngas por gyur pa’i spyi mtshan)之範疇的應用。格魯派則論證「勝義地」根本就是用來對抗中觀師有關世俗力用之觀點。
格魯派也透過質疑法稱著作的藏文譯本內「勝義地」一語的真確性(authenticity)來支援他們的立場。昂旺班丹引述克主傑的講法,班(藏:dpang)譯師提及過原梵本並無「勝義地」一詞。在這情況下,梵文只是讀成:
arthakriyāsamartham yat
tad atra paramārthasat
(事物只是世俗地,而不是勝義地堪任力用。)
克主傑也引述十四世紀西藏譯師羅卓丹巴(bLo gros brtan pa, 1276-1342)的意見,指述詞「勝義」(paramartha)未見之於梵本。克主傑還進一步注意到,勝義地堪任力用(藏:don dam don byed nus pa)一語也未見之於法稱的其他任何著作。
然而無論如何,格魯派主要不是據「勝義地」一語的可疑地位來反駁達倉,卻毋寧是據格魯派對該詞語的自宗詮釋,並以有利於格魯派立場的法稱其他篇章為據。於是討論的真正焦點遂變為,根據法稱的文本,那一類的事物才被視為「勝義地堪任力用」,卻完全不是要討論法稱是否有用過「勝義地」一語。
達倉注意到法稱用「唯事」(梵:vastumātra,藏:dngos po dag pa ba)一詞指例如極微塵等,並把它們從微塵所組成的蘊聚等其他無常法中區分出來,因而這些蘊聚既非自相法,亦非「唯事」。
達倉也引述法稱門人帝釋慧(Devendrabuddhi)來支持他的觀點,認為經量部所奉行的法稱《釋量論》(像隨理行經量部)二諦說與分别說部是一致的:
它到底是世俗地存在如水、奶等,或是勝義地存在如色、愉快等?
達倉認為水、瓶等是世俗有,因為它們不堪任於生起勝義境之力用,即不堪任於作為「勝義心」的「所緣緣」。對達倉的系統來說,能知覺一張椅子的心智並非勝義的,因為用「微塵蘊聚」來稱謂一張椅子,這根本就是心智對原子聚合的施設。唯有蘊聚內的極微塵,而不是一張椅子,才會勝義地起力用。故這些「蘊聚所成法」是「世俗事物,即依待於如命名(梵:saṃketa,藏:brda)一類的內在心智因素而成的意識現象」。對達倉來說,微塵蘊聚所成的整體不是真實的,它們只是思維施設。唯有被施設的事物(如桌、椅)的依處(即極微塵)才是勝義諦及堪任勝義力用。
法稱門人帝釋慧在其疏釋中指出,例如像牛奶或水之蘊聚所成的事物是世俗地存在。達倉引述這一句文,是企圖根據法稱來支持他對世俗諦及勝義諦的自宗詮釋。嘉木樣在其《宗義廣釋》內公開挑戰達倉,堅持在上述引文中,帝釋慧所列述的是毘婆沙師及隨教行經量部的共同見解,但卻不是隨理行經量部的觀點。
法稱還有一句對達倉及格魯派雙方立場來說都是重要的話可供考慮。達倉就事物的「可堪任性」引述法稱,見〈現量〉(pratyakṣa)章第三的第五頌,下文達倉的閱讀加上「勝義地」;而格魯派的閱讀則否:
若說一切自相法及共相法皆同具生起自果的力用,則(勝義地講)這不是實情,因為看不出共相法的出現與否,是否(勝義地)具有力用,生起如眼等能緣取共相法之心的效果。
對達倉來說,法稱在此以「對象產生或生起能量識的能耐」為準來問,自相法及共相法,即常住法及無常法,有否勝義地生起力用。達倉認為法稱所說的,共相法沒有能力可勝義地生起能認知共相法的識,這是「不合實情」,儘管在達倉的系統,「如眼、色等」也不是勝義地具有力用,然而它們是世俗地具有力用。故此,對達倉來說,「眼及色」是具力用的共相法的實例。再者,在印藏的因明及辯論的三支論式的語言中,達倉視這類共相法為「隨順喻」或「同喻」(梵:sadṛṣtānta,藏:mthun dpe)。達倉的推論是:若法稱的意思是指那些全無力用,甚至是世俗地全無力用)的東西,他理應採一個毫不含糊的「無力用」實例,如「兔角,不堪生起能取識」。反之法稱所採用的卻是具有「世俗力用」的例子,藉此只排除無方分微塵等所具的「勝義力用」義。
格魯派則視「如眼及色等(生起)心……」一頌句為反例或「異喻」(梵:asadṛṣtānta,藏:mi mthun dpe),即眼、色不是共相法一個實例。但昂旺班丹所代表的格魯派觀點卻認為:事實上法稱這一句正好是削弱,而非支持達倉的立場。昂旺班丹的解釋是,當法稱說:「若謂一切皆有能生自果的力用」時,他是要從「共相法不生果」的觀點指出這是一錯誤的論斷。故他和一般格魯派的立場都認為:
「如眼、色等生能緣取它們的心」一句是異品周遍 (梵:vyatirekavyāpti,藏:ldog khyab)的證明,指沒有共相法有力用,故定為異喻。
從而昂旺班丹稱正量永不會見到共相法起力用;故這些共相法不會扮演原因,來生起認知共相法的心識。
一、無常法如何生起力用﹖
達倉堅持,無常法(如桌子)不是勝義諦,卻只是思維所施設,並因而不堪任於勝義地具力用。故此,雖然達倉及格魯派的學者們都同意,對勝義識來說,心智所施設的事物,並不能起「因緣」的力用之原則,但達倉卻將一切極微塵所成的蘊聚事物,皆納入名言施設的事物之範疇中。然而,格魯派對此是不認同的。
「起力用」就是指「生起果」。無常法以兩種途徑生起果:首先,無常法生出它們自己相續串的下一剎那;其次,無常法又擔當「因緣」,生起能緣取無常法之識。在此一脈絡下,達倉指出:由眾多部分聚合而成的事物不能勝義地生起能認知它之識,因為這些事物只是意識的施設。總而言之,個別極微塵是心所施設的整體事物(如椅、瓶)的存在所依處,這些整體事物不離於個別微塵。格魯派雖然同意這一點,但格魯派也會說:各部分的聚合(即整體事物)是(例如)椅子,從而這聚合和極微塵本身相較,並未更加有賴於思維所施設。從格魯派的觀點來看,極微塵所成的蘊聚事物(即椅子本身)把其相投予眼識,從而成為生起勝義識的「因緣」。故把其相狀投予眼識的「所現境」(藏:snang yul)是指這整張椅子,而不只是它的各個部分。
反之,達倉強調只有極微塵(即無常法內的無方分)才是現量的所現境。只有極微塵,而不是被施設的整體(whole)事物,才真正把其相投予識。每一項事物全屬思維所虛構。循這思路,達倉強調:人類作為整體事物的認知者,從生活到工作,都是在一個幾乎完全是唯概念地建構的國度當中。達倉批評格魯派沒有公平地對待經量部的細緻與敏銳,因為他們主張經量部把粗分境視作勝義諦,但實際上即使連毘婆沙師也不會這樣看。格魯派可對此的回應是:極微塵蘊聚的意思不外就是「椅」或「壺」,而這就是格魯派經量部的勝義諦,格魯派與達倉巴都一樣,不願以與極微塵分離的另一整體實物作為假名所依。故此,昂旺班丹在他對嘉木樣的《註解》中提到:
以下的立論被評為不妥:首先,認為「壺」是生自與壺的諸部分是異體之另一整體物;其次,認為能緣取「拿、坐等行動」的概念心生起自與壺等是異體的另一系列活動。
這說明格魯派視整體事物(whole,如「壺」)不外是極微塵的蘊聚,而不是什麽另外的東西,因而一項整體事物(與其諸部分)就是一體(梵:ekadravya,藏:rdzas gcig)。或以另一種方式來說,例如用於澆水的壺被視為一蘊聚成的事物,而不是一自立的實體。
儘管達倉及格魯派學者們都同意:一項整體事物不是外於其本身各别部分的另一自立體,但達倉仍把一項整體物(如一個壺)理解為唯思維所施設,而格魯派論師則保持相反的見解。因此,雖然格魯派所述的隨理行經量部都視壺等為勝義諦,他們卻不因而較毘婆沙師在存有論上賦予這些實物更重要的地位。毘婆沙師所以會把世俗諦詮釋為實事有(藏:rdzas su grub pa),這是因為它們具有自立體的一切意涵,而這對隨理行經量部而言是勝義諦或自相法。這一系的經量部稱粗分無常法(如「壺」)為勝義諦,而毘婆沙師則稱之為世俗諦,但此一事實仍不會成為判定毘婆沙師高於經量部的决定性證據。此外,經量部會把它們施設為假有,但毘婆沙師卻不會這樣。我們剛看到,經量部所講的世俗諦(例如「虛空無為」)並沒有本身自足實體的施設有。經量部的二諦說,還進一步有更細緻的涵義:當中能包含著「無遮」(藏:med dgag)在內的一類否定性概念,即不能自足的實物。據毘婆沙師,所有世俗諦及勝義諦皆是實事有(藏:rdzas su grub pa);因而,即使「遮遣」也是以這種方式被確立,所以毘婆沙師完全無法確立「無遮」的存在,因為無遮既不是實事有(藏:rdzas su grub pa),而無遮本身也不具有自足(藏:rang rkya ba)的實體。
我們剛看過,「勝義諦」一範疇包括如桌、椅、樹等一般對象,以及組成這些蘊聚法的極微塵。格魯派此說是依法稱而立:「凡勝義地堪任力用者皆自相法,餘者乃共相法」。與達倉的看法相反的是章嘉,他認為法稱的論斷所提供的不是二諦的「性相」(梵:lakṣaṇa,藏:mtshan nyid),而是二諦的「名相」(梵:lakṣya,藏:mtshan gzhi)。章嘉認為,「勝義諦」的「性相」是:
依自住態,不依思維或名言的施設,而堪受正理抉擇。
這表示如桌、屋等一類對象,能夠憑藉它們作為一具有其自己「所住態」(藏:gnas lugs)的事物之體性與能耐,而顯現予現量;它們能夠在未經名言指涉或反映等之施設下而顯現。準此,格魯派主張,凡缺其本身的「所住態」者,就可說它是常住法、世俗諦及共相法。我們已經注意到:在格魯派經量部當中,自相法及常住法兩個範疇之間,是徹底互斥的;故凡存在,必定是二者居其一,而不能夠兩者皆是。
十五世紀早期的薩迦派學者達倉在宗喀巴身後數十年間寫下對法稱的不同詮釋,他對經量部二諦說有頗為不同的理解。依照達倉的看法,世親《俱舍論》的二諦說與法稱在《釋量論》內對自相、共相二法的解釋,提供了對真、俗二諦的平衡定義。世親說:
若一個對象(如瓶或水)被毀壞,或在思想上被分解後,就不會再被視作原先的對象,這就是世俗諦。
依照達倉的觀點,世親在此所謂的「世俗地存在的事物」,是指法稱所說的,除「勝義地堪任力用」以外的那些事物。同樣地,在世親的系統內,「勝義法」是指勝義諦及勝義地堪任力用者。反之,在應成派,勝義諦(即空性)既非勝義地,亦非真實地存在;空性在其「非實有性」這一點上,與所有其他事物無異。當然,「勝義法」之範疇所指的是:儘管在事物被物理地或概念地分解之際,「與義相應心」(梵:anvartha-buddhi,藏:blo don mthun)仍可繼續以原物(譯按:分解之前)作為所緣取的對象,而進行認知。
達倉與格魯派不同的是,他聲稱世親與法稱二諦說之間只是用詞不同,而不是定義不同,所以他沒有劃分隨理行經量部及隨教行經量部。達倉在其主要著作《宗義》(譯者按:書名全稱是《解一切宗義離邊之善說海》)內並沒有提過這種劃分,故前述的主張或許是格魯派的獨門理論。再者,達倉肯定經量部與毘婆沙師一樣,都認為只有物質中的無方分極微塵及不可分剎那識才是勝義諦。達倉依此認定:由於如桌等事物是世俗地作用,所以它們是由自相法所組成。同時,他指出藉著把它們稱為共相法,使它們成為蘊聚。根據達倉,蘊聚永遠不是自相法或勝義諦。這種看法衍生自達倉對法稱頌文的詮釋:唯「勝義地堪任力用」者才是自相法或勝義諦。於是達倉便在格魯派的詮釋上挑毛病,與格魯派針鋒相對,達倉主張,桌、椅及其他粗分的無常事物既不是勝義諦,也不是自相法。桌、椅等是「無常的共相法」(藏:dngos por gyur pa’i spyi mtshan),因為它們是「不堪任於勝義地起力用」。當然,桌、椅等是「世俗地堪任原因的角色與力用,進而還能生起能緣取(譯按:無常的共相法)的識」。
第一節 無常的共相法
達倉為了將「蘊聚所成無常法」納入他的二諦說,他發明出「具力用的共相法」之範疇。故此,達倉不接受格魯派隨理行經量部的假定,即:沒有一法既是共相法,又是有力用的事物,因為這二者是徹底互斥的。達倉提出這範疇就表示他不接受一切無常法都是自相的,例如「瓶」等項目可被視為「具力用的共相法」(藏:dngos por gyur pa’i spyi mtshan,譯按:本來依照藏文,理應譯作「成為實有(dngos po)的共相」,但作者在此及上一段卻分别用上兩個不同的英譯,分别是impermanent及functioning,今依英譯。譯者感謝陳又新博士指出這一點)。
為確立他自己詮釋的正確性,達倉必須解釋為什麽法稱似乎接受無常法(堪任力用者)及自相法二者是同義的。
事實上,格魯派學者嘉木樣就是引述該頌文以支持他的立論;對法稱來說,自相法及無常法是徹底互相涵攝的,即:舉凡是此也就是彼,因此桌、椅等既是自相法,故亦是勝義諦:
凡堪任力用者,皆具其自相。
在達倉身後兩百餘年,嘉木樣在其著作一步推論:達倉引用法稱這頌文作為證明(似乎是一個精確的意譯,但不是一真正的引述),乃是他「自暴其短」之舉。也就是說這位薩迦派學者或他的支持者並沒有提出一個在詮釋上能自圓其說、言之成理的滿意答案。當然,達倉確有談到這一點。他引述了法稱用「勝義地」一詞來規定「堪任力用」:
凡於此能勝義地堪任力用者,是勝義地存在;其餘是世俗地存在。此謂之自相(法)及共相(法)。
達倉堅稱,對法稱來說,只有那些勝義地堪任力用的事物才是自相法或勝義諦。一切具力用法或無常法等皆不屬於這個範疇。達倉寫道:
(法稱謂):「凡是堪任力用……」的段落加上「勝義地」之簡別,很明顯是用來統合出現在前、後不同處頌文的意義。
達倉把這必要性擴大,並聲稱透過義理上的綜合,把同一部文本內的不同文句變得合情合理乃是刻不容緩:
……提出的闡釋必定要兼顧任何文本中前後全體的安排,若只斷章地依文解義,會招惹出很多內在矛盾。
包括格魯派在內的所有釋義家都同意,必須依上文下理為脈絡來解讀特定文句。故達倉宣布了一條每人都同意的詮釋學(hermeneutical)原則;然而,這不表示所有人都會得出相同甚或相近的結論。
達倉運用文本綜合的方式把法稱對「自相法」的解釋規定為專指「勝義地堪任力用者」,並建立這一解釋的適切性。縱使「勝義地」一語未見之於上述所引的第一個句子,但卻見於他處,而達倉連結這兩個句子的方法,是把副詞「勝義地」用於兩者身上。
為著進一步確立他的詮釋,達倉擴大「勝義地」一語的意義重要性。他論證道,法稱利用這詞區分「勝義地具力用的事物」(如極微塵等)與「世俗地具力用的事物」(例如可被直接認知的桌、椅及所有其他蘊聚所成的無常事物)。色法極微塵所起的「勝義力用」是進行積聚,以形成無常法,即「具力用的共相法」。這些蘊聚物世俗地起力用,如盛水、托書等。
達倉及格魯派都同意,「自相法」對於勝義識來說,是起著「所緣緣」的力用。也許可想像對達倉來說,儘管聚成粗分境的那些個別微塵,既不是在視覺上可相分離,亦在時、地或體性上不相混,但這些微塵所組成的粗分境確實是以一種混合的方式顯現出來。例如,一張椅子代表了位置的混合,因為儘管左邊不是右邊,但椅子是由兩邊並成。同樣地,椅子世俗地存在於一段時間內,從昨日伸延到明日,並且椅子的體性遍布於從頂到底。椅子依此落實了時、空及體性的混和。故此,根據達倉,椅子及蘊聚所成的所有其他無常法,皆是具力用的共相法。這些蘊聚所成的無常法沒有勝義地起力用(若它們是這樣,則它們必定是自相法),它們只是世俗地起力用。
格魯派學者們如昂旺班丹、丹達拉讓巴、章嘉及貢覺晉美旺波皆不會把「堪任力用」劃分為世俗及勝義兩類。他們都主張法稱是在與中觀師對諍的脈絡下使用「勝義地」一詞,以求遮破中觀師的立論,即:事物只是世俗地,而非勝義地堪任力用。格魯派認為,經量部在這課題上是透過強調自相法勝義地起力用,指出經部與中觀見地之間的分歧。例如在昂旺班丹的《四宗義世俗及勝義解》(Grub mtha’ bzhi’i lugs gyi kun rdzob dang don dam pa’i don rnam par bshad pa),引述賈曹傑《善顯解脫道》(THar lam gsal byed)的頌文:
(法稱)說,(在第三品第三頌)加「勝義」簡別的目的是破斥那些(如中觀師)持只能世俗地堪任力用之錯誤見地。
昂旺班丹則注意到達倉的「具力用的共相法」之範疇與法稱的另一句說話相違:
因為它只是所詮境,它不是具力用的事物。
昂旺班丹視此為法稱「共相法不具力用」論點之證據。故他作如下結論呼應賈曹傑:
於「勝義地堪任力用」一句加「勝義地」之簡別的目的,乃是用以破斥無體論(中觀師)之論斷:(事物)只是世俗地堪任力用;然而它不是用作促成勝義及世俗二者俱堪任力用。
簡而言之,格魯派學者們及達倉雙方對法稱使用「勝義地」一詞的說明都各有法度。對達倉來說,「勝義地」一語指那些世俗地具力用的事物,以此來證成他對「具力用的共相法」(藏:dngas por gyur pa’i spyi mtshan)之範疇的應用。格魯派則論證「勝義地」根本就是用來對抗中觀師有關世俗力用之觀點。
格魯派也透過質疑法稱著作的藏文譯本內「勝義地」一語的真確性(authenticity)來支援他們的立場。昂旺班丹引述克主傑的講法,班(藏:dpang)譯師提及過原梵本並無「勝義地」一詞。在這情況下,梵文只是讀成:
arthakriyāsamartham yat
tad atra paramārthasat
(事物只是世俗地,而不是勝義地堪任力用。)
克主傑也引述十四世紀西藏譯師羅卓丹巴(bLo gros brtan pa, 1276-1342)的意見,指述詞「勝義」(paramartha)未見之於梵本。克主傑還進一步注意到,勝義地堪任力用(藏:don dam don byed nus pa)一語也未見之於法稱的其他任何著作。
然而無論如何,格魯派主要不是據「勝義地」一語的可疑地位來反駁達倉,卻毋寧是據格魯派對該詞語的自宗詮釋,並以有利於格魯派立場的法稱其他篇章為據。於是討論的真正焦點遂變為,根據法稱的文本,那一類的事物才被視為「勝義地堪任力用」,卻完全不是要討論法稱是否有用過「勝義地」一語。
達倉注意到法稱用「唯事」(梵:vastumātra,藏:dngos po dag pa ba)一詞指例如極微塵等,並把它們從微塵所組成的蘊聚等其他無常法中區分出來,因而這些蘊聚既非自相法,亦非「唯事」。
達倉也引述法稱門人帝釋慧(Devendrabuddhi)來支持他的觀點,認為經量部所奉行的法稱《釋量論》(像隨理行經量部)二諦說與分别說部是一致的:
它到底是世俗地存在如水、奶等,或是勝義地存在如色、愉快等?
達倉認為水、瓶等是世俗有,因為它們不堪任於生起勝義境之力用,即不堪任於作為「勝義心」的「所緣緣」。對達倉的系統來說,能知覺一張椅子的心智並非勝義的,因為用「微塵蘊聚」來稱謂一張椅子,這根本就是心智對原子聚合的施設。唯有蘊聚內的極微塵,而不是一張椅子,才會勝義地起力用。故這些「蘊聚所成法」是「世俗事物,即依待於如命名(梵:saṃketa,藏:brda)一類的內在心智因素而成的意識現象」。對達倉來說,微塵蘊聚所成的整體不是真實的,它們只是思維施設。唯有被施設的事物(如桌、椅)的依處(即極微塵)才是勝義諦及堪任勝義力用。
法稱門人帝釋慧在其疏釋中指出,例如像牛奶或水之蘊聚所成的事物是世俗地存在。達倉引述這一句文,是企圖根據法稱來支持他對世俗諦及勝義諦的自宗詮釋。嘉木樣在其《宗義廣釋》內公開挑戰達倉,堅持在上述引文中,帝釋慧所列述的是毘婆沙師及隨教行經量部的共同見解,但卻不是隨理行經量部的觀點。
法稱還有一句對達倉及格魯派雙方立場來說都是重要的話可供考慮。達倉就事物的「可堪任性」引述法稱,見〈現量〉(pratyakṣa)章第三的第五頌,下文達倉的閱讀加上「勝義地」;而格魯派的閱讀則否:
若說一切自相法及共相法皆同具生起自果的力用,則(勝義地講)這不是實情,因為看不出共相法的出現與否,是否(勝義地)具有力用,生起如眼等能緣取共相法之心的效果。
對達倉來說,法稱在此以「對象產生或生起能量識的能耐」為準來問,自相法及共相法,即常住法及無常法,有否勝義地生起力用。達倉認為法稱所說的,共相法沒有能力可勝義地生起能認知共相法的識,這是「不合實情」,儘管在達倉的系統,「如眼、色等」也不是勝義地具有力用,然而它們是世俗地具有力用。故此,對達倉來說,「眼及色」是具力用的共相法的實例。再者,在印藏的因明及辯論的三支論式的語言中,達倉視這類共相法為「隨順喻」或「同喻」(梵:sadṛṣtānta,藏:mthun dpe)。達倉的推論是:若法稱的意思是指那些全無力用,甚至是世俗地全無力用)的東西,他理應採一個毫不含糊的「無力用」實例,如「兔角,不堪生起能取識」。反之法稱所採用的卻是具有「世俗力用」的例子,藉此只排除無方分微塵等所具的「勝義力用」義。
格魯派則視「如眼及色等(生起)心……」一頌句為反例或「異喻」(梵:asadṛṣtānta,藏:mi mthun dpe),即眼、色不是共相法一個實例。但昂旺班丹所代表的格魯派觀點卻認為:事實上法稱這一句正好是削弱,而非支持達倉的立場。昂旺班丹的解釋是,當法稱說:「若謂一切皆有能生自果的力用」時,他是要從「共相法不生果」的觀點指出這是一錯誤的論斷。故他和一般格魯派的立場都認為:
「如眼、色等生能緣取它們的心」一句是異品周遍 (梵:vyatirekavyāpti,藏:ldog khyab)的證明,指沒有共相法有力用,故定為異喻。
從而昂旺班丹稱正量永不會見到共相法起力用;故這些共相法不會扮演原因,來生起認知共相法的心識。
一、無常法如何生起力用﹖
達倉堅持,無常法(如桌子)不是勝義諦,卻只是思維所施設,並因而不堪任於勝義地具力用。故此,雖然達倉及格魯派的學者們都同意,對勝義識來說,心智所施設的事物,並不能起「因緣」的力用之原則,但達倉卻將一切極微塵所成的蘊聚事物,皆納入名言施設的事物之範疇中。然而,格魯派對此是不認同的。
「起力用」就是指「生起果」。無常法以兩種途徑生起果:首先,無常法生出它們自己相續串的下一剎那;其次,無常法又擔當「因緣」,生起能緣取無常法之識。在此一脈絡下,達倉指出:由眾多部分聚合而成的事物不能勝義地生起能認知它之識,因為這些事物只是意識的施設。總而言之,個別極微塵是心所施設的整體事物(如椅、瓶)的存在所依處,這些整體事物不離於個別微塵。格魯派雖然同意這一點,但格魯派也會說:各部分的聚合(即整體事物)是(例如)椅子,從而這聚合和極微塵本身相較,並未更加有賴於思維所施設。從格魯派的觀點來看,極微塵所成的蘊聚事物(即椅子本身)把其相投予眼識,從而成為生起勝義識的「因緣」。故把其相狀投予眼識的「所現境」(藏:snang yul)是指這整張椅子,而不只是它的各個部分。
反之,達倉強調只有極微塵(即無常法內的無方分)才是現量的所現境。只有極微塵,而不是被施設的整體(whole)事物,才真正把其相投予識。每一項事物全屬思維所虛構。循這思路,達倉強調:人類作為整體事物的認知者,從生活到工作,都是在一個幾乎完全是唯概念地建構的國度當中。達倉批評格魯派沒有公平地對待經量部的細緻與敏銳,因為他們主張經量部把粗分境視作勝義諦,但實際上即使連毘婆沙師也不會這樣看。格魯派可對此的回應是:極微塵蘊聚的意思不外就是「椅」或「壺」,而這就是格魯派經量部的勝義諦,格魯派與達倉巴都一樣,不願以與極微塵分離的另一整體實物作為假名所依。故此,昂旺班丹在他對嘉木樣的《註解》中提到:
以下的立論被評為不妥:首先,認為「壺」是生自與壺的諸部分是異體之另一整體物;其次,認為能緣取「拿、坐等行動」的概念心生起自與壺等是異體的另一系列活動。
這說明格魯派視整體事物(whole,如「壺」)不外是極微塵的蘊聚,而不是什麽另外的東西,因而一項整體事物(與其諸部分)就是一體(梵:ekadravya,藏:rdzas gcig)。或以另一種方式來說,例如用於澆水的壺被視為一蘊聚成的事物,而不是一自立的實體。
儘管達倉及格魯派學者們都同意:一項整體事物不是外於其本身各别部分的另一自立體,但達倉仍把一項整體物(如一個壺)理解為唯思維所施設,而格魯派論師則保持相反的見解。因此,雖然格魯派所述的隨理行經量部都視壺等為勝義諦,他們卻不因而較毘婆沙師在存有論上賦予這些實物更重要的地位。毘婆沙師所以會把世俗諦詮釋為實事有(藏:rdzas su grub pa),這是因為它們具有自立體的一切意涵,而這對隨理行經量部而言是勝義諦或自相法。這一系的經量部稱粗分無常法(如「壺」)為勝義諦,而毘婆沙師則稱之為世俗諦,但此一事實仍不會成為判定毘婆沙師高於經量部的决定性證據。此外,經量部會把它們施設為假有,但毘婆沙師卻不會這樣。我們剛看到,經量部所講的世俗諦(例如「虛空無為」)並沒有本身自足實體的施設有。經量部的二諦說,還進一步有更細緻的涵義:當中能包含著「無遮」(藏:med dgag)在內的一類否定性概念,即不能自足的實物。據毘婆沙師,所有世俗諦及勝義諦皆是實事有(藏:rdzas su grub pa);因而,即使「遮遣」也是以這種方式被確立,所以毘婆沙師完全無法確立「無遮」的存在,因為無遮既不是實事有(藏:rdzas su grub pa),而無遮本身也不具有自足(藏:rang rkya ba)的實體。